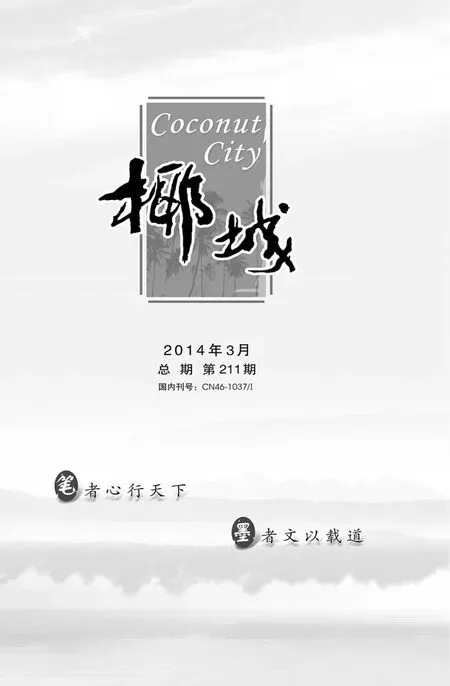十七棵松(外二篇)
2014-11-17 11:07:01張品成
椰城
2014年3期
■張品成
瑞金往北約十五公里的地方,有個由四個村民小組組合的小村,叫華屋。車入其境,始還不見,但汽車拐過一片樹叢,駛過一座小橋,村子就擁至視線里了。
和別處的客家老村落一樣,一些土坯房零零落落散布在山腳。山呈弓形,兩邊低中間高,當地人稱其“蛤蟆山”是有道理的,看去確實像一只窩開兩腿蹲趴在那的巨大蛤蟆。蛤蟆的“脊背”,長著一片茂密的林子。在客家,村村祠堂依坡而建,坡嶺上的林子都非常蔥郁,那叫風水地,樹叫后垅樹或者叫喉嚨樹,意指那是全村的風水寶地,一草一木是動不得的,所以,一般沒人砍樹削土,生態就尤其好。
就是在那片林子里,長著十七棵大松樹,松樹長了整整八十年了,主人指給我們看,果然那些松木殊然,遠遠能看到與其它雜木多不同之處。
主人給我們講了那個感人的故事,八十年前,有十七個華屋的青壯……其實我知道那一年的真實情況,在瑞金和周邊的蘇區,村里已經沒有什么“青壯”了,多是些未成年的少年。擴紅的那些日子,蘇區人民明白一個道理,沒有蘇區和紅軍,就沒有了田沒有了地沒有了一切,重新回到過去。毅然決然,這個詞就是當年十七個后生的心理寫照。那時他們十三四歲年紀,初生牛犢,意氣風發。
同是五月,我所知道的歷史,那時也正是禾青荷綠的時節。擴紅如火如荼。藍衫劇社的后生妹子走村串戶連軸轉了忙于演出,以歌喉和舞姿鼓舞前線和后方軍與民的斗志。但局勢不像歌舞里呈現的那么美好,不僅不好,而是十分糟糕。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