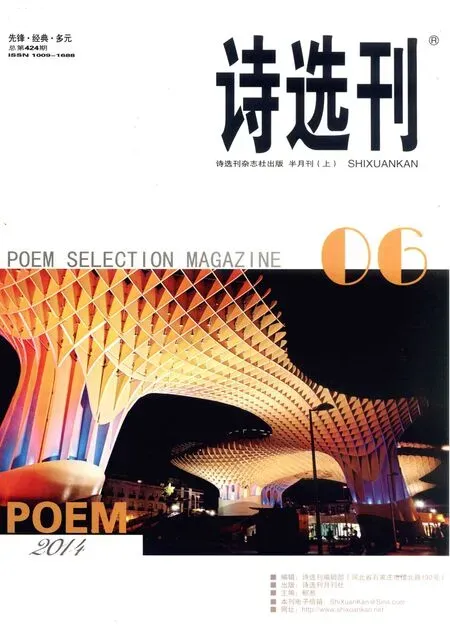純?cè)?/h1>
2014-11-15 06:19:24法國(guó)瓦雷里孟明
詩(shī)選刊 2014年6期
□【法國(guó)】瓦雷里/孟明 譯
社會(huì)上議論紛紛(我聽(tīng)到一些最可寶貴但用處最小的東西),大家紛紛議論這兩個(gè)字:純?cè)姟_@場(chǎng)議論,我多少有點(diǎn)責(zé)壬。幾年前,我給一位友人的詩(shī)集作序,我在序中偶爾提到這兩個(gè)字,當(dāng)時(shí)并沒(méi)有賦予它們以特別重要的意義,沒(méi)想到關(guān)心詩(shī)歌的人們竟從中作出一些推論。我很清楚我寫(xiě)下這兩個(gè)字所要表達(dá)的意思,但料不到會(huì)在文學(xué)愛(ài)好者中引起這么大的共鳴和這么大的反響。我當(dāng)時(shí)的用意,只是想引起大家注意一個(gè)現(xiàn)象而已,根本不是為了鼓吹一種理論,更不是給某個(gè)學(xué)說(shuō)下定義,也沒(méi)有把那些不贊成這一學(xué)說(shuō)的人視為異端。在我看來(lái),所有寫(xiě)出來(lái)的作品,所有語(yǔ)言作品,都含有某些可辨的、富于特征的片斷或成分,我們待會(huì)兒再作分析,我姑且把它們稱為詩(shī)歌性片斷或成分。每當(dāng)話語(yǔ)同最直接的思想表達(dá),即最不可感的思想表達(dá)有一定的距離時(shí),每當(dāng)這些距離以某種方式令人揣測(cè)出一個(gè)與純粹的實(shí)際世界不同的關(guān)系世界時(shí),我們多少會(huì)明確地去設(shè)想擴(kuò)大這一特殊領(lǐng)域的可能性,我們會(huì)有這樣的感覺(jué),好像我們抓住了某個(gè)高尚而生動(dòng)的題材的片斷,這一題材也許可以發(fā)揮或開(kāi)掘;一經(jīng)發(fā)揮和利用,它就會(huì)構(gòu)成作為藝術(shù)效果的詩(shī)。
這些成分非常具體可感,與我所說(shuō)的不可感的語(yǔ)言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我們應(yīng)善于利用這些成分來(lái)構(gòu)筑整部作品——通過(guò)一部韻文或非韻文作品,一方面把我們的觀念之間、意象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完整體系表現(xiàn)出來(lái),另一方面把我們的表現(xiàn)方式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完整體系表現(xiàn)出來(lái)——這一體系尤其適合于創(chuàng)造心靈的情感狀態(tài),純?cè)姷膯?wèn)題大致就是如此。我指的“純”,是在物理學(xué)家談?wù)搩羲囊饬x上說(shuō)的。我的意思是要弄清究竟能否組成一部完全沒(méi)有非詩(shī)歌性成分的“純”作品。我過(guò)去認(rèn)為,現(xiàn)在仍然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不可能達(dá)到的目標(biāo),詩(shī)永遠(yuǎn)只是為接近這一純粹的理想境界而作出的一種努力。簡(jiǎn)而言之,我們所說(shuō)的“詩(shī)”,實(shí)際上是由純?cè)姷钠瑪嗲对谝黄v話材料中構(gòu)成的。一句很美的詩(shī)乃是詩(shī)的一個(gè)很純的成分。人們把一句優(yōu)美的詩(shī)比作一顆寶石,這個(gè)平庸無(wú)奇的比喻說(shuō)明,這種純的品質(zhì)人人都感受得到。
美中不足的是,純?cè)娺@個(gè)字眼會(huì)使人想到一種道德上的純潔,但這不是我們?cè)诖擞懻摰膯?wèn)題。純?cè)姷母拍顚?duì)我來(lái)說(shuō)主要是分析性的概念。概括地說(shuō),純?cè)娛菑挠^察推斷出來(lái)的一種虛構(gòu),它應(yīng)有助于我們弄清詩(shī)的一般概念,應(yīng)能指導(dǎo)我們研究語(yǔ)言與它給人的效果之間的多種多樣的關(guān)系,這種研究是一項(xiàng)困難而重要的工作。也許,說(shuō)“純?cè)姟辈蝗缯f(shuō)“絕對(duì)的詩(shī)”好;似乎應(yīng)當(dāng)這樣理解,即把它看作一種探索,探索詞與詞之間的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效果,或者說(shuō)得確切一點(diǎn),探索詞與詞之間的共鳴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效果;一言以蔽之,這是對(duì)語(yǔ)言所支配的整個(gè)感覺(jué)領(lǐng)域的探索。這一探索可以摸索著進(jìn)行。也許有一天,這種探索會(huì)有系統(tǒng)地進(jìn)行,這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曾想對(duì)詩(shī)歌問(wèn)題有一個(gè)清晰的概念,至少有一個(gè)我所認(rèn)為的比較清晰的概念,至今我仍在做這方面的嘗試。今天,這類問(wèn)題顯然引起了人們十分廣泛的興趣。似乎從來(lái)沒(méi)有這么多熱心的讀者,他們不僅對(duì)詩(shī)歌本身感興趣,而且對(duì)詩(shī)歌理論也很感興趣。他們參加討論,出現(xiàn)一些探索,這些探索不像過(guò)去那樣僅局限于一些極其封閉、極少愛(ài)好者和實(shí)驗(yàn)者的團(tuán)體。我們時(shí)代蔚為奇觀的是,公眾中有這么一種志趣,有時(shí)是強(qiáng)烈的志趣,致力于這類近乎神學(xué)的探討(如探討靈感與制作,探討直觀的價(jià)值與藝術(shù)技巧的價(jià)值的比較,難道還有比這種探討更神學(xué)化的嗎?這些問(wèn)題不是很類似恩典與善功的著名神學(xué)問(wèn)題嗎?同樣,詩(shī)有些問(wèn)題,由于把傳統(tǒng)所確立的并固定下來(lái)的標(biāo)準(zhǔn)同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或內(nèi)心感覺(jué)的直接材料對(duì)立起來(lái),因而與神學(xué)領(lǐng)域里的問(wèn)題十分接近,神學(xué)領(lǐng)域也有對(duì)神性事物的個(gè)人感受、直接了解和各種宗教教育之間的問(wèn)題,即《圣經(jīng)》經(jīng)文和教理形式之間的問(wèn)題……)。
談到正題,凡不屬于完全的事實(shí)或非淺顯易懂的推論所得出的結(jié)果,我一概不提。讓我們回到“詩(shī)”這個(gè)字眼上來(lái)吧。首先要注意的是,這個(gè)漂亮的名詞產(chǎn)生兩種不同的概念范疇。我們說(shuō)“詩(shī)”,我們也說(shuō)“一首詩(shī)”。談到風(fēng)景,談到境況,有時(shí)談到人,我們說(shuō)它(他)們“很有詩(shī)意”;另一方面,我們也談詩(shī)的藝術(shù),我們說(shuō)“這首詩(shī)很美”。前者顯然是某種情感的問(wèn)題;當(dāng)我們受到某些環(huán)境的影響而感奮、愉悅時(shí),我們每個(gè)人都體會(huì)到這種特殊的震動(dòng)很接近我們的處境。這種情況完全不受一切業(yè)已確定了的作品的約束,它自然地、自發(fā)地產(chǎn)生于我們內(nèi)部的生理和心理狀況與引起我們強(qiáng)烈感受的(真實(shí)的或虛構(gòu)的)環(huán)境之間的某種和諧。但另一方面,當(dāng)我們講詩(shī)的藝術(shù)或談?wù)撘皇自?shī)時(shí),涉及的顯然是方法問(wèn)題,即怎樣產(chǎn)生類似上面的情形,怎樣人為地引起這種情感。這還不夠。還得讓幫助我們引起這種情感狀態(tài)的手段具有抑揚(yáng)頓挫的語(yǔ)言的特性和機(jī)制。我剛才所說(shuō)的情感,可以由事物引起,也可以由語(yǔ)言以外的其他手段激起,譬如建筑、音樂(lè)等;但嚴(yán)格意義上的詩(shī)本質(zhì)上采用語(yǔ)言作為手段。至于獨(dú)立的詩(shī)情,必須注意,它與人類其他情感的區(qū)別在于一種獨(dú)一無(wú)二的性質(zhì),一種十分奇妙的特性:它傾向于使我們感覺(jué)到一種幻象。或一個(gè)世界的幻象(這個(gè)世界中的事件、形象、生靈、事物,雖然很像充斥于普通世界的那些東西,卻與我們的整個(gè)感覺(jué)有一種說(shuō)不出的密切關(guān)系)。司空見(jiàn)慣的物體與生靈在某種程度上被“音樂(lè)化”了——請(qǐng)?jiān)徫沂褂眠@樣的字眼,它們變得互相共鳴,仿佛與我們的感覺(jué)是合拍的。這樣一解釋,詩(shī)的世界就與夢(mèng)境很相似,至少與某些夢(mèng)所產(chǎn)生的境界很相似了。當(dāng)我們回想夢(mèng)境的時(shí)候,夢(mèng)就使我們明白,一些產(chǎn)物的聚合可以喚醒我們的知覺(jué),使之或充實(shí)或滿足,而這些產(chǎn)物就其規(guī)律來(lái)說(shuō)與感知的普通產(chǎn)物是迥然而異的。但要隨便進(jìn)入或離開(kāi)這個(gè)有時(shí)可以通過(guò)做夢(mèng)而認(rèn)識(shí)的情感世界,并不是我們的意志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的身上包容了這個(gè)世界,而這個(gè)世界也包容了我們——這就是說(shuō),我們拿它沒(méi)法,我們不能對(duì)它施加作用以改變它,反之,它也不能同我們對(duì)外部世界的巨大作用力并存。它變幻莫測(cè)地出現(xiàn)和消失,盡管如此,人還是盡了一切努力,為一切寶貴而易逝的東西所做過(guò)的或曾試著做過(guò)的事,也為它而做了;人探索并想出了辦法來(lái)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創(chuàng)造這個(gè)境界,什么時(shí)候愿意就什么時(shí)候再現(xiàn)這個(gè)境界,并且最后可以人為地發(fā)展這些人類情感的自然產(chǎn)物。在某種程度上,人已經(jīng)能夠把這些極其不穩(wěn)定的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從自然界中抽出來(lái),從盲目流逝的時(shí)間中截下來(lái);人懷著這樣的目的,使用了我提到過(guò)的好幾種手段。在這些創(chuàng)造詩(shī)的世界并使之再現(xiàn)、使之豐富的手段中,最古老、也許最經(jīng)久的,然而也顯最復(fù)雜、最難使用的,要數(shù)語(yǔ)言了。
在這里,我要讓人們了解,現(xiàn)時(shí)代詩(shī)人的任務(wù)是多么的棘手,他在工作中遇到多少困難(幸而,他并不總是意識(shí)到困難)。語(yǔ)言是一種普通而實(shí)用的東西,當(dāng)然也就是一種粗陋的工具,每個(gè)人都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lái)使用它,傾向于按自己的個(gè)性改變它的形狀。不管語(yǔ)言與我們多么密切相關(guān),不管用語(yǔ)言的形式來(lái)思維多么接近我們的心靈,語(yǔ)言畢竟起源于統(tǒng)計(jì),而且純粹以實(shí)用為目的。所以,詩(shī)人的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是利用這一實(shí)用的工具,從中獲得手段來(lái)完成一件本質(zhì)上并無(wú)實(shí)用價(jià)值的作品。我早就說(shuō)過(guò),詩(shī)人的任務(wù)是創(chuàng)造與實(shí)用范疇無(wú)關(guān)的一個(gè)世界,或一種秩序,一種關(guān)聯(lián)體系。
為了讓人們能夠設(shè)想一下這項(xiàng)工作的全部困難,我要把擺在詩(shī)人面前同擺在與他目標(biāo)相近的另一類型的藝術(shù)家面前的初始狀況、已有條件、方法手段作一比較。我要比較一下詩(shī)人的已有條件和音樂(lè)家的已有條件。音樂(lè)家多么幸運(yùn)!他那門(mén)藝術(shù)的發(fā)展,幾百年來(lái)已經(jīng)給他提供了一個(gè)得天獨(dú)厚的環(huán)境。音樂(lè)是如何構(gòu)成的呢?聽(tīng)覺(jué)為我們提供音響的世界。我們的耳朵接納在某個(gè)層次聽(tīng)到的無(wú)限的感覺(jué),欣賞這些感覺(jué)的四種不同的質(zhì)。有些古代的觀察和古老的經(jīng)驗(yàn)早已能夠從音響的世界里推出體系或樂(lè)音的世界,這些樂(lè)音格外簡(jiǎn)單,格外清晰可辨,非常適于組合和搭配——樂(lè)音一經(jīng)產(chǎn)生,耳朵,或者確切地說(shuō)聽(tīng)覺(jué),就立刻感知它們的結(jié)構(gòu)、魅力、不同之處和相似之處。這些要素是很純的,換言之,是由很純的成分構(gòu)成的,也就是具體可感的;它們被恰到好處地確定下來(lái)了,更重要的是人找到了辦法,用樂(lè)器把它們持續(xù)地,同時(shí)地演奏出來(lái)。樂(lè)器實(shí)際上是名副其實(shí)的節(jié)奏的工具。一件樂(lè)器就是一件工具,我們可以調(diào)校它,支配它,用它來(lái)使確定的動(dòng)作相應(yīng)地收到確定的效果。這種聽(tīng)覺(jué)領(lǐng)域的組合,其效果是顯著的。樂(lè)音的世界從聲音的世界分離出來(lái),而我們的耳朵也習(xí)慣了清晰地分辨樂(lè)音之后,便產(chǎn)生這樣一種情況:一個(gè)純的音,即一個(gè)比較特殊的音,一旦被我們聽(tīng)見(jiàn),我們的感官就立刻產(chǎn)生一種特殊的氛圍,一種特殊狀態(tài)的期待;這種期待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引起一些相同的感覺(jué),跟已產(chǎn)生的感覺(jué)一樣地純。假如一座音樂(lè)廳里正在演奏一段曲子,突然間響起一個(gè)聲音(一把椅子倒啦,一個(gè)不悅耳的嗓音啦,或者聽(tīng)眾的一聲咳嗽啦)我們就會(huì)感到身上有什么東西被打斷了,不知冒犯了哪一處內(nèi)容或哪一條組合規(guī)律,一個(gè)世界破碎了,一種魅力消失了。
由此可見(jiàn),音樂(lè)家開(kāi)始工作之前,在他面前已有一切現(xiàn)成的準(zhǔn)備,從而使他的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活動(dòng)一開(kāi)始就有了內(nèi)容以及合適的手段,不致出錯(cuò)。他用不著改變內(nèi)容和手段,只需把業(yè)已確定并準(zhǔn)備好了的要素搭配起來(lái)就行了。
但詩(shī)人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擺在他面前的是普普通通的語(yǔ)言。這些籠統(tǒng)集中在一起的手段不是專為他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因而不合他的意圖。這里,沒(méi)有物理學(xué)家來(lái)為他確定這些手段的關(guān)系;沒(méi)有音階的創(chuàng)造者;沒(méi)有定音笛,沒(méi)有節(jié)拍器;在這方面沒(méi)有任何切實(shí)可靠的東西,只有字典和語(yǔ)法書(shū)之類十分粗糙的工具。而且,他必須借助于普遍的擴(kuò)散性的期待,而不是借助于聽(tīng)覺(jué)那樣特殊的唯一的器官。音樂(lè)家強(qiáng)迫聽(tīng)覺(jué)接受他所強(qiáng)加的東西,聽(tīng)覺(jué)是期待和注意的最出色的器官。作家則通過(guò)語(yǔ)言來(lái)借助期待,而語(yǔ)言是一個(gè)十分奇特的混合體,充滿了無(wú)條理的刺激,沒(méi)有什么東西比這種奇特的組合更復(fù)雜,更難以清理了。大家知道,聲音和意義的諧調(diào)是多么少有。大家也知道,一篇講話可以呈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特性:它可以合乎邏輯但不和諧;它可以和諧但沒(méi)有意義;它可以明白易懂但一點(diǎn)也不美;它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詩(shī)。只要舉出為探索語(yǔ)言的這種多樣性并研究其各個(gè)側(cè)面而創(chuàng)立的各門(mén)科學(xué),就足以一一概括這些各個(gè)不同的模式了。語(yǔ)言是靠語(yǔ)言依次加以辨別的,還要加上格律和節(jié)奏;既有邏輯的一面,又有語(yǔ)義的一面,包括修辭和句法。我們知道,這分門(mén)別類的學(xué)科可以采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來(lái)研究同一篇文字……詩(shī)人所打交道的就是這個(gè)五花八門(mén)、富于原始特征的大雜燴,它太豐富了,因而總體上顯得蕪雜。詩(shī)人就是要從這里提取他的藝術(shù)品,制造產(chǎn)生詩(shī)情的機(jī)器。也就是說(shuō),詩(shī)人必須支配這件實(shí)用的工具,這件人人創(chuàng)造的粗陋工具,這件用于滿足直接需要并由活人不時(shí)修改的日常工具,強(qiáng)迫它成為他所選擇的一種情感狀態(tài)的材料,這種情感狀態(tài)跟通常的感覺(jué)活動(dòng)或心理活動(dòng)的沒(méi)有明確延續(xù)時(shí)間的偶然狀況有著明顯區(qū)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普通的語(yǔ)言乃是共同生活雜亂無(wú)章的結(jié)果,因?yàn)椋鞣N類型的人所處的地位千差萬(wàn)別,他們各自的需求也多種多樣,他們接受了語(yǔ)言,卻盡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和趣味來(lái)使用它,藉以建立他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詩(shī)人雖然也得使用這一統(tǒng)計(jì)學(xué)上的混亂所提供的語(yǔ)言材料,但他的語(yǔ)言卻構(gòu)成一種個(gè)人的努力,即努力用民間粗俗的材料來(lái)創(chuàng)造一個(gè)虛構(gòu)的理想境界。
假使這個(gè)矛盾的問(wèn)題能夠徹底解決,即詩(shī)人能夠創(chuàng)作出不含半點(diǎn)散文成分的作品,寫(xiě)出來(lái)的詩(shī)具有不絕如縷的音樂(lè)美,各種意義之間的關(guān)系始終類似和聲關(guān)系,各種思想之間的演變顯得比任何思想本身都重要——那么,我們就可以像談?wù)摤F(xiàn)實(shí)的東西那樣談?wù)摗凹冊(cè)姟绷恕H欢吘共皇鞘聦?shí);語(yǔ)言的實(shí)際的或?qū)嵱玫牟糠郑?xí)慣與邏輯形式,以及我早己指出過(guò)的詞匯的雜亂與不合理(因?yàn)閬?lái)源很雜,年代不一,各種語(yǔ)言成分相繼引入)使得絕對(duì)的詩(shī)的作品不可能存在。但不難設(shè)想,這樣一種虛構(gòu)的或想象的境界,其概念對(duì)于欣賞一切可視的詩(shī)是大有裨益的。
純?cè)姷母拍钍且环N達(dá)不到的類型,是詩(shī)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理想極限……
猜你喜歡
如何在情感中自我成長(zhǎng),保持獨(dú)立中國(guó)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被情感操縱的人有多可悲家庭醫(yī)學(xué)(下半月)(2020年4期)2020-05-30 12:42:50 語(yǔ)言是刀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失落的情感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情感小太陽(yáng)畫(huà)報(bào)(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如何在情感中自我成長(zhǎng),保持獨(dú)立中國(guó)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讓語(yǔ)言描寫(xiě)搖曳多姿小學(xué)生作文(中高年級(jí)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多向度交往對(duì)語(yǔ)言磨蝕的補(bǔ)正之道瘋狂英語(yǔ)·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累積動(dòng)態(tài)分析下的同聲傳譯語(yǔ)言壓縮華北電力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4期)2016-12-01 03:59:30 情感移植發(fā)明與創(chuàng)新(2016年6期)2016-08-21 13:49:38
□【法國(guó)】瓦雷里/孟明 譯
社會(huì)上議論紛紛(我聽(tīng)到一些最可寶貴但用處最小的東西),大家紛紛議論這兩個(gè)字:純?cè)姟_@場(chǎng)議論,我多少有點(diǎn)責(zé)壬。幾年前,我給一位友人的詩(shī)集作序,我在序中偶爾提到這兩個(gè)字,當(dāng)時(shí)并沒(méi)有賦予它們以特別重要的意義,沒(méi)想到關(guān)心詩(shī)歌的人們竟從中作出一些推論。我很清楚我寫(xiě)下這兩個(gè)字所要表達(dá)的意思,但料不到會(huì)在文學(xué)愛(ài)好者中引起這么大的共鳴和這么大的反響。我當(dāng)時(shí)的用意,只是想引起大家注意一個(gè)現(xiàn)象而已,根本不是為了鼓吹一種理論,更不是給某個(gè)學(xué)說(shuō)下定義,也沒(méi)有把那些不贊成這一學(xué)說(shuō)的人視為異端。在我看來(lái),所有寫(xiě)出來(lái)的作品,所有語(yǔ)言作品,都含有某些可辨的、富于特征的片斷或成分,我們待會(huì)兒再作分析,我姑且把它們稱為詩(shī)歌性片斷或成分。每當(dāng)話語(yǔ)同最直接的思想表達(dá),即最不可感的思想表達(dá)有一定的距離時(shí),每當(dāng)這些距離以某種方式令人揣測(cè)出一個(gè)與純粹的實(shí)際世界不同的關(guān)系世界時(shí),我們多少會(huì)明確地去設(shè)想擴(kuò)大這一特殊領(lǐng)域的可能性,我們會(huì)有這樣的感覺(jué),好像我們抓住了某個(gè)高尚而生動(dòng)的題材的片斷,這一題材也許可以發(fā)揮或開(kāi)掘;一經(jīng)發(fā)揮和利用,它就會(huì)構(gòu)成作為藝術(shù)效果的詩(shī)。
這些成分非常具體可感,與我所說(shuō)的不可感的語(yǔ)言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我們應(yīng)善于利用這些成分來(lái)構(gòu)筑整部作品——通過(guò)一部韻文或非韻文作品,一方面把我們的觀念之間、意象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完整體系表現(xiàn)出來(lái),另一方面把我們的表現(xiàn)方式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完整體系表現(xiàn)出來(lái)——這一體系尤其適合于創(chuàng)造心靈的情感狀態(tài),純?cè)姷膯?wèn)題大致就是如此。我指的“純”,是在物理學(xué)家談?wù)搩羲囊饬x上說(shuō)的。我的意思是要弄清究竟能否組成一部完全沒(méi)有非詩(shī)歌性成分的“純”作品。我過(guò)去認(rèn)為,現(xiàn)在仍然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不可能達(dá)到的目標(biāo),詩(shī)永遠(yuǎn)只是為接近這一純粹的理想境界而作出的一種努力。簡(jiǎn)而言之,我們所說(shuō)的“詩(shī)”,實(shí)際上是由純?cè)姷钠瑪嗲对谝黄v話材料中構(gòu)成的。一句很美的詩(shī)乃是詩(shī)的一個(gè)很純的成分。人們把一句優(yōu)美的詩(shī)比作一顆寶石,這個(gè)平庸無(wú)奇的比喻說(shuō)明,這種純的品質(zhì)人人都感受得到。
美中不足的是,純?cè)娺@個(gè)字眼會(huì)使人想到一種道德上的純潔,但這不是我們?cè)诖擞懻摰膯?wèn)題。純?cè)姷母拍顚?duì)我來(lái)說(shuō)主要是分析性的概念。概括地說(shuō),純?cè)娛菑挠^察推斷出來(lái)的一種虛構(gòu),它應(yīng)有助于我們弄清詩(shī)的一般概念,應(yīng)能指導(dǎo)我們研究語(yǔ)言與它給人的效果之間的多種多樣的關(guān)系,這種研究是一項(xiàng)困難而重要的工作。也許,說(shuō)“純?cè)姟辈蝗缯f(shuō)“絕對(duì)的詩(shī)”好;似乎應(yīng)當(dāng)這樣理解,即把它看作一種探索,探索詞與詞之間的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效果,或者說(shuō)得確切一點(diǎn),探索詞與詞之間的共鳴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效果;一言以蔽之,這是對(duì)語(yǔ)言所支配的整個(gè)感覺(jué)領(lǐng)域的探索。這一探索可以摸索著進(jìn)行。也許有一天,這種探索會(huì)有系統(tǒng)地進(jìn)行,這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曾想對(duì)詩(shī)歌問(wèn)題有一個(gè)清晰的概念,至少有一個(gè)我所認(rèn)為的比較清晰的概念,至今我仍在做這方面的嘗試。今天,這類問(wèn)題顯然引起了人們十分廣泛的興趣。似乎從來(lái)沒(méi)有這么多熱心的讀者,他們不僅對(duì)詩(shī)歌本身感興趣,而且對(duì)詩(shī)歌理論也很感興趣。他們參加討論,出現(xiàn)一些探索,這些探索不像過(guò)去那樣僅局限于一些極其封閉、極少愛(ài)好者和實(shí)驗(yàn)者的團(tuán)體。我們時(shí)代蔚為奇觀的是,公眾中有這么一種志趣,有時(shí)是強(qiáng)烈的志趣,致力于這類近乎神學(xué)的探討(如探討靈感與制作,探討直觀的價(jià)值與藝術(shù)技巧的價(jià)值的比較,難道還有比這種探討更神學(xué)化的嗎?這些問(wèn)題不是很類似恩典與善功的著名神學(xué)問(wèn)題嗎?同樣,詩(shī)有些問(wèn)題,由于把傳統(tǒng)所確立的并固定下來(lái)的標(biāo)準(zhǔn)同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或內(nèi)心感覺(jué)的直接材料對(duì)立起來(lái),因而與神學(xué)領(lǐng)域里的問(wèn)題十分接近,神學(xué)領(lǐng)域也有對(duì)神性事物的個(gè)人感受、直接了解和各種宗教教育之間的問(wèn)題,即《圣經(jīng)》經(jīng)文和教理形式之間的問(wèn)題……)。
談到正題,凡不屬于完全的事實(shí)或非淺顯易懂的推論所得出的結(jié)果,我一概不提。讓我們回到“詩(shī)”這個(gè)字眼上來(lái)吧。首先要注意的是,這個(gè)漂亮的名詞產(chǎn)生兩種不同的概念范疇。我們說(shuō)“詩(shī)”,我們也說(shuō)“一首詩(shī)”。談到風(fēng)景,談到境況,有時(shí)談到人,我們說(shuō)它(他)們“很有詩(shī)意”;另一方面,我們也談詩(shī)的藝術(shù),我們說(shuō)“這首詩(shī)很美”。前者顯然是某種情感的問(wèn)題;當(dāng)我們受到某些環(huán)境的影響而感奮、愉悅時(shí),我們每個(gè)人都體會(huì)到這種特殊的震動(dòng)很接近我們的處境。這種情況完全不受一切業(yè)已確定了的作品的約束,它自然地、自發(fā)地產(chǎn)生于我們內(nèi)部的生理和心理狀況與引起我們強(qiáng)烈感受的(真實(shí)的或虛構(gòu)的)環(huán)境之間的某種和諧。但另一方面,當(dāng)我們講詩(shī)的藝術(shù)或談?wù)撘皇自?shī)時(shí),涉及的顯然是方法問(wèn)題,即怎樣產(chǎn)生類似上面的情形,怎樣人為地引起這種情感。這還不夠。還得讓幫助我們引起這種情感狀態(tài)的手段具有抑揚(yáng)頓挫的語(yǔ)言的特性和機(jī)制。我剛才所說(shuō)的情感,可以由事物引起,也可以由語(yǔ)言以外的其他手段激起,譬如建筑、音樂(lè)等;但嚴(yán)格意義上的詩(shī)本質(zhì)上采用語(yǔ)言作為手段。至于獨(dú)立的詩(shī)情,必須注意,它與人類其他情感的區(qū)別在于一種獨(dú)一無(wú)二的性質(zhì),一種十分奇妙的特性:它傾向于使我們感覺(jué)到一種幻象。或一個(gè)世界的幻象(這個(gè)世界中的事件、形象、生靈、事物,雖然很像充斥于普通世界的那些東西,卻與我們的整個(gè)感覺(jué)有一種說(shuō)不出的密切關(guān)系)。司空見(jiàn)慣的物體與生靈在某種程度上被“音樂(lè)化”了——請(qǐng)?jiān)徫沂褂眠@樣的字眼,它們變得互相共鳴,仿佛與我們的感覺(jué)是合拍的。這樣一解釋,詩(shī)的世界就與夢(mèng)境很相似,至少與某些夢(mèng)所產(chǎn)生的境界很相似了。當(dāng)我們回想夢(mèng)境的時(shí)候,夢(mèng)就使我們明白,一些產(chǎn)物的聚合可以喚醒我們的知覺(jué),使之或充實(shí)或滿足,而這些產(chǎn)物就其規(guī)律來(lái)說(shuō)與感知的普通產(chǎn)物是迥然而異的。但要隨便進(jìn)入或離開(kāi)這個(gè)有時(shí)可以通過(guò)做夢(mèng)而認(rèn)識(shí)的情感世界,并不是我們的意志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的身上包容了這個(gè)世界,而這個(gè)世界也包容了我們——這就是說(shuō),我們拿它沒(méi)法,我們不能對(duì)它施加作用以改變它,反之,它也不能同我們對(duì)外部世界的巨大作用力并存。它變幻莫測(cè)地出現(xiàn)和消失,盡管如此,人還是盡了一切努力,為一切寶貴而易逝的東西所做過(guò)的或曾試著做過(guò)的事,也為它而做了;人探索并想出了辦法來(lái)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創(chuàng)造這個(gè)境界,什么時(shí)候愿意就什么時(shí)候再現(xiàn)這個(gè)境界,并且最后可以人為地發(fā)展這些人類情感的自然產(chǎn)物。在某種程度上,人已經(jīng)能夠把這些極其不穩(wěn)定的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從自然界中抽出來(lái),從盲目流逝的時(shí)間中截下來(lái);人懷著這樣的目的,使用了我提到過(guò)的好幾種手段。在這些創(chuàng)造詩(shī)的世界并使之再現(xiàn)、使之豐富的手段中,最古老、也許最經(jīng)久的,然而也顯最復(fù)雜、最難使用的,要數(shù)語(yǔ)言了。
在這里,我要讓人們了解,現(xiàn)時(shí)代詩(shī)人的任務(wù)是多么的棘手,他在工作中遇到多少困難(幸而,他并不總是意識(shí)到困難)。語(yǔ)言是一種普通而實(shí)用的東西,當(dāng)然也就是一種粗陋的工具,每個(gè)人都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lái)使用它,傾向于按自己的個(gè)性改變它的形狀。不管語(yǔ)言與我們多么密切相關(guān),不管用語(yǔ)言的形式來(lái)思維多么接近我們的心靈,語(yǔ)言畢竟起源于統(tǒng)計(jì),而且純粹以實(shí)用為目的。所以,詩(shī)人的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是利用這一實(shí)用的工具,從中獲得手段來(lái)完成一件本質(zhì)上并無(wú)實(shí)用價(jià)值的作品。我早就說(shuō)過(guò),詩(shī)人的任務(wù)是創(chuàng)造與實(shí)用范疇無(wú)關(guān)的一個(gè)世界,或一種秩序,一種關(guān)聯(lián)體系。
為了讓人們能夠設(shè)想一下這項(xiàng)工作的全部困難,我要把擺在詩(shī)人面前同擺在與他目標(biāo)相近的另一類型的藝術(shù)家面前的初始狀況、已有條件、方法手段作一比較。我要比較一下詩(shī)人的已有條件和音樂(lè)家的已有條件。音樂(lè)家多么幸運(yùn)!他那門(mén)藝術(shù)的發(fā)展,幾百年來(lái)已經(jīng)給他提供了一個(gè)得天獨(dú)厚的環(huán)境。音樂(lè)是如何構(gòu)成的呢?聽(tīng)覺(jué)為我們提供音響的世界。我們的耳朵接納在某個(gè)層次聽(tīng)到的無(wú)限的感覺(jué),欣賞這些感覺(jué)的四種不同的質(zhì)。有些古代的觀察和古老的經(jīng)驗(yàn)早已能夠從音響的世界里推出體系或樂(lè)音的世界,這些樂(lè)音格外簡(jiǎn)單,格外清晰可辨,非常適于組合和搭配——樂(lè)音一經(jīng)產(chǎn)生,耳朵,或者確切地說(shuō)聽(tīng)覺(jué),就立刻感知它們的結(jié)構(gòu)、魅力、不同之處和相似之處。這些要素是很純的,換言之,是由很純的成分構(gòu)成的,也就是具體可感的;它們被恰到好處地確定下來(lái)了,更重要的是人找到了辦法,用樂(lè)器把它們持續(xù)地,同時(shí)地演奏出來(lái)。樂(lè)器實(shí)際上是名副其實(shí)的節(jié)奏的工具。一件樂(lè)器就是一件工具,我們可以調(diào)校它,支配它,用它來(lái)使確定的動(dòng)作相應(yīng)地收到確定的效果。這種聽(tīng)覺(jué)領(lǐng)域的組合,其效果是顯著的。樂(lè)音的世界從聲音的世界分離出來(lái),而我們的耳朵也習(xí)慣了清晰地分辨樂(lè)音之后,便產(chǎn)生這樣一種情況:一個(gè)純的音,即一個(gè)比較特殊的音,一旦被我們聽(tīng)見(jiàn),我們的感官就立刻產(chǎn)生一種特殊的氛圍,一種特殊狀態(tài)的期待;這種期待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引起一些相同的感覺(jué),跟已產(chǎn)生的感覺(jué)一樣地純。假如一座音樂(lè)廳里正在演奏一段曲子,突然間響起一個(gè)聲音(一把椅子倒啦,一個(gè)不悅耳的嗓音啦,或者聽(tīng)眾的一聲咳嗽啦)我們就會(huì)感到身上有什么東西被打斷了,不知冒犯了哪一處內(nèi)容或哪一條組合規(guī)律,一個(gè)世界破碎了,一種魅力消失了。
由此可見(jiàn),音樂(lè)家開(kāi)始工作之前,在他面前已有一切現(xiàn)成的準(zhǔn)備,從而使他的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活動(dòng)一開(kāi)始就有了內(nèi)容以及合適的手段,不致出錯(cuò)。他用不著改變內(nèi)容和手段,只需把業(yè)已確定并準(zhǔn)備好了的要素搭配起來(lái)就行了。
但詩(shī)人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擺在他面前的是普普通通的語(yǔ)言。這些籠統(tǒng)集中在一起的手段不是專為他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因而不合他的意圖。這里,沒(méi)有物理學(xué)家來(lái)為他確定這些手段的關(guān)系;沒(méi)有音階的創(chuàng)造者;沒(méi)有定音笛,沒(méi)有節(jié)拍器;在這方面沒(méi)有任何切實(shí)可靠的東西,只有字典和語(yǔ)法書(shū)之類十分粗糙的工具。而且,他必須借助于普遍的擴(kuò)散性的期待,而不是借助于聽(tīng)覺(jué)那樣特殊的唯一的器官。音樂(lè)家強(qiáng)迫聽(tīng)覺(jué)接受他所強(qiáng)加的東西,聽(tīng)覺(jué)是期待和注意的最出色的器官。作家則通過(guò)語(yǔ)言來(lái)借助期待,而語(yǔ)言是一個(gè)十分奇特的混合體,充滿了無(wú)條理的刺激,沒(méi)有什么東西比這種奇特的組合更復(fù)雜,更難以清理了。大家知道,聲音和意義的諧調(diào)是多么少有。大家也知道,一篇講話可以呈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特性:它可以合乎邏輯但不和諧;它可以和諧但沒(méi)有意義;它可以明白易懂但一點(diǎn)也不美;它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詩(shī)。只要舉出為探索語(yǔ)言的這種多樣性并研究其各個(gè)側(cè)面而創(chuàng)立的各門(mén)科學(xué),就足以一一概括這些各個(gè)不同的模式了。語(yǔ)言是靠語(yǔ)言依次加以辨別的,還要加上格律和節(jié)奏;既有邏輯的一面,又有語(yǔ)義的一面,包括修辭和句法。我們知道,這分門(mén)別類的學(xué)科可以采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來(lái)研究同一篇文字……詩(shī)人所打交道的就是這個(gè)五花八門(mén)、富于原始特征的大雜燴,它太豐富了,因而總體上顯得蕪雜。詩(shī)人就是要從這里提取他的藝術(shù)品,制造產(chǎn)生詩(shī)情的機(jī)器。也就是說(shuō),詩(shī)人必須支配這件實(shí)用的工具,這件人人創(chuàng)造的粗陋工具,這件用于滿足直接需要并由活人不時(shí)修改的日常工具,強(qiáng)迫它成為他所選擇的一種情感狀態(tài)的材料,這種情感狀態(tài)跟通常的感覺(jué)活動(dòng)或心理活動(dòng)的沒(méi)有明確延續(xù)時(shí)間的偶然狀況有著明顯區(qū)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普通的語(yǔ)言乃是共同生活雜亂無(wú)章的結(jié)果,因?yàn)椋鞣N類型的人所處的地位千差萬(wàn)別,他們各自的需求也多種多樣,他們接受了語(yǔ)言,卻盡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和趣味來(lái)使用它,藉以建立他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詩(shī)人雖然也得使用這一統(tǒng)計(jì)學(xué)上的混亂所提供的語(yǔ)言材料,但他的語(yǔ)言卻構(gòu)成一種個(gè)人的努力,即努力用民間粗俗的材料來(lái)創(chuàng)造一個(gè)虛構(gòu)的理想境界。
假使這個(gè)矛盾的問(wèn)題能夠徹底解決,即詩(shī)人能夠創(chuàng)作出不含半點(diǎn)散文成分的作品,寫(xiě)出來(lái)的詩(shī)具有不絕如縷的音樂(lè)美,各種意義之間的關(guān)系始終類似和聲關(guān)系,各種思想之間的演變顯得比任何思想本身都重要——那么,我們就可以像談?wù)摤F(xiàn)實(shí)的東西那樣談?wù)摗凹冊(cè)姟绷恕H欢吘共皇鞘聦?shí);語(yǔ)言的實(shí)際的或?qū)嵱玫牟糠郑?xí)慣與邏輯形式,以及我早己指出過(guò)的詞匯的雜亂與不合理(因?yàn)閬?lái)源很雜,年代不一,各種語(yǔ)言成分相繼引入)使得絕對(duì)的詩(shī)的作品不可能存在。但不難設(shè)想,這樣一種虛構(gòu)的或想象的境界,其概念對(duì)于欣賞一切可視的詩(shī)是大有裨益的。
純?cè)姷母拍钍且环N達(dá)不到的類型,是詩(shī)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理想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