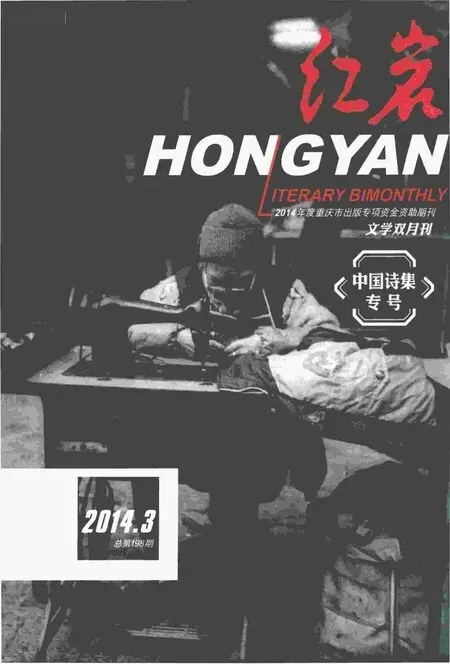臧棣詩集
2014-11-15 05:00:08臧棣
紅巖
2014年3期
天鵝湖叢書
住在周邊的人都管它叫
天鵝湖,里面卻沒有天鵝。
談不上空白玩弄了懸念,
也談不上接不接受命運,除非
有人佯裝喝醉,以你的名義,
給親愛的烏鴉寫過信。
冬日的灰暗未必就不是一種治療。
小風景忠于自己的地盤,
默數風的秋千上,麻雀飛進心靈的次數
竟比喜鵲身上的黑白還多。
而且,在盛夏,我確實見過
成雙的白鷺在它的淺水區覓食。
隨后,時間的底片像是意外曝光,
白色的舞者一再暗示
我們誤會了我們的瘋狂。
精確于自我,和嚴肅于自我
其實也沒那么復雜,它們的分別
沒準就像為什么這棵槐樹上
有鳥巢,而那棵榆樹上卻沒有。
要么就是,在春天,湖水已解凍,
玉蘭已在它的小燈籠里打磨過生命之火;
抽芽的柳枝充當了記憶的劉海,
你站在岸上,隨著波紋的樂譜漸漸攤開,
那里未必就沒有天鵝的倒影。
雪球協會
在靜物的范圍內,它算得上是
一個模范:和我們一起
來到巔峰,卻沒有替身;
已經比蘋果還渾圓了,且足夠硬,
卻沒有緋聞。它順從我們的制作,
順從得幾乎毫無懸念—
從揉捏到拍打,它默默承受,
沿每個角度體會,并鞏固我們施加
在它身上的冰冷的外力。
它小小的消極偉大得
如同一個假象。如此,靜物是它
封閉的童年,但它很快
就會滾向它的青春,并反襯
我們是還需補辦身份證的巨人。
從小變化到大,它用迅速的膨脹
取代了漸漸成長;但它的性急中
我們要負多半責任。它性急如
我們渴望盡早看到一個游戲的結果。……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