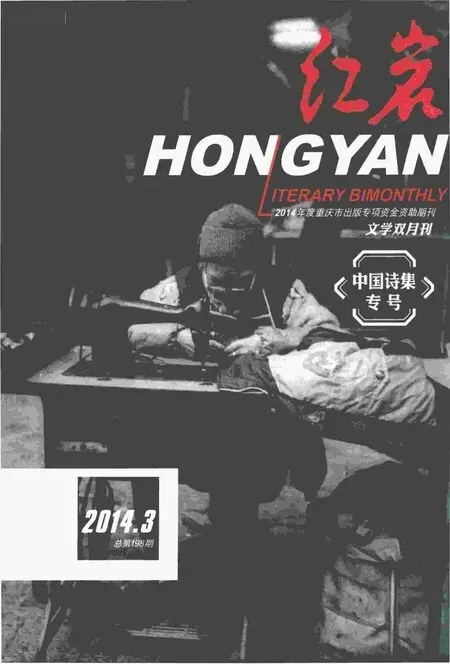我不認識楊黎
2014-11-15 05:00:08姚誠
紅巖
2014年3期
姚 誠
中午站在足球場邊的20分鐘,翻了一遍手里楊黎的詩,給我的印象是他在將一切嚴肅的東西淡定化,從一開始他就決絕地拒絕普通的人生,或者他的多次的愛,他的欲望,更加簡單干凈。
我喜歡楊黎,因為他不是君子,也不是偽君子,他是真實的人。于堅說他是“最沒有詩人氣質的詩人”,看到楊黎的照片,我只想說,上輩子,他肯定是賣豬肉的。楊黎。
尋找楊黎。楊黎的意義體現在80年代,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其中關于80年代詩歌的章節(jié),都提到了楊黎。“楊黎詩歌創(chuàng)作的意義就是通過對傳統(tǒng)詩歌語言習慣的顛覆,借鑒羅伯·格里耶小說的‘物化描述性寫作’,改變現實與語言之間的確定意義關系,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語感先于語義,語感高于語義’的新型的詩歌形式。”程光煒指出了語感在楊黎詩歌中的決定作用,或者他是有意地想保留語義,語義的作用雖然弱化了,可還存在,而這并沒有達到楊黎的真正意圖,消除語義。楊黎是非非主義最實干的詩人,他不像其他人醉心于理論的舌戰(zhàn),他用他最具力量的創(chuàng)作,《冷風景》《高處》《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等,實實在在地打出一發(fā)發(fā)威力十足的炮彈,轟隆隆地震顫著當時的中國大地。
我們問《冷風景》要表達什么?《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表達了什么?什么都沒表達。那我們讀的是什么?我們讀的是詩。詩是什么?楊黎說,詩啊,言之無物。詩是語言,詩就是語言,能指的集合,沒有所指,沒有意義。……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福建中學數學(2023年5期)2024-01-25 17:41:36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家庭醫(yī)學(下半月)(2020年4期)2020-05-30 12:42:50
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小太陽畫報(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護士進修雜志(2017年7期)2017-04-25 03:15:14
護士進修雜志(2017年4期)2017-04-19 11:31:07
護士進修雜志(2017年3期)2017-02-14 07:19:35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6年3期)2016-11-11 06: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