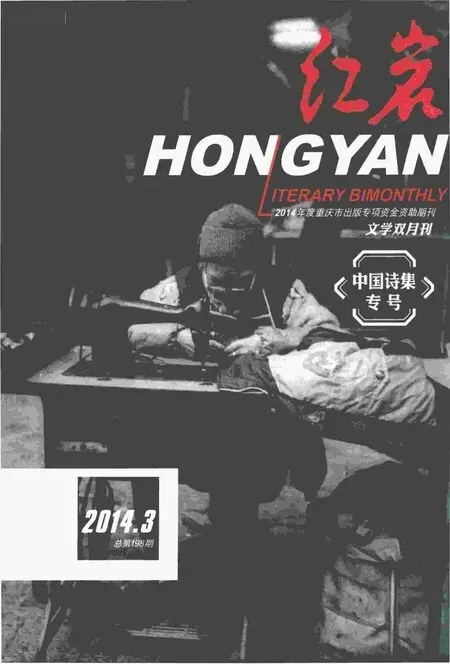給宋煒的齊東野語
2014-11-15 05:00:08陳瑞生
紅巖
2014年3期
關鍵詞:生活
陳瑞生
宋煒:
……值得稱道和欣喜的是,從《土主紀事》開始,你也走了敘事一路—當學科間的可通約性喪失、“元敘事”和“大敘事”走向終極的時候,我發現,你紀事系列的作品中,有著一種抗拒和制衡“小敘事”的努力。而對字斟句酌的顛覆,將地域色彩頗濃的詞恰到好處地穿插騰挪,更使這些詩歌與其他作品區別開來。我尤其看好《土主紀事》、《桂花園紀事》和《上墳》中開闊的語境、顧盼的語意和飽滿的語言,其間的詩歌理路和法度遺澤深遠、淵源有自,直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的《家語》、《戶內的詩歌和迷信》等。內中的泛神或泛靈之氣一脈相承,若合符契—無論道形還是佛神—盡管這種語言形態和敘述策略難度系數較高。
在空中隨風搖曳的天象館,
屋頂全都由亮瓦蓋成—某個星君
會在后半夜從上往下打探,
看見擁擠的房事,漣漪顫動的水缸,
和連夜長起的草木,瞬目間
就蓋過了屋頂:這是連神仙也看不盡的人間。
筋疲力盡的日子里,讀到這樣的句子,無疑是一種釋然。《土主紀事》呈現的心象和意圖是十分綿密的,讓人不期然遭遇了迫在眉睫的現時,莫名其妙地回想起過往那些因川資困竭而久暫的放浪和荒唐的悠游,在正本清源的沖洗后所受到的寬大對待,并進而日益變得清晰、生動,正中下懷。
我享受著這些蒙昧的雜碎,一邊吃
一邊打望,細辨從小區內魚貫而出的女眷們——
真是粉子如云啊,我想,這才是
這個如此腌臜的小區
被叫成“花園”的唯一理由。
我喜歡《桂花園紀事》中這種以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應付倒霉日子的世俗樂趣與心境超越。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