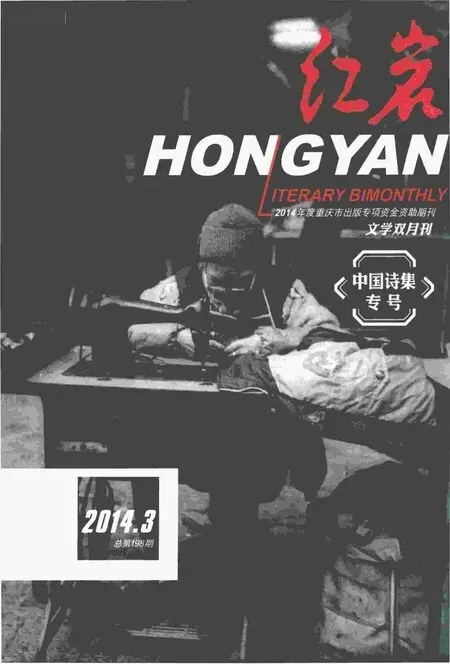宋煒詩集
2014-11-15 05:00:08宋煒
紅巖
2014年3期
下南道:一次閑居的詩紀(組詩選其四)
1、猶如市場街的……
猶如市場街的斯賓諾莎所見,
萬物中可以肯定的是身上的綢衣,
像感冒一樣周詳,不然就像嚴格的風俗或教育;
可以肯定的必然是眾街坊:剛一閃念就能迎頭撞上
一群小兒,一系列轉彎抹角,一小堆
垃圾(此時唯月光能使之清潔);
尤其可以肯定的是月餅中的蝦仁餡料,以及
頭下的枕頭,嘴中吮吸的大拇指(代表幼小的幸福)。
除此,不妨懷疑我所統治的這一身
皮肉和骨頭會消亡至無。我曾有過許多
能經由空氣與我相牽連的事物,
它們風起云涌,之后又風流云散。
現在我來到屋外,唯一能見的僅剩一群進山的香客:
其中一個腰纏紅紗,水色甚是了得。只有這些了。
或許可能會有某個地方神祗冒死出來否認
這正在行進的其實乃下南道最后的窮途:
四周風光沒落,景色一落千丈!
呀,仿佛我就這樣聽信道途之言,
將由小得來的信念給動搖了。但我不。
我還可以信任更多不存在的東西,當我
一再在心頭默想它們。因為倘若我在此刻
言說的比之于我死后(或我在掩體中)
必定發炎的骸骨更持久,我就不妨
以為現存的其實是足夠的,對,是足夠的,
哪怕全部書卷也有讀畢之日。同樣,天使也有休息日,
精密的計謀亦因敵人的美麗而放松了警惕;
一朝一夕,分娩的膿血化開,殷勤的學堂散課,
木梳和象牙梳的齒節斷落,
一只烏鴉身上也分離出燕子或喜鵲。
那么,沒有哪一種哭泣是有理的或正義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