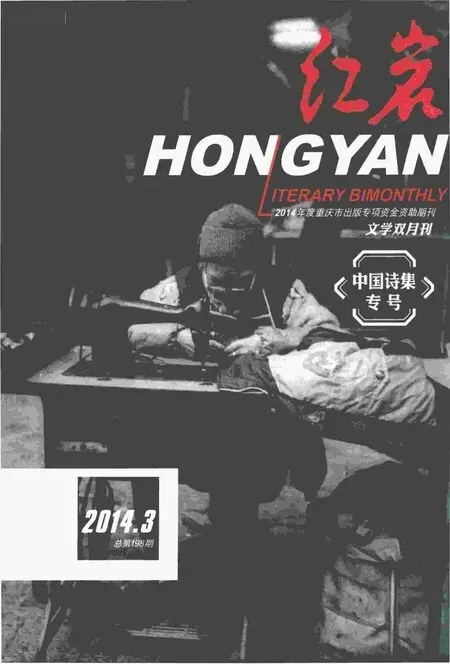在某詩(shī)歌論壇上的發(fā)言
余 怒
剛才胡續(xù)冬提到他在北大給學(xué)生講毛片,很好。很多學(xué)生太純潔了,不解世事。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歌界,也是這樣,很多詩(shī)人太純潔,太嚴(yán)肅,太不好玩了。詩(shī)歌中無(wú)趣、乏味、裝。文學(xué)應(yīng)該全面地反映人性,不只是純潔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不妨也弄一點(diǎn)毛片,但我所說(shuō)的這個(gè)“毛”并不是下半身那樣的“毛”,而是亨利米勒、凱魯亞克、納博科夫、庫(kù)雷西那樣的“毛”,帶有文學(xué)性和語(yǔ)言革新的“毛”。我個(gè)人覺(jué)得,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歌的現(xiàn)狀,是比較腐朽的,只有那么幾種類型的寫作方式。
大家都正兒八經(jīng)的在寫詩(shī),提起筆就提醒自己“我在寫詩(shī)”,作品過(guò)于像詩(shī)的樣子,寫出來(lái)就類型化了。我們?cè)倏纯串?dāng)代藝術(shù),不斷有人突破既有的藝術(shù)觀念,拓展藝術(shù)的疆界。詩(shī)歌如果是一門藝術(shù)的話,那么寫作者,有一個(gè)最基本的東西,就是不斷更新對(duì)詩(shī)的定義,不斷地拓展。
8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guó)詩(shī)歌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停滯了,沒(méi)有人“胡鬧”了,大家都正經(jīng)起來(lái)了。給詩(shī)歌附帶很多的,比如說(shuō)社會(huì)的責(zé)任、道德、擔(dān)當(dāng),都是詩(shī)歌本體以外的東西。我認(rèn)為道德、責(zé)任那些東西,是人的責(zé)任,而不是藝術(shù)的責(zé)任。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比如說(shuō)像塞林格、納博科夫那樣的作家。我們的詩(shī)歌,為什么不能像繪畫界那樣充滿活力?為什么不能像杜尚,弄一個(gè)小便池放在這里,說(shuō):這就是藝術(shù)、這就是藝術(shù)品?小便池是不是藝術(shù)品是不重要的,關(guān)鍵是杜尚借此質(zhì)疑了既有的藝術(shù)的定義、美學(xué)原則,拓寬了人們看問(wèn)題的視野和對(duì)藝術(sh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