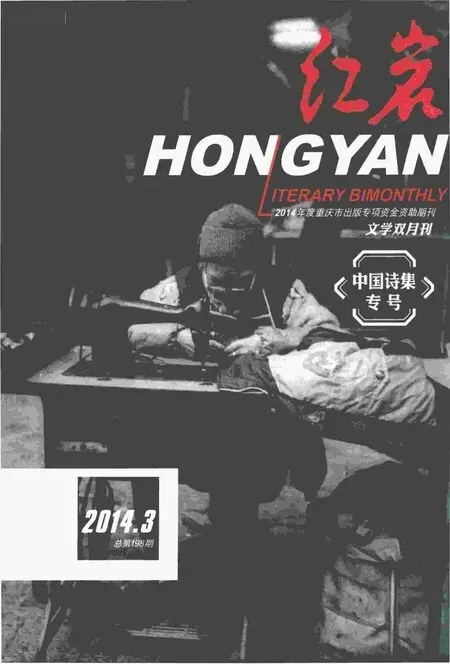三十年來我的幾種詩觀
2014-11-15 05:00:08柏樺
紅巖
2014年3期
柏 樺
1984:我的早期詩觀
人生來就抱有一個單純的抗拒死亡的愿望,也許正因為這種強烈的愿望才誕生了詩歌。
詩的價值在于它是一種高尚的無法替換的奢侈品,它滋補了那些患有高級神經病的美麗的靈魂。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懷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讀得懂詩歌,但我從不懷疑女性(或帶有女性氣質的男性)。她們寂寞、懶散、體弱和敏感的氣質使得她們不自覺地沉湎于詩的旋律。
詩和生命的節律一樣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旦它形成某種氛圍,文字就變得模糊并溶入某種氣息或聲音。此時,詩歌企圖去作一次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的純粹,但連最偉大的詩歌也很難抵達這種純粹,所以它帶給我們的歡樂是有限的,遺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是不能寫的,只是我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動用了這種形式。
我始終認為我們應當把注意力和興趣從詩歌轉移到詩人,因為我確信世界上最神秘的現象莫過于詩人這種現象。真正的詩人一定具有某種特殊的觸須,并以此來感知世界。詩人從事的事業對于他自己來說彷佛是徒勞而無意義的事業,但它是無垠的想象的事業。李白撈月的傳說,波德萊爾的人造天堂都證明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詩人是無所事事的奇怪的天才,然而是不朽的天才。
我的詩學時間觀
“夏天”是我個人命名的一個詩學時間觀。夏天是生命燦爛的時節,也是即將凋零的時節,這個詞讀出來最令人(令我)顫抖,它包含了所有我對生命的細致而錯綜復雜的體會。……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