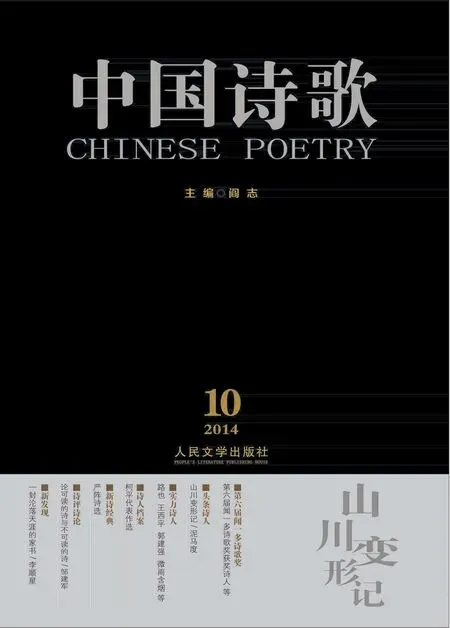微雨含煙的詩
微雨含煙的詩
一生熱愛的虛詞
啟動奇跡的日子是被命運接住的日子
我們感謝不經意到達和時間里
沒有錯失的那些
白車子依然揚塵,半卷的窗簾依舊
懸停在一個寂靜的下午
好于迢遙的一年一度。距此不遠
面南的山上,那些花
小野菊一樣頑強,成全了我的一年
一度。面對植物,勇氣可嘉
人就不必說了。
祝福總是第一個到達
但今日的缺席有令空氣阻滯的一瞬
高于落寞的宴請和空翻
一個月出現兩次的病毒,終于緊縮鼻孔
跟著一個傘柄,于驚鴻一瞥里
認出走出歷史的那個人
一生寫一首長詩,要用到怎樣的生平
符號就免了,用聲音代替
鼻音和卷舌音,成為依賴。
上午的末端,切開等待已久的草莓
鮮艷的火紅之心,守在案牘之上
如此。機緣。命運讓兩個一面之緣人再度重逢
維苡,有暗語穿梭的這些年
時間在維度上給予支持,由此及彼
拉住從地下通道涌出的青枝
第N次握手。并行的女人們
陷入空茫的等和猜測。低智的愛情
石橋鎮鎖住當年的疾病。如今
她又在同樣的月份里吃藥,打針,麝香正氣丸
還裝在背包里
連同那日的藥方和苦口的勸慰
燒鑄一個日子而已,這一等,歷史穿越屏障
天鵝翅膀下升起一座島嶼,黑與白的對峙
在那山坡上,在那綠樹下
在那水的交纏和火的洗禮中
契約生效,永無止期
白幔帳的車子揚塵而去
留下黑黑的你
和第三片白藥。夜走到中旬
針尖平息,流水靜止
潤滑是不遠的將來之事
紀念日。
用眾多詞搭建樓宇
第十三層歸你,第九層歸我
然后一起上到十四層。第三個房間。
愛生氣的青蛙和樹獺在沉睡
命運里有信任和交替而現的不安
買下時間的鏡面
體溫恒定在38.5℃,
迷迭香在集市上場,你在哪里
故鄉是哪里
但此刻,你我的黑夜
竟差了這么遠。風被阻隔在窗外
放它進來
恰如你合適的倒出,汁液和漿果
清洗第二遍血液。
掌上密布星斗。越長越像的兩個芒果。
快門“咔嚓”一閃,印跡生效。
籃球騎士在烈日下穿梭如風
躺椅也不能彎曲他挺拔的脊背
只有一種可能
能消解掉過剩的油脂
摩擦又摩擦
跑道永在,水龍頭和蓄水池
有奔襲和接納的榮幸
一條有待考察的街道和一個亟待打開的城市
鑰匙齊備,欄桿空置
紅碩的蘿卜,肥胖的手
向北的,豎在風中的小小鐵軌
等待爆裂的那日
黑夜和白晝一樣多汁而平穩
長椅上第二次坐著端莊的老虎
關于紙張的爭議已過,棉布裙束之高閣
在皮革盛行的第三年,他有樺鼠一樣美麗的三條銀線
她有老虎精致的花紋。七星在夜晚替老虎掃清障礙
命相里的九宮格預示安好
那在時間里遲到的
終于敞開蔽體的長袍,高山仰止
流水開動,在青草蓬勃之域
卸下重負,還針尖以流水
還日影以波紋,一庭院的兒女在列隊
齊齊站在偏北方向迎接
門在開啟,一年打開一個尺度
到全開時,藍蓮花得以歸位。
紫色的鳶尾和白天鵝等在拱橋之上
不為清風與明月
只有俠肝義膽的這一刻
潑墨生的留白,隨意附形
隨形附音,長在彼此身上
又不似彼此,眾多搖曳里的上升和攀附
然后塵埃一樣落下來,幸福地
無聲無息地
落
被舊事所吸收和成全
回蕩一種回蕩,無止境
極盡溫柔
在綿綿不斷的風中,如直覺
提醒那在風中被日子困囿之人
遠離堤岸要好于在風中見縫插針
鐵杵只在烈日的正午亮出白花花的身段
外人不懂,蒙著雙目
當然只有觀賞黑夜的權利
而我要收束這命定的箭鏃
替折紙人折好生之褶皺
留下風和流水,需要潤滑的針孔
剪刀就不必了,石頭也不必了
血管壁和血管壁里奔突著淡藍色的欲望之火
DNA幾近相似,血液在更新中
奔向睿智的你
汲取和給予基于自愿,
對于那些暗自叫囂乎東西的
請繞道而行
找到自己的畢加索和凡高,找到你的日光
放行自己
放開他人
舌頭抵住虛妄,磷粉在蝴蝶的翅翼下
牽引黑夜走向黎明。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極晝
一個高懸的春天
具備火,燒灼夏天的必然。
最終愛上的,才是守住命運的一個
用一生傾注,不抵抗,不產生歧義
水火相融,沒有撲滅和引燃一說
實在是好事一樁
還在等什么?二十四節氣步步為證
出發已是必然
只有忠誠和開始的第十三月
作為主角,我把粉紅色長裙燙了又燙
斜線條的擁抱和垂直而來的擊中
穿過雪山之巔和命運長河
一生熱愛相抵于一生倉促
在更早更早的遇見里,成為妻子,丈夫
我們美好的兒女
一曲箜篌亮出歸隱之心,守定田園
黑白棋子輾轉騰挪于方寸之間,大河之間
山川之間,相鄰的春風和花香滿徑輕輕的翹首之間
之間!
難以企及
距離巨大的懸崖。
難以企及。秋天漸漸紅腫
天造地設的懸念抖出包袱,差強人意
仍在原地。
時間能夠說了算的所剩無多。
玻璃罩中四處奔突的閃電
來自軀體,最后
鎩羽而息
難以企及時光設定的長久
度一日,一日便成多日
輾轉來去,留在最初的點上
難以企及。那個午后
他對她僅僅動了一下眉毛
她便成為一生無所終之人。
在無形的等中消耗掉已有的軀體
漫長有如虛擲。孤獨的、悲哀的、
疲倦的一切,在云朵的翻卷中落入極致的黑暗。
思想上的絕壁。
梯子取消向上的索要,歸于平
和低于海平面的涌動。城市濾掉星星的光芒
土撥鼠跳向糧倉
這一夜,有如更久前的一夜
黯淡、平靜,剔除水面上針尖的滑行
軀體消耗掉過剩的欲火
遠處的樹流出樹液
仿佛眼瞼,面向虛渺的來處
龐大的無形占據整個事件的始末
沒有人知道到來是個什么樣子,以及
那過程中有什么在慢慢失去。
有一座橋和無數盞燈
其實并不是一座橋。虛數甚于實數
在某些語意下,來得更恰如其事
不論日月,不論年代之先后
她是存在于此地的惟一一點
像橋上的霓虹,不斷轉換色彩與角度
惟獨橋身一直懸停于秋天之上
一個所等之物
一個起程的腳踵和一個抵臨的裙裾
將倒影印在月亮的環形山麓上
使你一抬頭,永遠在那里
或者在沉睡的另一側,使你一抬手
明天在那里,生長在那里
愛當然也在
銀河系永久的牽念中,修為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