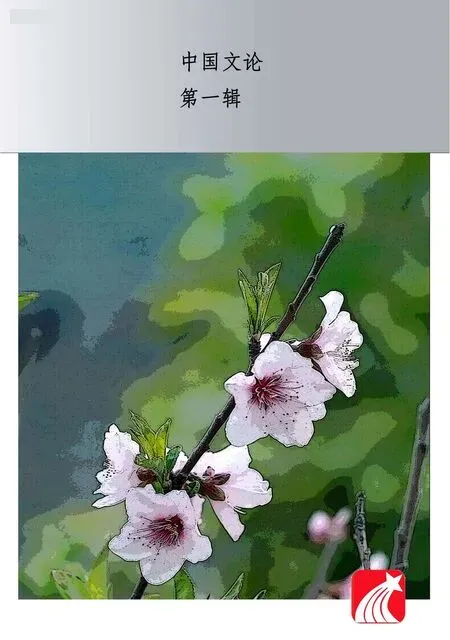歷久彌新的《文話》
陳家婷
歷久彌新的《文話》
陳家婷
著名語文教育大師夏丏尊、葉圣陶先生的《文話七十二講》,是中華書局“跟大師學語文系列叢書”收錄的五本關于文章寫作的名著之一,其源自于20世紀30年代兩位先生編的《國文百八課》,可惜因抗日戰爭爆發,《國文百八課》只出版了四冊,成七十二課。該書用七十二個主題,分別結合閱讀,主要講解文章的寫作方法。
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對“文”的定義與源流說法不一,因此對于“文”的解讀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是文學思想、文學現象以及文化的不同種類,大都是通過不同的文字形態呈現,并且這些文字有著其各自成文的規律和準則。信息時代的到來嚴重沖擊著傳統的文章觀,現代意義上以迅速、便捷為目標的觀念無疑逐漸淡化了諸多傳統觀念對文章的意義和作用的定義,甚至某些文體面臨岌岌可危的境況。在國學復興的今天,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國學在現實社會中的重要性,由此,“國學”統轄下的各個分支需要被重新認識和解讀。文章的寫作是每一個運用文字的人不可輕忽的技能,而今大多的學子仍舊會主觀臆斷地認為文章的寫作是信手拈來,尤其是對于大部分已在中學教育中普及到的常用文體,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人往往會被那些容易忽視的困難所羈絆。由此,《文話七十二講》在文章寫作中的指導作用就會愈發地歷久彌新。
或許大部分人會說,自小學開始我們就學習寫作,《文話》的內容只不過是重復一些耳熟能詳的內容,不值得一讀;或許會有人說《文話》每個主題內容過于簡短,重要部分沒有做出過多的闡釋;或許還會有人說,《文話》不過是用理論講寫作的又一部文章作法而已。
初識《文話》,有這樣的想法亦屬正常,但仔細研讀,自然別有會心。
《文話》由記敘文、論說文、文選三大部分組成,七十二講主要包括前兩個部分。《文話》將傳統認知上的記敘文細分為記敘文和敘說文;同時論說文部分也是將其區分為說明文和議論文兩種來展開講解。在每一種文體的講解中都是通過兩個視角去完成,即“文”的視角和“人”的視角。所謂“文”的視角即是針對不同文體的寫作要點來具體闡釋的,這也是為文的最基本要求。在書中講到關于記敘文和敘說文的順序,應用文、普通文的體式與禮儀,說明文、議論文的方法以及具體體式等一系列為文的基本準則與要求。
第二個視角,即“人”的視角,在談到敘述文時,《文話》涉及關于敘述的快慢、倒錯及觀點的一致與移動等一系列以情感的層次性和傳遞性為依據的解析方式。這些常常在為文過程中被我們忽視,卻又在文中充當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的敘事方法,猶如被寒冬肆虐的大地,經過一夜春風的吹拂,更是滋潤、更是柔軟了。更猶如第二十七講、二十八講、二十九講中關于敘述的場面、事物與心情、情感的流露等章節,并不是從如何寫好文章的角度去談論,而是站在“人”的角度設身處地去商榷如何真摯地講述一個故事、描述一個場景、表達一段真情,這樣的方式或許使我們更加容易接受,更愿意去接受。
一般來講,一本教你如何寫作的書,難免會硬性地強迫你去識記某一部分的理論,六要素、三方面等,這往往讓我們喪失了對學習寫作的興趣。魯迅認為:“不應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作文并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他還指出:“創造的基礎是生活經驗;而所謂生活經驗是在‘所作’以外也包括了‘所遇、所見、所聞’的。作者寫出創作來,對于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冰心也談到:“當由一個人物,一樁事跡,一幅畫面而發生的真情實感,向你襲來的時候,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長針,一陣卷到你面前的怒潮,你只能用最真切、最簡練的文字,才能描畫出你心尖上的那一陣劇痛和你面前的那一霎驚惶!”葉圣陶先生也曾說過:“我們知道有了優美的原料可以制成美好的器物,不曾見空恃技巧卻造出好的器物來。所以必須探到根本,討究思想、情感的事,我們這工作才得圓滿。”
由此可知,寫作的真正目的在于將自己所見、所聞、所感、所想記錄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形式重于內容的話就會顯得本末倒置。這也是我們歷來對于指導寫作的理論性書籍產生恐懼感的原因。然而《文話》整部書的寫作是以輕松講述的口吻將理論條理化、生動化,不再是之前刻板印象里嚴肅的先生,硬性地教你識記,而仿佛兒時母親的睡前故事,清新、明亮,帶你融入故事里,看似輕描淡寫,卻永遠記憶深刻。如書中第四十講關于“詩的本質”的講解,不是用大段理論告訴你什么是詩,詩的本質是什么,而是通過詩文與應用文的對比教你去感知。你或許會問,那到底什么是詩?為什么書中最后也并未給出答案?這也正是《文話》的妙處。它教你去感知,帶你去體會,教你用感覺統轄你所習得的基礎認知,好比《詩的本質》一講最后說道“……可以知道含有情緒、情操、想象的語言、文字就含有詩的本質”,“……必須是一個含有詩的本質的意思,用精粹的語言表達出來,那才是詩”。這些結語都不能看作是對“什么是詩”、“詩的本質是什么”的標準答案,但是或許這樣,我們才可以調動自身的各種感知和體驗,進而從“人”的角度去深層次認知。文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它本身就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文話》全書大都采取這樣的角度,完全以讀者為主體,既可以激發你閱讀的主動性,同時也不會給你重重的壓迫感。也正因如此,當讀完《文話》時,內心充滿了驚喜與詫異。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流傳于后世的不朽著作是一座巨大的寶庫,這其中有以文章為載體傳道的,有以文章表達情思的,而文章本身所體現出的審美屬性亦是不容置疑的財富。如《文心雕龍》,且不說其在文藝學、美學等領域的卓越識見,就其本身的寫作也為世人所驚嘆,它是后世文章寫作的極好典范。《文話七十二講》也是這樣,呂叔湘先生在《談國文百八課》中講到:“《文話七十二講》有系統而又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整齊,既有聯系,又不呆板,給讀者的整個印象是生動活潑的,本身就可以作為文章來學習。”如第二十八講“事物與心情”中說:“生性縝密的人常常喜歡寫事物優美的部分;生性闊大的人喜歡寫事物壯偉的部分;一個閑適的人聽了煩囂的蟬聲也會說它寂靜;一個憂愁的人看了嬌艷的春花也會感到凄涼。事物還是客觀的事物,一經主觀的心情照射上去,所現出來的就花樣繁多了”,第十四講和三十講中有言:“僅只有荊棘中的‘銅駝’,可以表現出國家的滅亡;僅只有鏡中的‘白發’可以表出衰老的光景……”,“明顯的方式比較強烈,好像一陣急風猛雨,逼得讀者沒有法子不立刻感受。含蓄的方式比較柔和,好像風中的柳絲或者月光下的池塘,讀者要慢慢的凝想,才能辨出它的情味來。”再如第三十一講說:“喜有輕喜和狂喜,怒有微怒和大怒,狂喜和大怒固然人己共覺,輕喜和微怒也決不會絕不自知。這種感情在我們心里激蕩的時候,好比江河涌來了潮水;等到激蕩的力量消退了,心境就仍舊回復到平靜……”《文話》中如此生動優美的論說比比皆是,確實是可以作為文章來學習的。以此而言,《文話》之作,可謂深得《文心雕龍》之三昧。
讀完這本書,或許有很大一部分讀者甚至包括我自己都會問:“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是否有必要從寫作的最基礎學起?”是的,我們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語文的學習從未間斷過,這就說明如何寫文章,寫好文章,一直是相伴我們左右的話題,即使是沒有認真學習,課堂中的耳濡目染,生活中的經歷已經教會我們如何講話、如何為文;經歷過高考模式化的訓練,我們積累了無數的素材,識記了無數的名言警句;再加上我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寫文章的水平應是不會太差。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寫作水平可能遠遠未盡人意,一個重要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文章被重重程式化所包圍,時常局限于一種狹隘的思維方式,從而忽略了大千世界的多面形態,也失去了基本的真情實感。戚良德老師在批改筆者的習作時說:“不要時時想著如何‘作文’,否則文章便會顯得拘謹。無論何種文章,首先是如實地傳達自己的思考,寫出自己真實的思想和感情。”《文話七十二講》的最終目的,亦正是如此。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章的寫作并不僅僅是那些華麗的辭藻與唯美生動的素材,有時候擁有一顆“復得返自然”的心,真正用心去體驗、用心去感知,以情為本,才能真正實現“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至高境界。
文章之作,關乎軍國大政、社稷蒼生,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謂“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所以《文心雕龍》開篇即言:“文之為德矣,大也!”詩圣杜甫亦告誡我們:“文章千古事。”也許正因如此,語文大師們才用心良苦地跟我們講解如何作文;實際上,《文話七十二講》既是作文之理,亦為人生之道。因為文“與天地并生”,亦必將與人生相伴左右;《文話》之歷久彌新者,良有以也。
陳家婷,女,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藝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