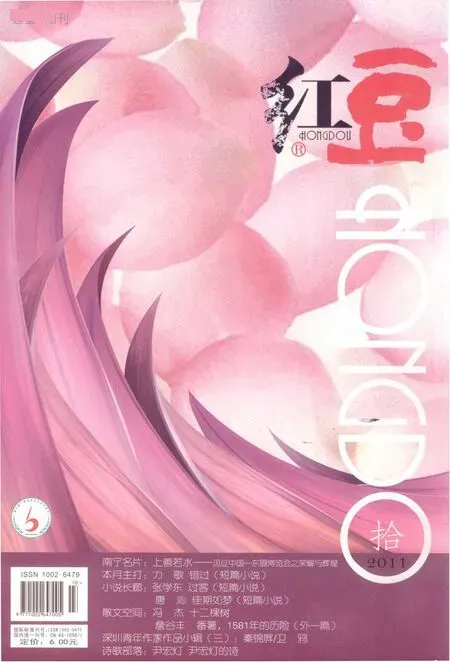馬過巴額
劍書,原名黃慶謀,80后,廣西鳳山縣人。散文、小說作品見于《廣西文學》《廣西文藝界》《紅豆》《野草》《讀者》《麒麟》《廣西日報》等報刊。曾獲2010年《廣西文學》“金嗓子”文學獎最具潛力新人獎。廣西作家協會會員。第十期廣西青年文學講習班學員,魯迅文學院第一期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學員。文學桂軍人才培養“1+2”工程扶持對象。
我的回鄉路常常是奔走在一場場夢境中。這夢,往往都是不請自來踢踏而入,仿佛一匹快馬,三步兩步就風塵仆仆跨進故園的疆界。
現在,我騎上馬背,策馬而去。彈指之間,我所說的故園,壯話叫巴額的寨子就在騰起的風沙里漸漸顯現它的輪廓、狀貌。
馬蹄噠噠,它一頭撞進童年的巴額。那時,巴額長有一顆拐爪樹,一棵柑橘,一棵桃樹,三棵李子樹。拐爪樹就長在我家瓦房前的菜地旁,它高過屋頂,稀疏的虬枝斜指天空,每到秋天,拐爪樹的葉子在風中打著旋片片飄下,拐爪在午后輕聲落地。那棵柑橘總是在還沒熟透前被像我這般的小孩兒摘光,酸澀的味道令我們齜牙咧嘴。那棵桃樹呢,入秋不久桃果就像半紅的燈籠掛滿枝頭,可惜我們剛過了幾個甜蜜的秋天,桃樹就被瘋狂的蟲子噬咬得奄奄一息,到了春天就干枯了,最終倒在刀斧之下,成為火灶里冒起青煙的柴火。那三棵李子樹倒是頑強,幾年來都不見一只蛀蟲冒犯它們,每年正月不久它就開出雪白雪白的花朵,在春寒料峭中洶涌怒放。當然,巴額不只有一棵拐爪樹,一棵柑橘,一棵桃樹,三棵李子樹,在它的領地里,還有兩座黑瓦木墻的吊腳樓,還有一口足有幾畝寬的大水塘,還有大片大片的層層梯田……
巴額,被大村大寨稱為巴掌大的巴額,那兩座黑瓦木墻的吊腳樓一家是我家,另一家是我滿叔家。原先的巴額不是這樣的。在我的堂姐斃命于一粒本該射向飛鳥但最后卻射向她的胸膛的子彈前,這里住有十幾戶人家,屋舍挨挨擠擠,人聲喧鬧。堂姐死后,寨子里來了一個身穿道袍的風水先生,他在享受了族人畢恭畢敬的禮遇和招待后站在寨子的曬臺上伸起食指朝巴額指指點點,預言“這個寨子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下去還會死人”。我的族人們嚇得面如土色,不過數月就相繼搬離巴額另尋別處安家立命,剩下的就只有我們家了。
不是我的家人不怕道袍先生可怕的預言,而是當時父親還在部隊服役,母親膝下還有未成年的一男兩女,她一個婦道人家手無縛雞之力,族人在一場血光之災后早已人心離散各掃門前雪,母親只能倚門以待盼望父親早日歸來。母親這一等,我家就在巴額待了三十幾年。幾年后,滿叔一家承受不了異族人的冷眼之苦,一怒之下拔屋而走重返巴額,我們家才漸漸變得有可傍依一掃愁容起來。
時至今日,我一如既往地堅執認為道袍先生的預言純屬一派胡言唯恐天下不亂。可是,我能抗拒道袍先生的危言聳聽,卻不能阻擋死亡在巴額的降臨,就如很多時候,我能止住眼淚,卻止不住悲傷。
滿叔的死和雄黃礦有關。我所在的鄉名叫金牙鄉,一個充滿俗世向往富貴的鄉名。與之相得益彰的是,金牙的山野不僅黃金儲量驚人,而且富含雄黃礦。本來,什么黃金什么雄黃和巴額半毛錢的關系都沒有,黃金是別人的,雄黃也是別人的,我們和別人同住在聚寶盆上,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開山采礦財源滾滾一夜暴富。可是,一場幾十年未遇的暴雨把巴額和雄黃礦勾連起來了,這一勾連就勾連出了一條人命。
那場暴雨下在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一夜之間,摧枯拉朽的山洪沖垮了雄黃礦山的攔砂壩,風停雨歇后早起的農人驚詫地發現,河灘上到處都是雄黃礦石,這天下的哪里是雨,下的是嘩嘩響的鈔票啊!很快,方圓幾里的村村寨寨炸開了鍋,大伙抓起口袋背起背簍牽兒拉女黑壓壓地撲向沿河河灘。一天下來,挖撿礦石的大軍多的有的能撿到一百多斤,少的也有十幾二十斤,那時的雄黃礦價格在兩三塊之間波動,一天下來的收入無不讓人心口火燒,雙眼發出高瓦度的亮光,仿若個個中了魔。
滿叔和我一樣,在攔砂壩垮塌的第三天也加入了挖撿礦石的大軍。我們來得晚了,河灘上已是千瘡百孔遍地狼藉,即使是掘地三尺,也就只挖到一些散碎的礦石。心有不甘的滿叔冒了險,和一些把死不當一回事的人摸入已經無人看管的礦窿。我害怕礦窿黑咕隆咚伸手不見五指,更害怕礦窿齊腰深的渾黃藏水,只能鎩羽而歸重返課堂。在我上學的路上,多次看到滿叔騎在高高的馬背大聲對我說“挖礦發財去咯”,第三次說這話時,拂曉的陽光正好打在滿叔的臉龐上,發出古銅般的光澤,我感覺,這時候的滿叔簡直就是畫中的人物,高大威凜,敬慕得令我心甘情愿抬頭仰視。而當暮色四合,我也多次見到滿叔牽著馬匹踏著微涼的夜色歸來。馬背上,兩袋滿滿的礦石在馬蹄聲聲中窸窣作響。看來,滿叔每一次冒死進入礦窿都沒有空手而歸。如今想起來,在回溯舊時光陰的視線里,我似乎看到一條金色的光束跟隨在此時的滿叔身后,那光束彌漫著燃燒的雄黃味道,刺鼻卻難以抵抗其魔力,這魔力可以讓滿叔寡淡的碗碟飄出勾魂的肉香味,可以讓常常相對無言的一家人突然從堂屋從門口從墻縫飛出歡聲笑語,甚至,可以讓睡著的滿叔冒出莫名其妙的笑聲。
事與愿違,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樣朝著好的方面發展。一個多月后,滿叔的雙腿開始腫脹起來,沒多久,腫脹蔓延到了他的肚腹。熬了一些時日,他的肚子已經腫脹如鼓,到醫院住了一段時間,醫生說滿叔的病癥因浸泡在雄黃礦水里過久而引起,現在已經晚了還是拉回家吧。回到家的滿叔頭段時間還能吃得下半碗干飯,后來就只能喝一些稀粥了。街天的時候,大人都去趕街,我和滿叔最小的兒子阿萬留下來守家。阿萬比我小,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孩童。空寂下來的寨子令我們恐懼,但一股強烈的好奇心卻驅使我們跑進屋子趴在門縫上向滿叔的病床張望。屏息靜氣中,我看到躺在床上的滿叔瘦得只剩下一副骨骼,先前那張曾被陽光照耀發出古銅光澤的臉龐被一張薄薄的皮包裹著,鼓突的兩只眼球直瞪瞪盯著黑蚊帳,似乎是有千言萬語要說,又仿佛是已經明白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但卻心有千般不服。
我和阿萬嚇得魂飛魄散,驚叫著奪門而出。等到四五天后我放學回來,滿叔已經被族人抬到堂屋正中間,臉上蓋著一張和臉龐同樣大小的紅紙,撒手人寰。長到這么大,我是第一次見到死尸,我躲到母親身后,頭卻不由自主地望向滿叔臉上的紅紙。一陣風吹來,吹亂了紙錢灰燼,也掀開了紅紙的一角。在稍縱即逝的那一刻,我看到滿叔的臉慘黃慘黃的,閉上眼睛,那紅紙覆蓋的臉強盜一樣跳進我的腦里,野蠻、霸道,讓我無處可逃,讓我一連數月都無法擺脫死亡氣息的追擊。
沒了爹的阿萬常常和我一起爬到屋旁的大水塘上,一坐就是發呆半天。有時我們有一搭沒一搭胡亂說些話,不過是放到山上的牛現在不懂跑到哪里去了,什么時候又能吃上一餐肉一類雞零狗碎的話。大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說什么話題好,只能默默無言。我們都明白,巴額實在太荒僻,實在疼痛得令人無話可說。如果沒有那一粒射向堂姐胸膛的子彈,那么眾人就不會逃離巴額;如果滿叔死心塌地在別的村寨做個泥腿子,那么他就不再回到巴額;如果滿叔不回到巴額,那么他就不會和雄黃礦搭上關系死于非命。阿萬最后對我說,千如果萬如果,如果我們不是生在巴額,而是生在北京上海就什么都好了。
我能說什么呢?事實是,這話是我先前對阿萬說的,現在只不過是他重復了一遍。
我們再次沉默下來。身下的水塘青綠青綠的,不時有青蛙跳上水藻鼓起肚皮呱呱地叫,頭上的碧空白云倒映在水面上,天上風卷云涌,水塘也風云激蕩。而我和阿萬的目光卻被阻隔,無法翻越面前的重重高山望到北京上海。我們的目光抬高是巴額的目光,落下也是巴額的目光,目光之中盡是巴額的柑橘桃樹拐爪樹李子樹,還有那風來風掃地、月來月點燈的吊腳樓,那層層鋪向天邊的梯田,和那爬上山崗在風中搖曳的野草……
我們憧憬山外,渴望彎彎曲曲伸向街市的黃泥小路走來一個來自遠方的人。我們很想知道這些見過大世面的人到底長一副什么了不得的容貌,穿一身多么光鮮的衣服,講一口什么驚天動地的話。
這是我們天天期盼的事情。而大水塘就是我們翹首等待山外來客最好的高臺。
可以想象得到,每天爬上大水塘的我們等來的都是失望。從頭至尾,走在黃泥小路上的都是附近村寨的人,他們和我的長輩一樣,身著廉價的攤販衣褲,或空手緊走慢走,或肩挑背扛日常家用,或大聲交談,或一言不發走向村口通向山坳的岔路,樣子都不像我們等待的人。
終于有一天,野草已經沒過腳踝的黃泥路走來了兩個異樣的人,他們腳踏皮鞋,頭發梳得光整光整的,胳肢窩下夾著烏黑的公文包,樣子抵近我想象之中的山外來客,但又感覺哪里不對勁。當時,我和阿萬已經從大水塘上爬下來,等了大半天,路上都沒出現個人影,我們已經沒有耐心再等下去。這兩個人的到來我們一絲察覺都沒有,似乎他們是偷偷摸進寨子生怕驚動我們。
那兩個人走近寨子時我正和幾個伙伴在曬臺上打少林拳。我們一個跟一個捉對廝殺,一下子擊出黑虎偷心,一下子打出迎門鐵扇,一下子甩出降龍十八掌,叫喊聲此起彼伏好似血戰沙場。八哥眼尖,見到這兩個人不是牽牛拉馬的莊稼人,叫起來,快跑,抓超生的人來了!我們撒開腿一哄而散,有的爬到枝葉茂密的樹上,有的鉆進厚厚的草垛里,有的跑進臭氣熏天的牛圈,我則躲進了米倉。米倉木板厚實黑暗悶熱,我能聽到那四只皮鞋踏進我家的吊腳樓,但聽不到堂屋上父親母親和那兩個抓超生的說了些什么。等我醒來已經躺在母親的懷里,原來我在米倉里睡著了。我問母親那兩個人來我們家干什么?母親說他們是我父親以前在部隊的戰友,他們是來我們家玩的。
第二天,八哥告訴我那兩個人不是父親的什么戰友,我是個超生兒,他們是來把我抓到鄉里去的。我膽戰心驚跑到家,家里空空蕩蕩的,父親犁田去了,母親上山打柴,我撿起一根木棍削尖一頭在曬臺上走來走去,眼睛總是盯著通往村外的黃泥小路,每看見一個人我就趴下來朝他們瞄準,不過出現在小路上的人都是種田的,所以我嘴里沒有噴出憤怒的槍聲。八哥他們還在打著少林拳,少了我,他們感到不過癮,八哥走過來手還沒觸到我,我就揚起木棍說,你們玩的拳都是騙人的把戲,我的槍才有用,砰砰砰,一槍斃一個!八哥他們哈哈大笑說,你斃一個給我看看。我朝一個遠遠牽著羊的過路人放了一槍,過路人沒有倒下,他的羊卻昂起脖子咩咩叫,我說你看,羊中彈了。我又朝樹上的一只鳥放了一槍,那鳥拍拍翅膀飛走了,我說,你看,你看,鳥中彈了。八哥他們笑得更厲害了,我很惱火,操起木棍戳向八哥的大腿,八哥捂著傷處在地上滾,我說,你看看,你看看,八哥中彈了。
晚上,父親母親回到家,我舉起木棍對他們說,我已經準備好了槍,那兩個人還敢來抓我,我就斃了他們。母親把我拉入懷里,拿走木棍,說誰說要來抓你?不要聽別人胡說八道,那兩個干部真的是你父親的戰友,昨晚他們邊聊邊喝酒,喝到高興時還猜起了碼,碼聲響得可以震破屋上的瓦片。你父親老是輸,我還幫他喝了不少酒呢。母親怕我不相信,揭開酒缸說你看昨天還滿滿的酒現在已經不滿缸了。
我不相信母親的話,不僅是因為母親笑得很生硬,更因為那缸酒是八哥他們前天在我的允許下偷偷喝了幾勺。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我仍然舉起木棍在曬臺上走來走去,一見到有人在小路上露頭就趴下來瞇眼瞄準。阿萬八哥他們仍然在我身旁打著少林拳,八哥對我一槍之傷的怨恨已經消散,因為我又允許他偷喝了父親的酒。喝下酒后的八哥到了放牛的時間卻沒打開牛圈,他巴掌一拍說兄弟們練起來!練好了幫七弟打跑抓超生的干部!一時間曬臺上拳光腿影吆五喝六,熱鬧得不得了。
出事的那天,藍天一碧如洗,根本看不出到了傍晚會下起瓢潑大雨。到了太陽爬上我家屋頂之后,母親說的父親的兩個戰友來了,他們身后還跟著一幫身強體壯的家伙。這一次是阿萬先發現了他們,我趴在草叢里睡著了。迷迷糊糊中阿萬叫了一聲抓七哥的人來了!我睜開眼,看到的不是八哥帶領伙伴們沖下曬臺和那幫家伙拼命,他們還是像前次那樣,有的爬到樹上,有的鉆進草垛,有的跑進牛圈。我嚇破了膽,腳底生風也跑進了牛圈里,透過木板的縫隙,我看到一個家伙拿起長長的竹竿要捅我家的瓦片,三四個家伙追著我家的雞,屋里屋外一地雞毛。
父親跺起腳連連說,我賠,我賠,我用豬來賠你們不行嗎!
很快,五六個家伙跳進了我家的豬圈,我看不到他們怎么抓到了豬,但是聽到豬在嚎叫。我還聽到母親在哭,聽到她說,什么鬼賒銷,以后就算是白送打死我也不要!
現在你才賠,便宜你了!那幫抓豬的人說。
沒多久,黃泥小路上一路響起我家的豬尖利的嚎叫,漸漸的,嚎叫漸漸響遠,最后什么都聽不到了。
這一天我才知道,原來這些人不是來抓超生的,而是來逼交賒銷款的,原先我家跟鄉里賒了一些蚊帳、鋪蓋、糧油,交款的日子早已過了好幾年,父親一直沒有還上這筆賬,那兩個干部催款不成,就叫上了工作隊的人沖進了巴額。
我還能說什么呢?我渴盼山外來客,最后等到的卻是這種結果,這讓我黯然神傷,讓我不知如何收拾內心的兵荒馬亂。經此一劫,那口大水塘后來我仍然是一如既往地爬上去,只是在拉長的目光里,一絲細若毛發的驚悸仍然暗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都還能翻撿出它的痕跡。
多年以后,阿萬家和我家最后還是選擇搬離巴額,在鄉里新起了樓房。巴額徹底人去樓空,再也沒有一戶人家在那里居住了,唯剩屋舍傾頹,荒草瘋長。如今我遠在他鄉,只能常常騎上夢中的馬背返回巴額。而我夢里的物事總是光怪陸離,總是透射出草野的闃曠以及已然消逝但卻固執常在的離人影蹤。那些亡人,那些翹望,那些疼痛,誰能開出一味藥幫我將之淡忘,甚或拋卻?
只要肉身不死,必將還有回鄉夢。
只要還有夢,夢中奔騰的馬必將翻山越嶺返回巴額。
責任編輯 侯 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