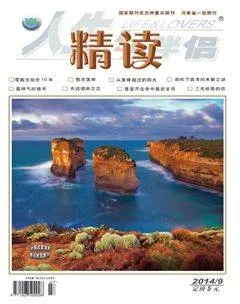三毛給我的信
徐靜波
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間新聞突然播出一條消息:臺灣女作家三毛在臺北自殺身亡。我當時正躺在床上,聽到這一消息,如觸電般地跳了起來。1991年1月4日,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兩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殺前給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裝著的不是賀年卡而是一枚禮卡,上書三個字:謝謝你。郵戳是1990年12月29日。
和三毛相識,是在1987年春天。當時,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我為三毛的才學所傾倒,也為她浪跡天涯的動人故事所迷戀。于是寫了一篇評論《撒哈拉故事》的文章,發表在一本文學雜志上。文章后來托三毛在中國內地的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帶給了她。一個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來信,里面還夾了一枚她簽名的個人照。三毛在信中說,她是第一次讀到大陸有關她的評論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聯系。未了,她還寫了自己在臺北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開始。
當時,三毛的書在中國內地已呈“洛陽紙貴”之勢,年輕人幾乎是人手一冊。但是,在大陸出版的書,大多是盜版,三毛一分錢的稿費都沒有拿到。當年5月,三毛給我發來一份委托書,委托我作為她在中國內地的代理人,與各出版社進行交涉。記得當時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調查中國幾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況。結果,詢問信發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沒把我這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黃毛當回事。我著急,三毛卻寫信勸我“不急,不急”。
仲夏的一個深夜,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拿起話筒,只聽到那邊傳來急促的聲音:“弟弟,我快死了。”細問是誰,回答說:“是我,三毛,是三姐呀!”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電話,第一次聽到對方的聲音。三毛那一口臺灣國語,帶著很重很尖的童音,幾乎使人感覺不出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當時臺灣與大陸要通電話,很不容易,弄不好會被當成“國特”。
我以為她病了,但是三毛告訴我,她正在閉門造車,為寫《我的寶貝》已經七天七夜只喝水與吃餅干,沒有碰過米飯。“好可憐的女人。”我當時心里這么想。
我的孩子出生后,三毛為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夠成為一面旗幟。三毛還特地在臺灣定做了一把金鎖送給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進入1988年,臺灣和大陸的關系處于緩和狀態,我極力鼓勵三毛回大陸探親。三毛開始時還心有顧慮,擔心會不會被大陸拘留,因為她的爺爺是“地主”。我把三毛的這—顧慮轉告給了國家有關部門,部門領導說:“歡迎她回來,一切接待與安全,均由我們負責。”我把這話傳給三毛后,三毛說:“我不需要大陸接待,能讓我自由地走就行。”
過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計劃在4月份回大陸,名義是給爺爺掃墓。交代我辦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陸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實在舟山老家的掃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爭取叫出版社付稿費。
在三毛接近來大陸的日子里,單位領導說: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于是,我不用上班,到處出差,落實接待。
1989年4月份,三毛從香港抵達上海,然后先去看了張樂平先生,因為張老畫了漫畫《三毛流浪記》,讓原名叫“陳平”的三毛有了自己的可愛筆名。接下來,三毛去了蘇州,游歷了當時大陸人還不知道的“周莊”,還蹲在油菜花的田野里哭了一頓。
三毛的爺爺是舟山人,從小在上海做生意,有一點錢,還在家鄉小沙辦了小學。后來因為成了“地主”,在50年代,作為清算對象,遺體還被挖出來暴曬數天。其實,三毛爺爺的墳墓已經找不到了,當地的親戚在大概的位置,趕在三毛到來之前重新修建了一座空墳。
去小沙之前,三毛囑咐我準備兩樣東西,其一是一個小盒子,準備裝一點爺爺墳頭的土。另外準備一個瓶子,裝一瓶老家的井水,帶給在臺灣的爸爸媽媽。
好在老房子還在,祖宗祠堂也在,讓這一次祭祖的活動搞得很體面。當時,我特地請浙江龍泉寶劍廠為三毛打制了一把寶劍,據說與當時的國防部長張愛萍先生的那一把是姊妹劍。
三毛在來大陸之前,把自己的所有病歷單全部寄給了我,委托我安排在杭州為她治病。我找到了當時擔任農工民主黨浙江省委社會服務部部長的著名內科醫生林抗生先生。林先生看了病歷,說三毛是百病皆有。于是他組織了杭州最有名的醫生成立了一個專家小組,在花家山賓館為她診斷治療。三毛自己拉下衣領,露出脖子上周圍紅紅點點,說:“我患有淋巴癌,一直沒有治好。”
三毛在大陸幾次旅行,我大都陪著她走。她身體其實極差,有時一天要昏倒好幾次,在拉薩的那一次,差一點走了。
(摘自《燕趙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