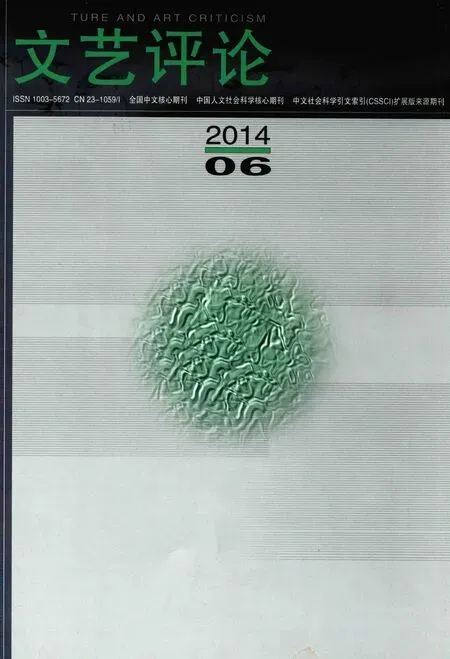漢初的文化整合與《說苑》雜記的文體功能
李翠葉
雜記作為知識整理的文本形式,不始于劉向,而是從戰國時期進行個人著述的諸子興起。諸子廣采各類言行事語作為知識儲備,如韓非子的《內儲說》、《外儲說》等,但是這些文本并不具備文體形態。西漢劉向輯錄了西漢以前經史系統中以事語為主體的各種經史傳說,編成《說苑》和《新序》兩書,才正式有了筆記體專書,為后世的筆記散文集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先秦時期各種經史傳說文獻是文人共有的知識形態,因此在漢前的典籍中,由于諸子將其作為知識要素使用,我們常看到傳記材料互見的情況。這種情況展現的是一個時代共有的知識要素在公共文化傳播中的文本形態。至于漢初,對這些早期文獻的序次不僅僅是諸子將其作為個人的知識儲備,它涉及到新時代下的雜記發揮怎樣的文體功能以不斷地建立傳統和激發創新,從而展現一條知識觀念與文體文獻相互影響、交錯發展的路徑。本文將從漢初知識學術形態的整理傳承為角度,考察雜記類文獻的文體形態與文體功能。
一、漢初序、次和新知識體系的形成
序次,是一個文化整理的過程。漢人的學術建構,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對古文獻的整理序次。呂思勉:“漢人所述,辭義古者,實亦與先秦之書,不相上下……故書雖成于漢世,說實本于先秦;又先秦人書,率至漢世,始著竹帛,其辭亦未必非漢人所為,或有所潤飾也……其書多引古事,與各種古書相出入,足資參證。劉向之《新序》、《說苑》、《列女傳》,專于稱述行事,取資處更多矣。”①漢初書籍在文體上的特點就是述古事。漢初,陸賈作《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②觀其內容,均為整理舊有傳說記,而以“新語”為名,在于作者是具有選擇性的一種整理。漢初諸儒大量征用先秦的知識要素,一則保證了源自先秦的知識體系脈絡不斷,二則保證了建立在先秦時期的觀念品格的傳承。
既言序次、編述,就不是紛然的雜錄。今考《漢書》各傳,漢初對成書所用詞語共有“序次”、“著”、“撰”三種形式,可以看出時人對知識體系的整理在文獻形式的反映。漢對先秦書籍進行序次整理的,如“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③由八十二家,而編選為三十五家,所言“序次”者,其中有選編取舍的工作,其中也許有雖用古文獻詞語而合并整合出新篇的工作。這種工作,實際是劉向校勘工作的先聲。漢人的序次是對先秦知識體系的整理,代表著對文化的自我抉擇。尤其劉向的官方姿態,更代表著漢人對思想準則的自覺整理。而先秦百家傳記中所包含的道理也因劉向的定本,廣為傳閱,必然使這些古傳記再次具備對漢人思想意識的規整。
然而,更重要的是,漢人在序次這些古代典籍時所伴隨而產生的文學觀念,以及序次的多種形式可能形成的新的文體體例,也就是古傳記與漢初雜記文獻形態之間的聯系。在我們了解了漢初的文化現象之后,要進一步看,“序次”在哪些方面改造了古傳記,也就是新朝是如何消化舊有的知識體系的?
二、古傳記向《說苑》體例的轉化
西漢前期的經史傳說,因學派傳承的原因,多為事語類文獻,如當年孔子與時人議政論政的問答、春秋戰國年間君臣賢士大夫的問答等,都有當時的教學背景和政治背景。至于漢初,劉向則將其歸為“政理”、“臣術”,這實際上體現了古傳記逐漸模糊了早期政治活動背景而以義理的形式存在。曾鞏作《說苑序》:“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之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孔子言論的精微之處,孔子言論背后的義理體系,在劉向的整理之下,才初步突顯出來。使漢前散落在歷史中的事語材料,開始有個基本的歸旨。這說明,先秦知識形態在新的時代下不斷獲得一種意義和價值取向。
《漢書·杜欽傳》中記載建始四年漢成帝在《白虎殿策方正直言》:“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④天地之道、王者之法、六經之法和人倫規范,就是漢人真正關注的“義理”。漢人最大的貢獻,在于從這個“義理”的高度上整理百家傳記,以期建構漢代此時的知識體系和人道法則。這一時代精神對整個漢初文學風尚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比如《五經正義》的產生和漢初文人淹貫六經的學識修養的形成等。
劉向編選《說苑》的義理指歸,一本于儒家。首先表現在材料的選取上,如《說苑·雜言》: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于人乎。⑤
在《莊子》達生篇中也有這則故事的框架,但主旨完全不同。“達生”篇旨在于宣揚人與自然之間物我兩忘后所達到的境界。而在《孔子家語·致思》中,和《說苑》此章相同。可見這個故事有兩個傳說系統。
《漢志》將《說苑》列為儒家類,正因其有述圣之意。劉向的另一部著作《新序》亦然。石光瑛《新序校釋》在評論《雜事》篇言:“開章明義,以孝為先。繼又由孝而推論仁道。傳曰,孝弟為仁之本,豈不然乎。由此觀之,編次之本意,隱則乎《論語》,非茍焉已也。”⑥指出儒家義理不但影響材料取舍,還會反映在編述體例上。
《說苑》編選的價值,就在于將義理變成一種體例,即“篇名”的確立和“總論”體例的形成。《說苑》共二十篇:《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反質》。每篇下所雜錄的古傳記,本無名稱,更無類聚、群分的文獻形態。劉向于古傳記中取大義相近者,類聚而群分,立篇名以統率古傳記,這個編選工作是龐大的。是劉向所說的“一一條別篇目”。將篇名作為“義理”來統率材料,這時,材料就變成了各個時代的“事語”對篇名的詮釋或注解。
“總論”的體例,只有《君道》一篇沒有,其它每篇篇名之下,均撰寫一段議論性的文字,然后再序次百家傳記材料。總論的寫法:第一,博采傳記中有微言精義者,整合以成己論。如《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陭,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⑦第二,自我從博采的各類傳記中提煉以成己言。如《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茍合,位不茍尊,必有益于國,必有補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⑧。第三,有論點、論據,有論證,其文本本身就是劉向的議論文。這樣的議論文,是可以脫離雜記材料,自成一篇的。如《立節》篇旨。這種總論的方式,設在每篇之下,起一個閱讀古傳記前進行思維指向的作用。劉向所創造的這種序次體例,使漢之讀者,每習一篇,則知古傳記之大義,則傳記之大義因篇名、總論而得以大揭。
另外,劉向在一篇之下更造新事。這是以義理來品評當代了。這個開端是漢代核心價值體系開始確立的標志。如在《建本》篇中,載新朝河間獻王事。“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榖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⑨是錄河間獻王語以為新事。儒家之所以能成為漢代的思想基礎,在選拔制度等外,還在于文獻的傳播對萬民的導向。儒家的義理和思維是伴隨著篇名、文體的確立而滲透到漢代文獻中,進入到知識體系的傳播中。
劉向的古記新作,采百家傳記,以類相從,主要通過分類歸總、篇題確立、撰寫小序的形式,發揮序次整理的文體功能,其中以義理為“篇題”的形式,使戰國的傳記材料走向一種新的義理匯總。這種創造性的雜記,傳播著新穎的信息,呈現出新的價值理念,前代思想觀念既得到穩定的傳承,其中又蘊含著變革性的內容,成為新王朝的知識平臺和文化出發點。
劉向《說苑》為標志的這類雜記文獻,作為知識的儲備,不得不謂善矣。社會的文化觀念和思想文化,必有所托才能傳承,作為知識素材的傳承,是民族共同的語言平臺。如均為“論”,則沒有知識之承繼,和后人之論的生發點了,這就是雜記的重要性。而在序次當中通過篇題、小序等方式所融合的深刻的寓義,關注現實進行材料的取舍,實際上又是論的特殊形式。劉向的《說苑》、《新序》之書,在記與論之間平衡,對于漢代文人而言,大可為思想觀念、人文規范的知識儲備。這類書籍,遠比議論類的文章更能帶動天下之望,它以官方文化的姿態確立了一個時代共有的話語體系。
三、經學傳記與《說苑》的具體編次
將《說苑》的材料和《孔子家語》、《韓詩外傳》、《列子》等相互比對,會發現大部分材料字句略有調整,說明古傳記“事語體”的基本形態已經定型,是廣為流傳的一種知識樣態。
從文辭角度看,對古傳記進行文辭潤色,從傳記產生開始,到諸子應用,再到漢代劉向的選編,一直未有停止。如“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的故事,最早定型的時間應在戰國時期,之后《韓非子·說林》征用,語句略有不同,而在《淮南子·人間訓》中,這則故事描寫得就更為生動了。這是古傳記在文辭潤色上的表現。但,劉向在文辭上所作的修繕,整體上大不如《孔子家語》中的材料,甚至在很多文意方面,劉向的更改都不甚妥,如《孔子家語·辯政》“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劉向改為“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文意反而不順。而劉向對于《說苑》編選的功勞,主要在于:
1.以篇題取舍古記字句
《孔子家語·六本》: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聽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⑩
《說苑·敬慎》: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11)
《孔子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有兩層內涵,第一層,羅者言:“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孔子推論言:“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第二層,羅者言:“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推論言:“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至于《說苑》則將第一層的內容刪掉,而只保留了“君子慎其所從”以照應篇題《敬慎》。
又如《孔子家語·正論解》記載:“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作崇……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而在《說苑·君道》對這一故事的記載為:“楚昭王有疾……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12)家語的寫作重點在于保留孔子對一件事情的所有言論,因此家語中有“孔子曰,又曰”,保留了孔子當時的所有語錄。而在《說苑》中,因“君道”義理的確立,而刪去了其中的一條。
2.以己意改動字句
《孔子家語·六本》:子路問于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兒寡,為內私婿,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后雖欲悔,難哉!(13)
《說苑·建本》改為“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14)原文的“讓則讓矣”,是說“讓是讓了,然而是不符合禮義的讓”而劉向認為這也是一種忠。
又如劉向將《孔子家語·政理》“仲尼見宋君”中“崇道貴德,則圣人自來”,改為“善為刑罰,則圣人自來。”(15)劉向認為以道、德著稱的圣人時代已經遠去,今天的圣人只要善用刑罰則可召致。又如劉向會去掉孔子言談中柔弱的部分。《孔子家語·致思》“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劉向在《政理》中去掉了“愛而恕”、“溫而斷”,而強調恭敬寬正廉潔。將字句改成“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16)又如劉向會將一篇之中談話前后的排列順序更改,《孔子家語》講三君問政于孔子,《說苑·政理》則將三個談話片段調整次序,先言政在懷近而來遠,次言政在諭臣,最后言政在于節用。在這些言語改動中,可以征見劉向的政治思想。
3.主動對傳記進行評議,突出義理
《孔子家語·六本》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欣然而起……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17)
《說苑·建本》在“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后,加入自己的評議“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18)這種感嘆式的評價又一次強調了文中的義理。
又如:《孔子家語·致思》:“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的故事,《說苑》在故事結束后加入劉向評價孔子的話:“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19)又如“楚恭王出游亡弓”,《說苑》在事情結束后,評議“仲尼所謂大公也。”再如《孔子家語》中,孔子為魯司寇時,斷案必遍問眾人,然后言“當從某子”。《說苑》在這段結束后,加上了自己的議論“憑著孔子的智慧,難道一定要等待某某人的意見,然后才知道如何裁斷嗎?”這樣的引申對文義并沒有改變,只是起一個強調的作用。這就是《四庫總目提要》中所說的:“舉經文,而下己意以申戒之”。
4.進一步闡釋,使經義更完滿
《孔子家語·六本》“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一段,并未對《損》、《益》作解釋。而劉向在其中則加入了自己對盈、虛,損、益的看法。而且將故事敘述完后,又用“是非損益之徵與?”來總結,最后加入自己的評論:“所以說,謙虛,是用恭敬來保存自身地位的。‘豐’卦說趁著中午時分行動,那時候陽關明亮,所以就宏大,如果已經達到了宏大的程度就開始虧減。我們要引以為戒”。劉向對這些古記材料的編寫,雖有闡釋和改寫,但并不會在整體上影響義理指向。
5.材料中具有多重義理指向的,劉向的更改會突出其中的一層義理
《孔子家語·好生》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20)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各種不良社會思潮和負面信息迅速傳播,使得思政課的教學受到嚴重沖擊[2]。通過與醫學院校宣傳人員和學生座談發現,學校大部分只通過官網和官方微信公眾號發送信息,并且更新內容較官方,形式較單一。仍有30%的學生不清楚學校有沒有網絡思政教育。由此可見,加大網絡思政教育宣傳力度勢在必行。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21)
在《孔子家語》中孔子評價漆雕子的善談與明智。“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劉向的更改是,將“孰克如此”這句話去掉,將評價漆雕子明智的話“智而不能及”改為“智不能及,明不能見”,整個意思就變成:“所以那些智慧達不到,眼光看不遠的人,能不多次占卜嗎?”這就是評價孺子容了。
6.在每篇的編選上注意統合首尾
《說苑·復恩》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家見公之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22)
《左傳·宣公四年》也記載有此事,而在《復恩》章中,最后用子夏語:“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來作總結。
由以上所論,劉向在《說苑》中所作的工作,第一,改編古傳記。第二,更造新事。第三,定篇名以統合古傳記。第四,統合首尾、編次材料。《漢書·楚元王傳》:“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規覽,補遺缺。”(23)董其昌《劉向說苑序》:“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于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覩聽者,是為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后,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余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入儒家,是為述圣,可傳也。”(24)劉向整理的目的,也正在于教化眾民。文章與時高下,所謂編選序次者,古記新作也。
劉向雜記類作品的性質,就在于采摭群言,總文理、統首尾,雜而不越,在經與論之間平衡。《漢志·諸子略》儒家類:“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即劉向的《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共四部著作。《說苑》與前期諸子對古傳記材料使用的不同在于,以雜錄的形式廣收傳記,改變諸子將傳記材料作為論據的形式,既體現“雜記”體廣泛收錄的性質,又有序次的內涵。它不是當年諸子一家的知識儲備,而是漢人可以持中評議的話語根基。
綜上所述,在先秦諸子時代,首次形成各種雜記文本作為諸子的知識儲備,形成戰國諸子新的觀念體系。而至于兩漢雜記文體的確立,則意味著創自周代的禮學知識、戰國新型的價值觀念再一次經過編纂序次的建構,逐漸獲得一種意義和價值取向,并延展為漢代政論散文中文人所共同遵循的觀念品格。可見,雜記是一個可以不斷被應用的文體形式,自始至終參與著對文化的傳承與構建。
①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③④(23)班固《漢書》,中華書局 1960 年版,第 1388、3673、1957頁。
⑤⑦⑧⑨(11)(12)(14)(15)(16)(18)(19)(21)(22)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 年 版 , 第 427、56、34、73、261、23、71、153、163、61、171、335、141 頁。
⑥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頁。
⑩(13)(17)(20)王國軒、王秀梅注《孔子家語》,中華書局 2011 年版,第 188、191、192、115 頁。
(24)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卷二百九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2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