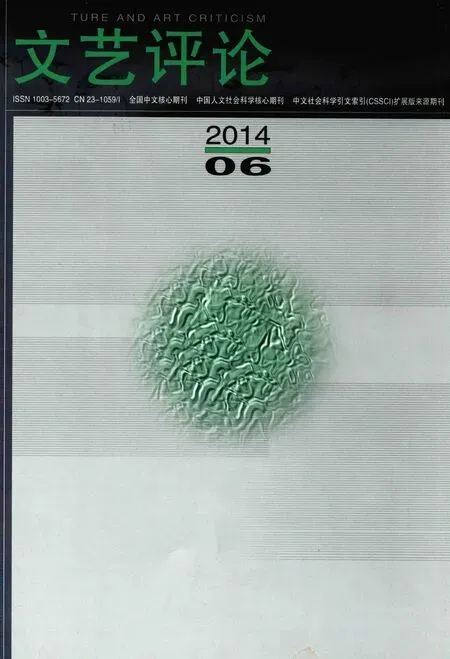秦族源、早期秦文化與秦文學的萌芽
劉 原
一、秦人早期歷史與殷商文化的關系
目前只能依據《史記·秦本紀》來對秦人的祖先和他們的早期歷史來進行認識,司馬遷是這樣述說這段歷史的:“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①秦人的始祖神話與夏、商、周的始祖神話有著相似之處,都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親是因為受到神異而感生后代。秦的后人如此追溯其祖先世系,也可以說明秦人與夏、商、周人一樣也是中華大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這種說法得到了在陜西鳳翔縣南指揮村的秦公大墓中發掘出土的石磬銘文的證實,銘文中說:“天子匽喜,龔(共)桓是嗣,高陽又(有)靈,四方以鼏(宓)平。”②其中的“高陽”是顓頊帝,而秦人稱高陽是自己的先祖。
又據《史記·秦本紀》中載: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后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③
大業之子伯益因為舜帝調教鳥獸有功而被賜姓為嬴,并且把費地(今天的曲阜附近)封給他,從此,自成一族,史稱“嬴秦”。關于“嬴”姓的問題,劉節在《釋嬴》一文中這樣說:“文公六年賈季曰:辰嬴嬖于二君。杜預云:辰嬴,懷嬴。……而燕、嬴,實為同類雙聲。”④可知,嬴姓既是燕姓。在《呂氏春秋·仲春記》中載高誘注曰:“玄鳥,燕也”,⑤燕就是玄鳥,林劍鳴先生認為,殷人和秦人崇拜同樣的圖騰—“玄鳥”,而原始先人有一種習俗,就是把祖先崇拜的圖騰名稱作為自己的姓。因此,可從信仰方面將“玄鳥”考證為他們的祖先。⑥在《史記·殷本紀》中這樣記載殷人祖先的傳說:“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⑦在《史記·秦本紀》中也記載秦人的先祖說,其曰:“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⑧可見,秦與殷一樣,是源于位于我國東方,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部落。王洪軍指出《封禪書》中所載秦文公建祠以祀得雉鳴之瑞,而《史記·殷本紀》中也記載了殷帝武丁被野雉之鳴所驚動,因為玄鳥生商的歷史原因,在殷人的心中“野雉鼎鳴代表著上天意志,也代表著祖先神諭,所以武丁驚恐萬狀。秦人先祖和商人祖先都對鳥的光臨表達了崇高禮敬,反映他們文化心理和宗教趨向的一致性”。⑨從實際的生產生活本身來看,“殷人早先本是以狩獵、牧畜為主的游牧氏族……秦人祖先也是以游牧、狩獵為其經濟生活主要內容的……”⑩可知秦人與殷人一樣以狩獵、游牧生活為主。再從墓葬習俗來看,據林劍鳴先生考證,“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墓葬,與殷商時期墓葬有不少相關之處,例如殷制天子墓為亞字形,諸侯墓為中字形,有嚴格等級界限。而在陜西省鳳翔南指揮發現的秦公大墓,……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而絕無亞字形墓。這表明秦國陵墓形式仍遵循著殷制,秦公僅以諸侯自居,而不敢潛越。……其它象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與殷墓也有驚人的類似之處。”(11)這也證明了秦人對殷商文化有著明顯的繼承,秦人與殷人一樣都來自于東方。
2008年7月入藏清華大學的戰國竹簡中有一種保存良好的史書,整理者將之暫題名為《系年》,內容是對周武王伐紂一直到戰國前期史事的記錄。李學勤先生在整理過程中經研究發現,在《系年》篇中,存有許多對傳世史籍進行修正或者補充的材料,其中就有關于秦人是自東方遷來的商奄之民的記載。“清華簡《系年》的第二章,……簡文敘述了周武王死后發現三監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飛(廉)東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殺飛(廉),西遷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飛’就是飛廉,‘商盍(葢)氏’即《墨子·耕柱篇》、《韓非子·說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稱作‘商奄’的奄”。他還說道:“由《系年》簡文知道,商朝覆滅之后,飛廉由商都向東,逃奔商奄。奄國等嬴姓東方國族的反周,飛廉肯定起了促動的作用。亂事失敗以后,周朝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治‘商奄之民’,同時據《尚書序》講,把奄君遷往蒲姑,估計是看管起來。但在《系年》發現以前,沒有人曉得,還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強迫西遷,而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這真是令人驚異的事。”(12)《系年》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嬴秦與少皞、顓頊確屬于同一族群的證據,王洪軍認為《清華簡·系年》的發現,為“秦族東來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文獻支撐,解決了秦人族源及禮俗等問題,其中所說的“秦先人”是被周人遷徙至甘陜一帶的商蓋(商奄),女防和他的商奄之民。(13)所以,《史記·秦本紀》中所載秦人是以自稱是顓頊之后,并不是東方諸侯所鄙薄的戎、狄異族,而是華夏一族,也是真實的。在《史記·秦本紀》中還記載了,大費之子孫輔佐殷國,“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14)我們可以看出,從商湯伐桀開始,秦人的祖先在渭水中游捍衛著殷王朝的西部邊疆,這其中也應該存在著一定的民族使命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戰國時期被中原國家視為“秦戎”的秦人,有著強烈的“中國”意識。《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穆公與由余的一段對話,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秦統治者思想中的這種“中國”意識: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15)
秦穆公面對戎使自稱“中國”,就是已經把秦國放在了華夏的范圍內,以自別于“戎夷”。后來的幾代秦國統治者的思想一直存在這種意識。秦人自認為是華夏一族,那么他們自然也和其他諸侯國一樣對作為天下政治、文化核心的周王室有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春秋初年,秦襄公率秦兵護衛平王東遷;據《左傳》記載,秦穆公十一年,“秦、晉伐戎以救周”;秦穆公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秦國的這些行為,得到了來自周王室的封賞和認可,而這正是秦立國的政治基礎。立國以后,秦人也在努力維護與周王室的良好關系,其在文化上也極力向周文化靠攏,可以說,在秦國由弱小而壯大的過程中,一直從周文化中汲取著豐富的營養。
二、嬴秦與戎狄之間的淵源
由上述史料可知,從商王朝時開始,嬴姓秦先祖被遷徙至西方戎狄林立之地,并承擔了為殷商“保西垂”的重任,開始了與戎狄雜居的經歷。最初,他們與戎狄部族友好相處互不侵犯。在與戎狄的雜處、交流中,秦人學會了戎狄以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民族推翻了殷商王朝的統治,并以周王朝取而代之,商王朝覆亡,嬴姓秦先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打擊。周武王去世后,殷商舊主的兒子武庚聯合了包括秦人在內的東方各氏族和諸侯國發動了大規模的叛亂。周公旦平息叛亂后,嚴懲了參與叛亂的人,并強迫遷出原住地。秦人被強制遷往各地,其中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遷入了西方邊陲。秦人在西部惡劣艱難的自然環境之下繁衍生息,求得生存,過著游牧生活,養馬成為了他們的特長。據《史記·秦本紀》中載,周穆王時期,秦人造父被封為“御”,為周穆王駕車;西周末年,孝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日漸衰敗,秦的地位卻變得越來越重要,秦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惡來之后,因非子為周孝王蓄養馬匹,而立功,于是,周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16)據史料記載,非子于今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秦亭一帶建造秦邑,(17)由于秦邑之地遍居中戎狄,所以,秦人與戎狄部族之間必然發生往來。從此,嬴姓氏族才真正定居于秦,“秦”這個名稱才真正登上歷史舞臺。由于長期處于偏遠的西北部,長期的游牧生活以及與戎狄的交往也給予秦人粗獷、豪放的性格。西部惡劣的自然條件,成就了他們的強悍、勇敢、豪放的作風,培養了他們極強的與自然搏斗的能力,從而形成了好戰尚武的精神品格。
俞偉超先生曾指出:“秦國的文化,最遲從西周晚期以后,也許就從西周中期穆王時的‘造父’開始,就受到了周文化的強烈影響;但秦人在很長的時間內仍保留了她自身的文化特征。這種特征,據現有資料,至少知道有三點是很突出的:一點是盛行蜷屈特甚的屈肢葬,蜷屈程度就跟甘肅永靖的辛店墓一樣……秦人和永靖的辛店墓都流行極為相似的屈肢葬,正表明了族源上的密切關系,即都是戎人的一支。第二點是秦人在其根據地,即汧、渭之間的寶雞和甘肅東部一帶,直到戰國時代還使用一種雙耳高領袋足鬲,其特征是足端扁平,過去蘇秉琦先生叫做‘鏟形袋足鬲’。這種‘鏟形袋足’也是甘肅辛店文化陶鬲中所特有的,而周文化本身的陶鬲,足端則是尖的,二者即使其它外形相似,足尖的形態卻明顯地不同……這種遺存同卡約、寺洼、安國式、唐汪式、辛店這個系統的文化,存在著親密的血緣關系……秦人不斷使用具有‘戎式鬲’作風的陶鬲,至少暗示了秦人和戎人的長期密切關系,而這是有歷史上的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第三是洞室墓。在黃河中、下游,無論是仰韶、龍山、二里頭、二里崗以及殷墟、周原等地的商、周文化,都沒有洞室墓的傳統,而是一種豎穴土坑墓。但洞室墓在甘青地區起源很早。在陜西地區,東周的秦墓也流行洞室墓。那些秦墓,除了豎穴墓以外,橫穴和豎穴的洞室墓都很多,這顯然同羌戎系統的文化有聯系,說明了秦人的文化傳統,同羌人是有特殊關系的”。(18)俞先生關于秦人族源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有誤,但是他關于西周文化對秦國文化的影響的論述,確是中肯的。俞先生認為,秦人最遲從西周晚期以后,開始受到周文化強烈影響,并且秦人在一定時間內仍保留著自身的文化特征。并且對考古資料進行考證的結果也可說明,秦人在與西戎的不斷接觸中的確吸收了戎狄的異族文化,并與周文化相融合,形成的秦族自身的文化特征,即以粗獷豪放的性格、強悍勇敢的作風、好戰尚武的精神品格為內容的嬴秦精神。
三、周文化對早期秦文化的影響及秦文學的萌芽
從非子封于秦邑后,其子孫一直在此安居,但是,在曾孫秦仲統治的時候,秦地的周邊形勢發生改變。據《史記·秦本紀》中記載: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地西犬丘,生子三人,……襄公為太子。(19)
從上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秦仲三年,西戎打敗了秦人的先祖大駱留在犬丘的其他分支后裔,并占領這片土地長達二十余年。其間,秦、戎雙方進行了長久而慘烈的戰爭,在秦仲戰死后,由其長子秦莊公最終戰勝了西戎。周宣王隨后封莊公為西垂大夫,并將秦和犬丘兩地封給他。莊公選擇居于犬丘,秦族的活動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犬丘地區。秦莊公之子襄公也居犬丘,直到秦文公四年復又遷居“汧渭之會”。可見,從秦族自非子至秦文公早年,早期秦人主要在秦和隴上的西垂這兩個中心區域活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學者根據對于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園的發掘和西漢水上游的考古調查,已經確定早期秦人活動的中心地區就位于渭水上游的禮縣境內,與文獻記載的地址完全一致。而此處所屬的關中地區也正是周民族的崛起的地方。在1973年左右,在甘肅靈臺縣,有一批兩周墓葬出土,其中有屬于西周康王時期的姚家河西周墓和洞山墓,還有比西周中期更早的西嶺墓葬。(20)靈臺縣與禮縣相距不遠,位于黃土高原之南。可以說,在西周早期,秦族聚居地中已經能夠發現周文化蹤跡。趙化成在《甘肅東部秦和羌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中對秦文化的分布狀況進行了考證:
在甘肅東部,從總的地域范圍看,周、秦文化處在一種交錯分布的狀態下;從局部看,可能相對集中。如隴山以東的平涼、慶陽地區,……這里的“周代遺存”,主要的應當屬于周文化系統。……隴西西河灘遺址在今天水以西,這一地點如果像《甘肅文物考古三十年》中所講的那樣是屬于周文化系統的遺存,那么類似的遺址應當還有一定數量。這樣,以天水一帶為中心的秦文化遺存便處在東西兩面周文化的包圍之中。(21)
嬴秦族人必定會與周文化發生接觸,并且,就那時的周秦雙方文化狀況的差距來看,嬴秦文化的變化應該是由周文化的介入而引發的。再從《史記》中的記載看,當秦剛剛進行國家政權的建構時,西周作為宗主國,已經具有了成熟的國家政治結構和進步的思想意識,幅員遼闊的土地。秦人在政治上奉周王室為宗,接受其分封和支配。所以,初生的秦文化自然不可與深厚的周文化同日而語,對秦國來說,吸收先進而強勢的周文化是很自然的選擇。
上世紀80年代,在甘肅東部的毛家坪、董家坪地區,由北京大學考古系與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找到了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在毛家坪遺址共發掘出秦文化墓葬31座,屬于西周中晚時期的有12座墓葬,其墓壙都是長方形的豎穴土坑。主要有以陶器為隨葬品,其中包括最基本的組合為豆、罐、鬲、盆。其陶質、陶色雖與同時期的西周同類陶器有較大的差別,但陶器形態基本相似。墓中以屈肢葬為葬式,其中有八座蜷屈特征很重,骸骨頭部都朝向西方,這與同地發掘的其它19座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墓存在明顯的繼承。不僅如此,這些墓葬與在陜西關中發掘出的同類墓葬完全相同。因此,可將毛家坪西周時期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22)這些考古資料可說明:最晚,從西周中期開始,秦人就吸收了周文化,從而豐富了自身文化的內容。不過,從出土于毛家坪墓葬的器物上看,秦人還處于在物質文明的層面上,對周文化進行吸收。秦人在精神層面對周文化進行吸收,應該是在西周晚期開始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秦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殷商文化、戎狄異族文化和周文化的影響。秦在西周、春秋時,有著清晰的“中國”意識,在文化上也不斷的吸收周文化,同時由于長期地處西垂,戎狄異族文化在秦文化的形成、發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此時的秦文化具有以周文化因素為主而又剛勁、崇武、好勇的特征。
文化精神是文化系統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該文化區別于其它文化的本質要素。文化精神可以外化為文化主體的語言文字、習俗歷史、典章制度、宗教、藝術等。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部分,誕生于文化的母體,流淌著文化的血液。秦文學做為秦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秦文化精神的外化。因此,伴隨著秦文化逐漸形成的腳步,秦文學也正在萌芽。
在西周時期,秦人由在西初期對周文化的被動接受,到西周晚期對周文化的主動吸取,秦文化也進行了由對周文化在器物層面上模仿到對周文化在精神層面上模仿的轉變。從而使秦文化對周文化在精神層面上的模仿逐漸成了秦文化創作的源泉。在上海博物館以重金購回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區中流失海外的出土文物4鼎2簋,其中簋器與不其簋在形制上非常相似,但其銘文及其簡略,均謂:“秦公作寶簋”;鼎器銘文也很簡單:“秦公作鑄用鼎”、“秦公作寶用鼎”。(23)禮縣公安局繳獲的同地出土的二鼎一簋銘文也與之相類。大堡子山陵區目前探明的只有兩座大墓,又據《史記》,秦國君死后葬西垂的有秦莊公、襄公及文公,鼎、簋銘文既稱“秦公”,而“莊公”又是死后追謚,故其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文公。據簡報介紹,鼎、簋不但在器形上仿照周器,而且其所用的紋飾及其配合規律也襲自周器,如鼎飾中的竊曲紋配垂鱗紋,簋飾中的竊曲紋配瓦棱紋等。(24)另外,在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區還發現,從墓葬形制、規格以及隨葬品的類型、工藝來看,都能夠突出顯示秦人受周文化的巨大影響。這些可以表明此時秦人對周文化的吸收是以模仿來實現的。此時的銅器銘文中的“秦公作寶用鼎”這類的語句,明顯是仿自不其簋銘文中的“永寶用享”;而后來的秦子簋蓋銘“秉□受命屯(純)魯,義(宜)其士女,秦子之光,邵(昭)于聞亖(四)方,子 = 孫 =(子子孫孫),秦子姬甬(用)享”等,這種贊語都是對不其簋銘文中“用匄多福,眉壽無疆”的模仿。關于不其簋,陳夢家先生在《殷虛卜辭綜述》中說:“西周金文不其簋為秦人之器。”(25)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不其簋是秦人之器;二是指,此時秦人還在沿用西周的文字。據李學勤先生考證,“不其”就是秦莊公,不其簋在器形、紋飾方面與西周晚期的師酉簋很相像,這也可表明在秦莊公時期秦文化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精神上都沒有顯示出秦文化的獨特性。從不其簋的銘文的思想內容上來看,顯示出了秦文化對西周禮樂文化的繼承,《不其簋銘文》云: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伯)氏曰:“不其,馭方獫狁廣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女以我車宕伐獫狁于高陶,女多折首執訊。戎大同,(永)追女,女及戎大敦搏。女休,弗以我車圅(陷)于艱。女多禽,折首執訊。”白氏曰:“不其,女(小子),女肈誨于戎工。錫(賜)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里,用永乃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乍(作)朕皇祖公白(伯)、孟姬簋,用匄多福,眉壽無彊,永屯(純)霝冬(終),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26)
可見,銘文內容涉及周宣王時期秦莊公戰勝西戎的戰爭。記錄了不其隨伯氏戰勝獫猶后,伯氏在回朝向周王獻俘時,受到了周的嘉獎和賞賜;不其以鑄器刻銘的形式頌揚公伯和孟姬。在西周時期人們認識到了青銅文字的社會功能,把銘文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們用銘文記彰功烈,宣揚孝道,贊頌美德。馬承源先生對此總結說:“一是用以形成奴隸主貴族的權威。西周早期的貴族,都是滅商以前的宗族子弟或者小貴族,輔助文、武,伐商滅紂時有功于王室,隨著武王的軍事勝利,被分封受爵,成為大的權貴。他們把自己的功勞或父輩對王室的貢獻,以及周王的賜命鑄在青銅禮器上,就等于獲得了地位和職務的證件,具有護身符的作用。以便造成他們的權威。二是加強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周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周人維護其內部、鞏固和加強統治的一種手段。其核心就是嚴格的宗子法承襲關系。……他們在青銅器銘文和祭祀活動中,追訴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榮譽,都是為了加強自己在其宗族體系中的地位。”(27)從這一角度看,不其簋銘文正是對西周銅器銘文的模仿,可見,秦文學的發展正是從模仿周人起步的。
從不其簋銘所鐫內容來看,其中所述與《史記·秦本紀》中的記載的周宣王令秦仲和莊公抗擊西戎,并將他們封為西垂大夫的這段史實相吻合。而在秦國早期的文學作品中也有以此作為背景的詩篇,就是《秦風·無衣》,此詩以直白的文字描寫了戰前秦國的士兵們修整武器、擦亮鎧甲,以一種積極、旺盛的狀態準備投入戰斗。表現出了秦師出征的熱烈場面。秦地迫近戎狄之壤,在長期與戎狄的爭戰和接觸中,形成了驍勇善戰的精神和強悍的民風。此詩雖然文字簡單直白,但卻體現了秦人“尚氣力,先勇力,忘生輕死”(《詩集傳》)的民族特性。秦人以其簡單、直白的文字表達了向西周王室盡忠的決心和秦人驍勇善戰的精神風貌。
秦人從西陲蠻夷之地走來,對于秦人來說,入主中原不侵入式的過程,而是長久游離之后回歸,秦人時刻銘記自己的祖先是“華夏”一族。從早期秦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對周文化具有歸屬感的不自覺的吸收,也有對長期接觸的西戎一族文化的融合。在秦人對西周文化的吸收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秦人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所進行的模仿,這可反映出秦人對西周禮樂文化的認同,由單純的器物層面而滲入秦人的精神層面,但是,秦人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與吸收,而是在模仿中不自覺的融入了秦人長期地處西陲所形成獨特的民族精神。正是在秦人與西周文化的融合過程中,秦文學初步生成,與秦文化的形成一樣,在最初的對西周文字的模仿中,融入了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質。這就是以秦人精神為中心對其他文化的吸收與融合的文學創作方式,成為了秦文學的發生和變化的內在動因。
①③⑧(14)(15)(19)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 1959年版,第 173、174、173、174、178、192 頁。
②(26)王輝《秦出土文字編年》,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21頁。
④劉節《釋嬴》,《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研究集刊》第一冊。
⑤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頁。
⑥⑩(11)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9頁。
⑦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頁。
⑨(13)王洪軍《新史料發現與“秦族東來說”的坐實》,《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12)李學勤《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
(16)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5-136頁。
(17)班固《漢書》卷94上《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744頁。
(18)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頁。
(20)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靈臺縣文化館《甘肅靈臺縣兩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2期。
(21)趙化成《甘肅東部秦和羌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俞偉超《考古類型學的理論和實踐》,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頁。
(22)趙化成《尋找秦文化淵源的新線索》,《文博》,1987年1期。
(23)李朝遠《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5期
(24)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信息梳理》,《隴右文博》,2004年第1期
(25)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頁。
(26)馬承源《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