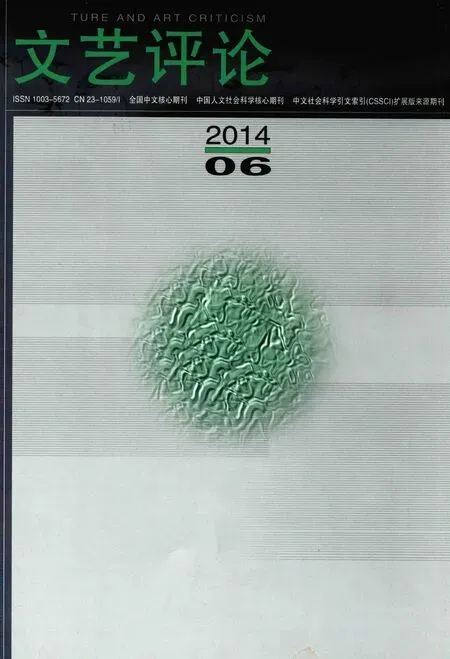杜甫詠物詩中的“物理”與“性靈”
王建生
偉大的文學家杜甫,在詩歌創作道路上進行孜孜不倦的探求,為后世留下許多名篇杰構。據浦起龍《少陵編年詩目譜》,杜甫現存詩作1458首,始于25歲,終于59歲。乾元二年(759),四十八歲的杜甫從同谷入蜀,此后便“飄泊西南天地間”①。客居秦州、成都、夔州、湖湘等地時,杜甫創作了大量的詠物詩,詳觀物態,細推物理,陶冶其詩性精神。通過詠物詩,所了解的杜甫,不再是“醉里眉攢萬國愁”②,一味的憂嘆,而是與自然萬物親密接觸。自然、物態、物理,觸動著他的靈感,撫慰著他的用世情懷,詩人那種靜觀、涵養,浸潤于詩意內外。
一、憂郁心境的調劑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客居秦州。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共創作十六首詠物詩:《天河》、《初月》、《搗衣》、《歸燕》、《促織》、《螢火》、《蒹葭》、《苦竹》、《除架》、《廢畦》、《夕烽》、《秋笛》、《空囊》、《病馬》、《蕃劍》、《銅瓶》。這十六首詠物詩構成大型詠物組詩,縹緲者如天河、秋月,微小者如螢火、促織,甚至無生命的存在體如廢畦、空囊等,都進入杜甫的視野。在對這些大小不一的事物的題詠中,寄寓了杜甫詩性情懷;這一點,鐘伯敬總結得很到位:
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馬》、《病馬》、《孤雁》、《促織》、《螢火》、《歸雁》、《鸚鵡》、《白小》、《猿》、《雞》、《麂》諸詩,有贊羨者,有悲憫者,有痛惜者,有懷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勸誡者,有計議者,有用我語詰問者,有代彼語對答者;蠢者靈,細者巨,恒者奇,默者辨,詠物至此,神佛圣賢帝王豪杰具此難著手矣。③
誠然,在十六首詠物詩中,杜甫本人的情感得以自覺流露,而這種情感又是被壓縮過的,所以在詩中的表露很平和、細緩。如《促織》:“促織甚微細,哀音可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意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④浦起龍注云:“哀音為一詩之主……為‘哀音’加意推原,則聞之而悲,在作客被廢之人為尤甚。感以其類,故深也,絲管不足擬矣。”“音在促織,哀在衷腸。以哀心聽之,便派與促織去,《離騷》同旨。”⑤人情、物意交融在一起,很難分辨出是“哀心”聆聽“哀音”,還是“哀音”觸動“哀心”。之所以稱之為“自覺”,言其有意為之,就十六首而言,雖所詠之物個個不同,卻表現出總體一致的風格,詠物寫心,委婉地寄寓自己的多樣情感,而總體效果卻是物意與人情水乳渾融。
檢點杜甫此前的詩作,未見如此集中創作詠物詩的現象。他如此自覺地創作詠物組詩,與其心境的變化密不可分。客居秦州,開始踏上飄泊之旅,“此作客之始,為東都舊廬殘毀之故,自是長別兩京矣”⑥。遠離政治文化中心長安、洛陽,引起了杜甫心境的變化。因為“長別兩京”,就意味著告別政治文化中心。時年杜甫四十八歲,有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抱負,有“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⑦的才華,卻不得不收起大展宏圖的雙翼,內心深處的酸澀、凄楚不待言表,積郁遂深,該如何調適呢?杜甫調節這種心境的表證,就是聯章體遣興詩的大量創作。秦州時期,杜甫共創作了五組(十八首)聯章體詩。如《遣興五首》之一:“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古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隴阺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干,歲久為枯林。”借古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楊倫評“第一首雖有兩古人作骨,卻多說自家話”⑧。出于調節心境的需要,除了聯章體的遣興之作,杜甫還嘗試用詠物詩的形式,來排遣抑郁。從這個角度來講,秦州詠物詩充當了杜甫憂郁心境的調適劑。
秦州詠物詩的創作,大大開拓詩歌題材,其前雖也有詠馬、詠月之作,卻有一種昂揚的少年精神在其中,就其詠對象而言,大都具有精神激勵意義。而秦州后的詠物詩,其對象更為寬泛,而且更著眼于物意人情之間的溝通,這也是秦州后詠物詩的總體特征。如《病馬》詩中,老馬衰病而不被棄,與詩人哀憐情感相吻合,即是如此。在尋求意情相通的意旨下,“物”不在于形體之大小,可以是日月風雪,也可以是花鳥蟲魚,即便是微不足道之物,彼時彼境,杜甫亦能找到物意關聯點;將情感積淀后通過物意傳達出來。
二、詠物詩的精進之路
從同谷入蜀后,杜甫寓居成都,過上了相對安適的生活。相對閑暇平靜的草堂生活,讓詩人有充裕的時間,帶著詩興的眼光觀物、觀世、觀我,從而誕生諸多清新靈動的詩作。如《江頭五詠》組詩:《丁香》、《麗春》、《梔子》、《鸂鶒》、《花鴨》。浦起龍評:“江頭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時而自防,時而自惜,時而自悔,時而自寬,時而自警,非觀我、觀世,備嘗交惕者,不能為此言。先儒每困于流離中,煉于身心學問,此詩應有合焉。”⑨詩人情感蘊涵在物意之中,詩意中分明有一個“我”,詠物與自詠自喻完美的統一。《梔子》詩:“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⑩在杜甫眼中,梔子有著與眾不同的風姿、情韻;而能發現并賞識梔子之風情,不正是詩人性情的映現嗎?就其所詠之物而言,杜甫善于抓住最有特征的點而透視其全貌,如《梅雨》中“茅茨疏易濕,云霧密難開”(11)二句,將江南梅雨時節淅淅瀝瀝,連日不開的特征概括出來,其中也體現了北方人對南方風土節候的靜觀細察。從成都時期開始,杜甫的詠物詩朝更加精微的方向發展。不僅詠物詩出現精微之作,許多詠物句亦精微迭現,讓人目不暇接,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12),又“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13),無限情致,盡從“繁”、“嫩”出。體物至此,足以“驚風雨”,“泣鬼神”。
到達夔州之后,杜甫的詠物詩創作進入高峰期,約有50首詠物詩誕生。黃白山評價道:“前后詠物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之大,體物之精,命意之遠。說物理物情,即從人事世法勘入,故覺篇篇寓意,含蓄無垠。”(14)夔州時期詠物詩達到自然化工的境界。故李子德評價說“何處得其微妙,貫乎化工矣”(15)。試舉兩例以證之:
《雨》:“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須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才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16)此詩大歷元年(766)春云安作。首聯說時節,頷聯言天氣悶熱,竟用起了扇子,反襯所用非其時,頸聯寫綿綿細雨,尾聯虛筆一晃,讓人頓生無窮遐想。
《江梅》:“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后多。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郁嵯峨。”(17)該詩乃大歷二年(767)春于夔州西閣作。由梅花及春意、客愁,次及雪樹江風,落筆于故園、巫岫,這種跳躍性的物象與空間切換,使“風景不殊河山之異”的今昔感喟,躍然而出。它如《見螢火》、《月圓》、《吹笛》、《庭草》、《樹間》、《白露》等,都可稱得上詠物之杰構。
到達夔州后,同題詠物詩的批量創作,顯示出杜甫獨特的創造力,敏銳的洞察力及非凡的想象力。月、雨成為反復吟詠的對象,詠月七次十首,詠雨十三次十七首。我們不得不驚嘆杜甫同中求異,另辟蹊徑的藝術構造能力,所詠之月,個個清輝,在月光的撫慰之下,有寫不盡的羈旅行愁,碾不碎的還鄉夢。同題同旨的約束下,“江月”與“圓月”又是如何超脫共性,成就其獨特性呢?以《江月》一首為例證明:“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18)浦起龍注云:上四,瑯然清圓;五、六,無塵氣;七、八,更不即不離。月得江而彌光,光滿樓而動思,思由“作客”,客故“霑巾”,觸之者“江月”,為所觸者客“思”也。“玉露”、“銀河”,旁筆寫景。(19)
同題多詠的藝術魅力,在詠雨詩中也得到很好的展示。云安春雨“煙添才有色,風引更如絲”(20),夔州雨“風吹滄江去,雨灑石壁來”(21),寫急雨“行云遞崇高,飛雨靄而至”(22),寫綿綿細雨則“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云,蕭蕭沙中雨”(23),寫密雨則“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24),寫晨雨“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才灑地,風折旋隨云”(25),寫夜雨“山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26),詠江雨則“亂波紛披已打岸,弱云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菜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27),詠寒雨則“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28)等等。這種對雨全方位多視角的描述,只有心入其境,心神與自然的冥合,才能產生如此杰作。有第一等襟懷,有第一等洞察力,方有第一等詩人。才學、識見及詩性感觀,都是這類詩創作所具備的材料,否則,就會跌入呆滯、重復的低谷。在杜甫詠月、詠雨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心靈的律動,這是杜甫詠物詩創作的三昧。
說理、議論的參與,是杜甫夔州詠物詩另一顯著特點。《鸚鵡》、《孤雁》、《鷗》、《猿》、《麂》、《雞》、《黃魚》、《白小》八首,已或多或少的加入議論成分。觸物感懷,感而發之,本是一種通行的詩文寫作規律。由物到情感是一種很自然的表露,而由物到議論,超越個體情感,則是一種突破。一旦進入議論層面,個人情懷已上升到一定高度,民胞物與,所感發的多是大眾情懷或普世性的道理。這既需要情感的轉換,更需要相當廣闊的胸襟與懷抱。當然,在杜甫這里,我們看到議論的火花,星星點點,靈光乍現,給人一種閱讀的沖擊、震撼。以杜甫詠物詩數例,以見證杜甫議論之風采。
《鸚鵡》末句“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29)詩歌結句寫別離之故,感慨遙深。“就剪羽解嘲,言正不須豐滿見奇,有憐而收汝者,將復損之,不如息意于此。”(30)“解嘲”抑或“感慨”,均針對世事人心而發議論,見解明確,發人深省。
《猿》“慣習元從眾,全生或用奇”(31),因猿啼而發議論,借猿智能遠患,來說明涉世之難。《麂》“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32),浦起龍評曰:“五六名言,漢、晉間士人之禍,十字括之。”(33)仇兆鰲注云:“后半慨世,不離詠物,而卻不徒詠物,此之謂大手筆。”(34)感慨議論的強化,使全詩境界闊大。王士禎云:“詠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35)杜甫能跳出一己之私,放眼古今,故能有超脫世俗之見。
《白小》“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句,朱鶴齡評曰:“一魚雖小而不盡取之,豈得為義乎?”(36)拾卵而不盡取,深深的觸動杜甫民胞物與的情懷,所以尾句之議論,實際上包含斥責、呼吁等復雜的情感。
杜甫夔州詠物詩那種行云流水式的筆法,突兀峭拔的警句,水到渠成的情韻,使詠物詩的創作進入自然天成的佳境。這恰好與杜甫總體詩藝的圓熟合拍。黃庭堅有一番經典評論:“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耳。”(37)進入夔州后,杜甫詩歌尤其是律詩的技藝渾然天成,“不煩繩削而自合”。杜甫詠物詩能有如此成就,與杜詩藝術的整體發展密切相關。縱觀杜甫從秦州到夔州時期的詠物詩,可以看出他詩藝精進的過程。
三、“細推物理”、“陶冶性靈”
明代詩論家胡應麟對杜甫詠物詩有一段精當的評論:
詠物起自六朝,唐初沿襲,雖風華竟爽,而獨造未聞。惟杜公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詠月則“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詠雨則“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詠雪則“暗度南樓月,寒深北諸云”;詠夜則“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38)
胡評“自開堂奧”、“盡削前規”、“精深奇邃,前無古人”,誠不為過。杜甫詠物詩確實是一道奇峰,它劈開了一個新的天地。“物”決非消遣之玩偶,而是兼融物理人情,醞育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單不說他那近百首詠物詩,即便那些散落于各體詩作中的詠物寫景句,亦包含人情物理,杜詩中觸目皆是,聊舉數例,以茲證實:“鮮鯽銀絲鲙,香芹碧澗羹。”(39)“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40)“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41)“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42)
杜甫已自覺的將“物理”納入寫作的軌道,“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43),“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44)“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45),又“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46),“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47),等等。“物理”,在杜甫的詩集中有廣泛而深刻的內涵,它既指有形之物的生長榮枯,如花開花落、北雁南飛等等,又蘊含著自然界損益變動,生生不息,興衰更替的規律,乃至當下人情冷暖,世態薄厚,名利的羈鎖,生途的艱澀……足夠讓一社會人躁動不安,形勞神傷。忠君愛國,仁民愛物牽動杜甫的用世情懷,疲憊著那顆憂傷的心靈,“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48),“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49),“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50)。物,舒平詩人眉宇間的憂愁;物,潤澤詩人跳動的心靈。故凝眸望去,物物含情,“沙晚低風蝶,天晴喜浴鳧”(51),“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52),“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53)。
物之理并非終極目的,詩人由物理上升到浮生之理,順應此理,不悖不逆,從而達到物理、生理與人情的自然融合,他明言:“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54)楊倫評此句“言欲識浮生之理,即觀物情可見”。又,“自喜逐生理,花時甘缊袍”(55),如此“體物”,以求“自適”、“自覺”,即追求心靈的安適和內心境界的提升。
因對“物理”的關注,帶動詩人對物情、物態、物色的靜觀細摩。物色方面:“物色兼生意,凄涼憶去年”(56);“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流與老夫”(57);又楊倫評《江村》“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稱“二句物色之幽”(58)。“物色”近于物類,杜詩中,物的品類之盛,讓人稱嘆。物情,含人情而非人情,王國維云:“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59)人之情一經物之潤澤,已非人情,讀者亦不覺是人情,蕩漾著自然的清新與活力,讓人流連,讓人勞神。“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60),“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61),“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62),“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63),“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64),緣不論一笑一喜,一愁一戀,物情、人情幾難分辨,又何須分辨?
植根于物我同視的情誼,以物為友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65)。淡出世俗的物累,看到一個清新澄明的靈物天地,靜的、動的、靜中有動的、動中含靜的,百態俱見。以詠雨詩為例:寫平靜之細雨“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云,蕭蕭沙中雨”(66);寫暴風驟雨“峽云行清繞,煙霧相徘徊。風吹滄江去,雨灑石壁來”(67)。至于詠物句中動靜態的例證,舉不勝舉,此不贅述。
與物理相關捩,便是詩人“性靈”的陶冶。凡偉大之詩人,必具多方面之才能。就杜甫而言,既有體民忠君的懷抱,又有親和自然的情調,若千詩一旨,何以成為偉大詩人!通過詠物詩及詠物句,我們看到詩人生命的律動,感受到他對自然、人事永不疲倦的叮嚀、追索。物,在詩人的煉爐中燃燒,點亮詩人心香一角,那是別樣的杜甫,不是“三吏”“三別”式的悲吟,而是在遣興,在涵養心性。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68)
“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69)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勞。”(70)
在詠物詩中,詩人的心性陶醉在自然物中,性靈的舒展與物象的描摹相牽連,同步運行。何謂性靈?一為精神,一為情感。緊繃心弦的,舒緩平和的,不一而足。物在精神或情感的促動下,對情感的發抒起著緩沖作用,這在《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以諷諭為旨的詠物詩中,表現更突出。將己之情轉化融注在“物“之中,然后由物托出,經此曲折運動,委婉平和,不露鋒芒。如《病柏》一首:“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云會。神明依正值,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鸮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依賴。”(71)李西崖認為,這首詩乃傷悼房琯之作。至于喜怒哀樂等情感,在詠物中有廣泛的體現,如《丁香》末二句“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楊評“若護若誡深婉可味”(72)。
就整體而言,詠物詩中愁、憂的感情成分比較多,這與杜甫經歷、志意有關。黃庭堅二句詩說得好,“中原未得平安報,醉里眉攢萬國愁”(73)。樂也好,愁也罷,一旦經過“物”的洗滌過濾,所散發出來的都是詩性的情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74)、“憑幾看魚樂,回鞭急鳥棲”(75)、“隱幾看帆席,云山涌坐隅”(76)等等,超脫單純物象描摹,彌漫著情感的氤氳,閃爍著跳動的性靈,這也是杜詩魅力所在。
詠物詩的發展源遠流長,《詩經》鳥獸草木,《楚辭》中香草美人,雖為零星散句,遠非后世連篇詠物可比,然狀物貼切,又兼比意,基本上奠定后代詠物之格局。后世詠物,多從物、意兩方面進行開拓:寫物則力求真切神似,托意則求隱委圓融。由先秦的言志、意,到六朝的類化情志,及至唐代,則為個體情懷,極盡曲折,漸至佳境。杜甫詠物詩超越前人,自開堂奧,即使在同時代人中,亦卓然特出,截斷眾流。舉同一時期李白與之相比,杜甫詠物詩的典范意義更為卓著。李白感興散漫之人,詠物詩數量少,遠沒有杜甫的耐心與工巧,興象隨至,無拘無束,感情的激流奔騰橫溢,所以并無規矩可尋,如《南軒松》:“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瀟灑終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云霞,直上數千尺。”(77)杜詩除了情感的蕩漾外,還有物態具象的刻畫。其詠物詩物與情、形與神的有效結合,都為后世詠物詩甚至詠物詞提供了范本。總之,杜甫在詠物詩史上占據承前啟后的地位,其作用重在啟后,其意義是多重的、廣泛的。
①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一,《杜詩鏡銓》卷十三,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50頁。
②(73)黃庭堅《老杜浣花溪圖引》,《山谷外集》卷十六,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342頁。
③楊倫《杜詩鏡銓》卷六《歸雁》引,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62頁。
④⑦⑧⑩(11)(12)(13)(16)(17)(18)(20)(21)(22)(23)(24)(25)(26)(27)(28)(29)(31)(32)(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4)(75)(76)楊倫 《杜詩鏡銓》,第 257-258、25、234、386、317、345、355、580、737、666、580、626、626、627、742、743、782、747、857、828、830、830、64、178、341、357、180、671、922、277、271、952、952、963、445、467、778、813、277、446、968、320、355、446、447、504、890、968、627、626、817、739、1012、370、385、344、782、971頁。
⑤⑥⑨(19)(30)(33)浦起龍《讀杜心解》,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96、27、431、504、523、525頁。
(14)(15)(36)楊倫《杜詩鏡銓》卷十七引,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32、830、832頁。
(34)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七,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33頁。
(35)王世貞《分甘余話》卷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2頁。
(37)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其二,《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本。
(38)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頁。
(59)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77)李白《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