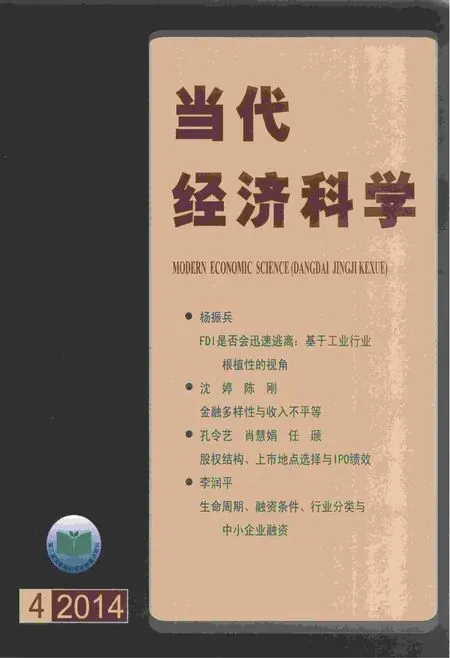金融多樣性與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國經驗數據的實證研究
沈 婷,陳 剛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重慶 401120)
金融多樣性與收入不平等
——基于中國經驗數據的實證研究
沈 婷,陳 剛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重慶 401120)
金融發展的受益邊際是由金融結構而非金融規模來界定的。因此,金融多樣性的上升將有助于擴展金融發展的受益邊際,促進經濟增長成果的包容性分享。本文采用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驗數據,考察了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金融多樣性的上升顯著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這主要源于金融多樣性的上升降低了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間的工薪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不平等。因此,實現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需要放寬當前金融市場上存在的某些歧視性的準入門檻,以此提升金融機構種類的豐富性,同時促進各類金融機構規模分布的均勻性。
金融多樣性;包容性發展;收入不平等
一、引 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GDP總量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遙遙領先于同期世界各國的增長速度。但在財富蛋糕不斷做大的過程中,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卻在持續拉大,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國家之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報道顯示①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0.4-聚焦民生[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截止2011年底,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3:1,中西部城鄉收入差距比為4:1,而行業間差距比更為明顯,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最高行業(金融業)與最低行業(農林牧)之比高達4.48:1。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產生重要影響[1],而且也制約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金融機構作為一國經濟活動的中心,是資本形成與配置的核心職能部門,對收入分配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明晰金融機構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一國政策制定者制定更符合實際的經濟政策具有著重要的作用[2]。國內外許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如章奇,等在分析了中國的金融體系影響城鄉收入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利用1978-1998年的數據,對中國各省的銀行信貸和城鄉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金融中介的發展顯著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3]。姚耀軍基于 VAR模型及Granger因果檢驗法,認為金融規模的發展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且兩者具有雙向的 Granger因果關系[4]。但 Liang、Jalil and Feridun 的研究卻發現金融發展降低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5-6]。陳斌開和林毅夫分析了中國金融抑制影響收入分配的機制,研究表明,金融抑制使得收入不平等現象趨于惡化,甚至造成長期的“兩極分化”,提出逐步放寬銀行業準入標準,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實現收入分配的逐步改善[7]。
上述研究為我們深入分析金融機構的收入分配效應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甚至相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這些研究忽略了金融規模擴張背后的金融結構的變遷,而金融結構的變遷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可能遠比金融規模更為重要。近年來,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大量外資銀行涌入中國金融市場,2000-2011年中國市場上的外資銀行資產規模擴張了7.56倍①2000年,中國市場上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是2850.25億元,但到2011年已達21535億元,數據摘自歷年《中國金融年鑒》。;同時政府出臺一系列措施、政策對國內金融領域進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據中國人民銀行推算②《中國人民銀行》2013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http://money.163.com/13/0509/1818UF2HPOA00254715.html.,中國的金融相關率(FIR)超過3,貨幣化率(M2/GDP)接近2,銀行資產占金融產比率為80%左右,其中,國有銀行資產占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例在2011年已下降到了47.3%,相比2001年下降了35.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政府逐漸放寬對金融機構的準入限制,各類非國有金融機構迅速增長。截止2012年底,中國金融機構共有法人機構3747家,資產總額133.6萬億元③《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2 年報》,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3 -04/24/c_124625348.html。。這表明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已大幅下降,金融機構主體多樣性的金融格局逐漸形成。金融多樣性意味著更寬廣的籌資融資渠道,更豐富的金融產品,更多參與金融活動的機會,這對想獲得資金的農民、低收入者或小微企業具有普惠性,進而從這一層面擴大了金融服務的受益邊界,并將更多低收入群體“包容”進金融市場,這會直接作用于收入分配。
那么,金融機構的多樣性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收入不平等?這是一個需要經驗支持的問題,但現有理論及實證研究并未全面而合理地回答這個問題。在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利用來自中國省際2005-2011年的數據,首先全面考察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再具體分析金融多樣性對城鎮居民各項來源收入集中率的影響。該問題的明晰既是對相關研究的再驗證與發展,也是對金融發展如何更具包容性的探索。
本文余下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將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評論;第三部分介紹收入不平等指標的分解及金融多樣性的測算;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經驗分析框架;第五部分是金融多樣性和收入不平等關系的計量檢驗及討論;最后是本文的結論。
二、文獻綜述
金融體系作為一國經濟的核心部門,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動力。金融機構及其產品多樣性程度的提高,進一步發展了金融市場,拓寬了籌資、融資的渠道,使金融業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美國經濟學Kuznets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也稱“倒U形曲線”),對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開始的時候,尤其是在國民人均收入從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時,收入分配狀況先趨于惡化,繼而隨著經濟經濟發展逐步改善,最后達到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狀況,即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呈倒U的形狀。但是,有關金融與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直到Goldsmith提出金融結構理論[8],Mckinnon和Show創立金融深化論以來才被研究者們普遍關注[9]。現代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發展可以加快經濟增長速度[10],所以,近十幾年來,研究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頗有興趣。Kirkpatrick分析了金融機構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11],Pagano and Volpin[12]、Christodoulou and Tsionas[13]、Shan[14]、Ma and Jalil[15]以及 Shahbaz et al.[16]討論了金融發展程度對經濟持續增長,實物資本積累和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表明,運行良好的金融體系具有動員儲蓄,資源分配,風險管理等功能,這些反過來有利于資本積累,提高投資效率,促進技術改革,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按照這一邏輯,金融結構的發展,更確切地說,金融多樣性發展應該也會產生顯著的經濟影響。Greenwood and Jovanovic開創性地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機構的發展和收入分配放在一個動態模型中討論三者的關系[17]。他們認為,經濟增長為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使其可以更有效地進行投資,金融機構的效率提高反過來也會促進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金融機構運行不完善,經濟增長緩慢。當收入增加,對金融產品需求增多,相應的金融機構主體變多,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加大。當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經濟體系中的金融機構進一步得以發展,收入分配也趨于穩定,即金融機構的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呈倒“U”型關系。Galor and Zeira[18]和Banerjee and Newman[19]認為金融市場的完善,特別是信貸市場的完善能減少收入不平等。但Beck et al.卻指出,在金融發展的早期階段,金融機構收取較高的服務費來保證一定的利潤以及抵御風險,貧困的人由于無力支付高額的成本,會一直處于收入分配的低端[20]。并且,對于本來就沒有抵押品、信用記錄和政治背景的貧困群體而言,貨幣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以及金融中介的交易成本等因素限制了他們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所以,即使有足夠的資金、合理的利率,他們也無法利用這些服務,也就無法獲得金融發展所帶來的的好處,按照這樣的趨勢,隨著金融機構的發展,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
基于這樣的理論基礎,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金融機構的發展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周立和胡鞍鋼分析了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及其特征,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金融資源的條塊分割,無法形成金融資源在地區間和行業間的有效配置。政府的過度介入,加劇了中國金融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差距超過了經濟差距和財政差距,但對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卻未提及。章奇等首次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數據,對中國各省以銀行信貸量占GDP比例表示的金融發展水平和城鄉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金融發展會顯著拉大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他們認為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高度管制及金融機構的高度壟斷導致金融市場的扭曲發展,從而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然而,姚耀軍基于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作出的實證研究結果卻表明,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存在著一種長期均衡關系;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正相關且兩者具有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金融發展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負相關且兩者也具有雙向的Grager的因果關系。廖進中等認為貧困家庭的收入增長大約有31%可以歸因于金融發展的收入分配效應,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所致[21]。楊俊等分析了中國整體、城鎮、農村的金融發展對相應貧困減少的長、短期影響和并進行了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他們的研究發現,農村金融發展抑制了農村貧困減少,中國城鎮金融發展加深了城鎮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甚至進一步惡化了城鎮貧困人口收入分配狀況;中國整體金融發展在短期內緩解了全國貧困狀況并改善了貧困人口收入分配情況,但從長期看,它沒有成為促進貧困減少的重要因素[22]。
通過梳理既有文獻可以發現,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的關系上,而幾乎沒有關注過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在金融市場化改革的趨勢下,放寬金融市場準入條件,逐漸提高金融機構主體多樣性,這勢必會加劇金融機構間的市場競爭,促進金融機構運作的效率[23],降低需求者融資籌資成本,進而降低進入市場的“門檻”。這樣,多樣性的金融機構可以被用作一個有效的工具來影響收入不平等。首先,金融多樣性能更加廣泛的集聚閑散資金,刺激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這將直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其次,金融多樣性發展能使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更適合各層次需求的金融產品,使貧困群體、低收入者、小微企業等都有機會進入金融市場。并且,金融多樣性也能促進各類金融機構分類經營,有利于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第三,金融多樣性不僅能促進實物資本的積累,也能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具體而言,隨著教育、文化、醫療等方面的投資增加,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本也將直接增加。
針對上述研究的爭論和空缺,本文評估了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雖然現在有大量文獻分析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影響,但據我們的觀察,目前還沒有文獻考察金融機構主體的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此,本文可能是首篇做此嘗試的研究文獻。第二,本文構建了一個用于度量金融機構多樣性的指標,具體表述為金融機構集中度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的倒數(1/HHI)。第三,我們不僅總體考察了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而且還具體地考察了金融多樣性對城鎮居民各項來源收入集中率的影響。第四,本文將使用來自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際內部數據(包括自治區、直轄市)來避免跨國數據可能顧慮在的不可比性。
三、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及金融多樣性的測算
(一)收入不平等的測算
現在有許多度量不平等的指標,包括基尼系數、廣義熵指數、Atkinson指數等。本文的主要目的除去考察金融多樣性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外,還希望考察金融多樣性對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各項來源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此,我們選擇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標就需要滿足按照收入來源進行分解的可分解性,基尼系數可能是目前滿足上述條件的一個理想的指標①基尼系數在度量不平等程度時也存在二個不足。首先,它對富人的觀察值比較敏感,如果樣本中富裕人群的收入數據誤差較大(這是常常發生的),那么基尼系數的估算值就很不可靠;其次,同一數量的轉移收入如果轉移到樣本眾數附近,其帶來的不平等的下降比轉移到收入底層更大(萬廣華,2008)。。基尼系數有很多不同的計算方法,我們借用Yao發展的方法來測算和分解中國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
如果總人口被劃分成了n個收入組,且按照平均收入mi由小到大的順序對這n個收入組進行排序。設pi是第i個收入組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重,wi是第i個收入組人口所擁有的收入占收入總額的份額,mi是第i個收入組的平均收入。此時,基尼系數Gini可采用如下公式來計算:


在得到了F種來源收入各自的集中率后,度量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也可以通過如下的公式計算得到:

從上式可以看出,度量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是各項來源收入集中率的一個加權平均,權重是各項來源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wf,wfCf可被視作f種來源收入對總收入不平等的貢獻量,wfCf/Gini則是f種來源收入對總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
如果f種來源收入的集中率Cf大于基尼系數,意味著增長f種來源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權重wf將會擴大收入不平等,說明f種來源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促增來源;反之,若Cf小于基尼系數,說明著f種來源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促減來源。
進一步,我們在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鎮)生活與價格年鑒》上摘得了2005-2011年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的分項來源收入數據(工薪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并在此基礎上分解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結果表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各項來源中,工薪收入所占比重最高,接下來依次是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根據公式(2),測算得到了中國城鎮居民各項來源收入的集中率。
(二)金融多樣性的測算
變量diversity是衡量金融多樣性的指標。本文是以各類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測算的銀行業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來測度中國的金融多樣性。但是,為了得到一個正向度量金融多樣性的指標,本文最終以銀行業HHI指數的倒數來度量金融多樣性變量diversity。因此,變量diversity是由如下公式計算得到的:

其中,si是i類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s是金融機構總資產規模,si/s即i類金融資產占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m是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的種類數①中國各省不同類型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數據摘自歷年各省人民銀行發布的金融市場運行報告,報告中將金融機構劃分為了11大類,包括:大型商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合作機構、財務公司、信托公司、郵政儲蓄、外資銀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他。因此,金融機構種類數m在本文中是11。。變量diversity的取值介于1-m之間,其值為1,說明市場上只有1類金融機構,金融多樣性程度最低;反之,其值為m,說明市場上的m類金融機構的規模分布是絕對平均的,此時的金融多樣性程度相對最高②衡量金融多樣性變量diversity的取值與如下二個因素有關:一是,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的種類數m,二是,金融市場上各類金融機構規模分布的均勻性si/s。因此,當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種類數一定時,金融多樣性就由市場上各類金融機構規模分布的均勻性來決定。實際上,本文以HHI的倒數作為衡量金融多樣性的指標,與生物學中衡量生物境內生物多樣性的Simpson指數的構造思想是一致的。。
四、經驗分析框架

上式中,下標i和t分別是第i個省份的第t年;ν是不可觀測的地區固定效應,它控制了那些在地區間存在差異但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ε為隨機擾動項;β是待估參數。方程(5)右邊的被解釋變量inequality是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指標,我們將采用前文介紹過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Gini)來度量城鎮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同時,我們還將分別以工薪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這四種來源收入的集中率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以考察金融機構多樣性對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居民之間各項來源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解釋變量中diversity是衡量金融多樣性的指標。
最后,為了盡可能緩解遺漏變量引起的回歸偏誤,本文將在回歸方程中納入與被解釋變量密切相關的控制變量:金融發展規模(findev),本文按照既有文獻的普遍做法,以銀行類金融機構總資產占GDP的比例來度量中國金融部門的規模。除去金融多樣性和金融發展規模外,我們還控制了其它一些影響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變量,包括:①人均GDP(萬元)(pergdp)及其平方項(pergdp2),納入這二個變量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演進是否同Kuznets倒“U”形曲線假說保持一致,即檢驗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是否會隨著經濟增長先發散再收斂;②政府支出(gove),本文以政府支出占 GDP總額的比例來衡量;③本文推算6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時,設定小學受教育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專及以上16年。教育水平(education),以6歲及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③;④經濟開放(open),以進出口總額占GDP總額的比例來衡量;⑤城市化率(urban),以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
我們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隨機效應模型(RE)估計回歸方程,對方程進行總體考察。考慮到解釋變量diversity和findev的內生性問題,為了避免產生聯立性偏誤,我們需要尋找工具變量,但在模型之外尋找有效的工具變量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在模型內來尋找。具體來說,我們將采用差分廣義矩估計和(DIF GMM)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 GMM)完成對回歸方程的擬合。系統GMM估計的思路是,首先對回歸方程進行差分變換以消除固定效應,從而得到如下的差分方程(Δ表示一階差分):

上述變換過程實際上就是差分廣義矩估計(Difference GMM)變換。此時,我們可以用水平變量作為差分變量的工具變量,從而采用GMM估計得到參數的一致性估計量。但差分GMM估計也存在缺陷,特別是當變量近似遵循隨機游走時,其滯后水平項與差分項只是弱相關,滯后水平變量就只是差分變量的弱工具變量,此時,參數的差分GMM估計量將不具有漸進有效性[24]。針對這種情況,Blundell和Bond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系統GMM估計。他們認為當固定效應同解釋變量的差分項不相關的情況下,差分變量將是其水平變量的有效工具變量。此時,如果將水平變量作為差分變量的工具變量,并將差分變量作為水平變量的工具變量,對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同時進行估計,就能夠得到在統計上更加有效的估計結果,且在一般情況下,系統GMM二步估計比一步估計更優。系統GMM估計的有效性依賴于工具變量的選取是有效的,以及隨機擾動項的差分項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假設條件,這可通過Sargan過度識別檢驗和殘差序列相關檢驗來進行判斷。
五、計量檢驗及討論
(一)總體考察
我們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隨機效應模型(RE)估計了回歸方程(5),結果匯報在表1中。其中,第1-3列是OLS估計結果。第1列中首先檢驗了核心解釋變量金融多樣性diversity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其估計系數為-0.018并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金融多樣性的提高減少了收入差距;第2列中,再納入金融發展規模變量findev,以控制金融發展規模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此時,核心變量diversity的系數為 -0.017,仍保持1%的顯著性,findev的系數為-0.018,說明在控制金融發展規模之后,金融多樣性的提高仍顯著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第3列中,生成金融多樣性diversity和金融發展規模findev的交互項findiv,進一步準確地考察二者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findev和diversity的系數不顯著,但findiv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為負,這說明金融多樣性是金融規模擴張影響收入不平等的門檻條件,只有當金融多樣性超過一定的門檻值之后,金融規模的擴張才能顯著地降低收入不平等。
以上回歸結果似乎表明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會產生一定影響,但由于OLS沒有控制地區效應,上述檢驗可能因為遺漏某些變量而存在估計偏誤。因此我們根據Hausman檢驗,進一步采用RE效應模型重新估計了回歸方程,結果匯報在表1的第4-6中列。回歸結果與OLS估計結果基本一致,也表明金融多樣性能顯著縮小收入不平等,并且是金融規模擴張影響收入不平等的門檻條件。

表1 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OLS估計和RE估計
OLS和RE的回歸提供了金融多樣性影響居收入不平等的初步證據,但是金融發展規模及金融多樣性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關系,將導致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是有偏且非一致的。因為,隨著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低收入群體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種類和數量都可能減少,這的確可能反過來引致金融規模的縮小和金融多樣性的降低。因此,為了修正方程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偏誤,并驗證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否穩定,本文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再次估計了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素的回歸方程(表2第1-6列)。第1-3列是差分GMM的估計結果。同樣,我們首先考慮核心解釋變量diversity(第1列),估計結果顯示提高金融多樣性能顯著降低收入不平等。將金融發展規模findev納入方程后(第2列),金融多樣性和金融發展規模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前者不顯著,而金融發展規模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金融發展規模也可能會縮小收入不平等。再加入金融多樣性和金融發展規模的交互項findiv后,金融多樣性和金融發展規模的回歸系數不顯著,但二者的交互項findiv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只有當金融多樣性超過一定的門檻值(2.57=0.018/0.007)之后,金融規模的擴張才能夠縮小收入不平等,與之前OLS和RE估計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肯定了金融多樣性在金融發展、改革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作用。

表2 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
由于差分GMM中的差分項可能是水平項的弱工具變量,因此為了提高估計效率,我們遵循Blundell and Bond的建議,采用系統GMM估計再次對方程進行估計,結果顯示在表2第4-6列。當考慮金融多樣性diversity時(第4列),其估計系數也為負,并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金融多樣性的提高能顯著地縮小收入不平等。再納入金融發展規模findev后(第5列),金融多樣性的系數仍顯著為負,而金融發展規模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金融多樣性的提高能縮小收入不平等,而金融發展規模卻可能擴大收入不平等,這和差分GMM估計結果不一致。在將金融多樣性diversity和金融發展規模findev的交互項findiv納入方程之后(第6列),變量diversity和findev都不顯著,但他們的交互項findiv的系數為負,并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并不一定能縮小收入不平等,而只有當金融多樣性超過一定的門檻值之后(2.57=0.018/0.007),金融規模的擴張才能夠縮小收入不平等,這也解釋了系統GMM和差分GMM中關于金融發展規模對收入不平等影響不一致的現象(第5、2列)。系統GMM中的估計與之前OLS、RE效應模型及差分GMM的估計得出的結論基本是一致的。
系統GMM中(第12列)①與差分估計相比,系統估計是將回歸方程中各解釋變量的水平項作為差分項的工具變量,同時將差分項作為水平項的工具變量,對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同時進行估計,從而可能提高估計效率。因此,本文選擇信賴并以GMM估計結果來討論控制變量。系統GMM估計過程可見Blundell and Bond(1998)的論文。,估計其他解釋變量,變量pergdp系數及pergdp2的估計系數分別顯著為正和負,說明城鄉收入不平等的演進軌跡大致遵循Kuznets倒“U”型曲線。教育變量(education)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加劇了收入不平等,這可能是高收入群體接受教育的機會優于低收入群體。城鎮化率(urban)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不顯著。政府財政支出(gov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增加財政支出會擴大收入不平等,這和理論預期是一致的。從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來看,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社會福利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財政支出比例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上,這種失衡結構下的政府支出可能更多的是惠及了中高收入群體,使得居民間的收入不平等隨著財政支出的增加而被進一步的惡化了。經濟開放程度(open)也顯著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原因可能在于高收入群體有更好的機會可以利用經濟開放所帶來的貿易優勢,也就能獲得更多的貿易收益。
(二)基于收入來源分解的考察
在Demirgü?-Kunt和 Levine梳理的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及影響機制的研究中,他們認為金融改革、收入不平等、經濟增長是聯合內生的,三者通過某些機制相互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
其中重點分析了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機制[25]。他們從兩個維度來分析,首先,他們分析了金融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渠道和間接渠道。金融改革使金融服務能直接適用于廣泛的、不同收入組的群體,使那些以前沒有機會進入金融系統獲得金融資源的人也能進入金融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收入差距;并且金融也能通過影響社會總生產及信貸分配,進而影響勞動力市場對不同勞動技能工人的需要,這樣間接地影響收入分配。其次,他們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分別研究了金融對家庭、企業以及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機制。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性使低收入家庭在進行家庭投資決策時會更加慎重考慮收入不確定性、高風險性,以至他們經常會選擇不投資,包括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人力資本投資、醫療投資等,其中特別是人力資本的投資會影響代際間的收入不平等;金融發展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會提高工資率,這樣間接的使更多人能有機會進入金融系統,并且金融發展使更多微型企業成立,促進微型企業的發展,也就能刺激勞動力的需求,改善收入分配;金融發展通過促進整體經濟發展來影響收入不平等,具體而言,金融發展所帶來效益的40%是作用于最貧困的五分之一人口,60%是作用于經濟總量增長,進而通過這兩方面影響收入不平等。
基于這樣的影響機制分析,我們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分解各項來源收入的情況,進一步全面考察金融機構的多樣性對城鎮居民各種來源收入集中率的影響②由于缺乏各收入組農村居民的分項來源收入的統計資料,我們此處只考察金融多樣性對城鎮居民各項來源收入集中率的影響,樣本數據為2005-2011年中國20個省份的數據。。集中率越大表明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也越大,因此考察金融機構多樣性對各項來源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和分析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機制。在具體的操作中,我們使用各項來源收入的集中率對金融機構多樣性及其它影響收入不平等的變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
第1、2列是對工薪收入集中率進行回歸的結果。第1列的估計結果顯示,金融發展findev和金融多樣性diversity各自對工薪收入集中率的影響不顯著,但在考慮它們的交互項findiv后(第2列),findiv的系數為-0.018,并通過5% 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在金融發展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提高金融多樣性能縮小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工薪收入不平等。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性、教育的固定成本,教育投資或人力資本投資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對高收入群體更加可行,換而言之,高收入群體有更多更好的機會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即便他們的學習效率并不比其他群體的學習效率高,他們也能通過更好的人力資本投資及積累進入高收入行業。相反,低收入群體卻不能進入金融系統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就不能取得很高的工薪收入。作為高收入行業之一的金融業,該行業中的金融機構大部分屬于國有,這些國有金融機構依附于國家的庇護,規模大,但總體運行的效率卻有待提高。而隨著金融多樣性的提高,金融市場的競爭會加劇,進入金融市場的門檻會變低,金融服務能更廣泛地惠及各收入群體,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都能獲得一定的人力資本投資機會,這樣勢必會提高他們的工薪收入水平,即金融多樣性會從整體上縮小各收入群體的工薪收入不平等。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的金融改革不能只是一味的強調金融規模的發展,也應重視金融機構主體的多樣性。

表3 金融多樣性對各項來源收入集中率的影響:差分GMM估計
同時,金融多樣性還降低了財產性收入的集中率(第5列),意味著金融多樣性縮小了城鎮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不平等,這和理論預期的相一致。我們的解釋是,金融多樣性的提高,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這不僅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而且最主要的是更大的競爭壓力會促進金融機構貸款給效率更高、信用更好的企業,用來降低自身的經營的風險。金融機構的擇優選擇反過來又會加劇企業間的競爭,因為企業為了籌得資金不得不向金融機構證明自己的在市場和信用上的優越性。競爭激烈時的歧視成本很高[26],這樣在金融多樣性的發展趨勢下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各自所面臨的競爭加劇,他們會減少就業歧視,釋放出更多的經濟機會。特別是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他們的邊際受益更多,財富積累總量也會增加,這也使得他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可能性更大,從而通過這一機制縮小了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的不平等。
金融多樣性對城鎮居民經營收入(第3、4列)的集中率具有的負向影響,但不顯著。此外,金融多樣性對轉移性收入(第7、8列)的集中率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因為轉移性支出是政府部門宏觀調控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發展沒有直接關系。金融部門對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的影響不顯著是符合理論預期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金融多樣性對其他分項來源收入影響的正確性。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穩健性,我們在上述模型中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金融機構集中度的赫芬達爾指數的倒數(diversity0),重新估計的結果仍顯示,金融多樣性的提高會顯著地縮小收入不平等,并且在分項來源收入的估計中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詳細列出長穩健性檢驗的估計結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金融多樣性對工薪收入、財產性收入不平等仍有負向顯著影響,而對經營收入、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具有不顯著的影響。這些估計結果大致和上述模型的初次估計結果一致。
六、結 論
通過以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為樣本,本文得到一些金融多樣性影響收入不平等的經驗證據。首先從總體上考察了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然后在分解各項來源收入的框架下,進一步考察了金融多樣性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機制。回歸結果顯示,金融多樣性的提高能顯著的縮小收入不平等,而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并不一定能縮小收入不平等,只有當金融多樣性超過一定的門檻值之后(2.57=0.018/0.007),金融規模的擴張才能夠縮小收入不平等。我們還發現,金融多樣性的提高對各項來源收入的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金融多樣性主要縮小了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工薪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不平等,它對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只是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上述結論在穩健性檢驗中也得到證實。
金融多樣性發展會加劇金融機構的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從而降低個體和企業金融市場的進入門檻,也能降低金融服務的固定成本,從而使得金融服務具有普惠性,使金融服務更廣泛地適用于更多不同收入群體及不同規模的企業。特別是金融多樣性有利于更多企業的成立,使整個社會釋放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來吸收低技能工人。其次,金融機構的多樣性不僅能加劇金融機構的競爭,他們的擇優選擇也會促進企業提高運行效率,加劇企業間的競爭,這樣社會的總產量會提高,信貸分配更加合理,這些又會反過來作用于勞動力市場。在理論研究及具體實踐中,金融多樣性發展的經濟效應未得到充分理解,使得金融多樣性發展的積極效應容易被忽視。本文說明,金融多樣性程度的提高能縮小收入不平等,并且對工薪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影響更顯著。在市場經濟進一步自由化,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運行的背景下,金融多樣性的發展能將更多群體“包容”進金融市場,分享金融改革所帶來的好處,因此,金融改革的過程中不能只重視金融規模的發展,金融多樣性的發展同樣不能忽視,從廣度和深度兩個層面共同著手才能更顯著地縮小收入不平等,這是實現包容性金融發展的必要條件。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在推進金融規模發展的同時,適當放寬金融機構準入條件、增加金融機構主體的多樣性,并促進各類金融機構規模分布的均勻性,將有利于實現效率下的公平。
[1]陳剛,李樹.中國的腐敗、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J].經濟科學,2010(2):55-68.
[2]Mohapatra D.Income inequality:The aftermath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03,10:217-248.
[3]章奇,劉明興,陶然.中國金融中介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J].中國金融學,2004(3):71-99.
[4]姚耀軍.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經驗分析[J].財經研究,2005(2):49 -58.
[5]Liang Z.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system GMM panel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 to urban China[J].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2006,31(2):1-21.
[6]Jalil A,Feridun M.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Asia Pacific Economy,2011,16(2):202 -214.
[7]陳斌開,林毅夫.金融抑制、產業結構與收入分配[J].世界經濟,2012(3):3-23.
[8]Goldsmith R.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Published b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9]McKinnon R I.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Published by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10]Levine R,Loayza N,Beck T.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6:31-77.
[11]Thorsten B,Demirgü?-Kunt A,Levine R.New database on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or[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3):597-605.
[12]Pagano M.Financial markers and growth:An overview[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3,37:613-622
[13]Christopoulos D K,Tsionas E G.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55-74.
[14]Shan J.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lead”economic growth?A vector autoregression approach[J].Applied Economics,2005,37:1353 -1367.
[15]Ma Y,Jalil A.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 and adaptivefficiency: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J].China & World Economy,2008,16:97 -111.
[16]Shahbaz M.Income inequality-economic growth and non - linearity:a case of Pakist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10,37:613-636.
[17]Greenwood J,Jovanovic B.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076-1107.
[18]Galor O,Zeira J.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35-52.
[19]Banerjee A V,Newman A F.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74-298.
[20]Beck T,Demirguc- Kunt A,Levine R.Finance,inequality and poverty:cross - country evidence[J].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No.3338.
[21]蘇基溶,廖進中.中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貧困關系的經驗分析——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研究[J].財經科學,2009(12):10-16.
[22]楊俊,李曉羽,張宗益.中國金融發展水平與居民收入分配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6(2):23-33.
[23]尹希果,陳剛,程世騎.中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再檢驗——基于面板單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計[J].當代經濟科學,2007(1):15-24.
[24]Blundell R,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5 -143.
[25]Beck T,Levine R,Demirgü?- Kunt A.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across countries and over time:Data and analysis[J].World Bank Econ Rev,2010,24(1):77-92.
[26]Becker H S,Blanche G.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A comparison[J].Human Organization,1957,16(3):28 -32.
Financial Divers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SHEN Ting,CHEN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defined by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instead of financial scale,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diversity will expand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way to share the results of economic growth more inclusively.Using the empirical data of31Chinese provinces from2005 to2011,this paper observes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iversity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China.We find that the rise of financial diversity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come inequality,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at the rise of financial diversity reduces the salary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high income group and the low income group.Therefore,if we want to realize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we need to relax some discriminative access thresholds that exist in current financial market to enrich the typ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the even scale distribution of all kin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Diversity;Inclusive Development;Income Inequality
A
1002-2848-2014(04)-0026-11
2014-03-27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促增與公平分配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2CJL022)。
沈婷(1989-),女,四川省成都市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陳剛(1981-),四川省內江市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book=36,ebook=364
責任編輯、校對:郭燕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