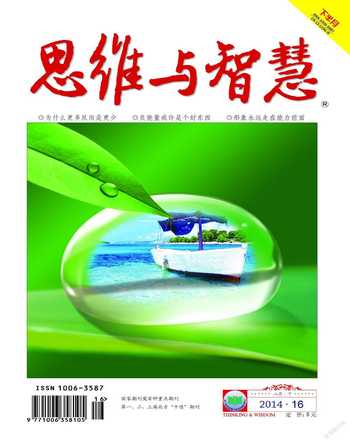訥言者慧于心
林頤
宗璞憶父親馮友蘭,提起馮老的口吃與他的哲學成就一樣有名。
馮先生說“顧頡剛”的名字時,“咕嘰咕嘰”良久而念不出“剛”字;念“墨索里尼”,也必“摸索摸索”許久。馮先生在清華開“古代哲人的人生修養方法”課,首次聽講者達四五百人,第二周減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聽講,因為他的口才不堪卒聽,一句“學而時習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鐘。然而,馮先生把他的口吃轉化成一個有用的演講辦法。每當口吃的時候,馮先生都停頓一下,這樣一停頓反倒給聽眾一個思考他接下來講什么的機會。馮先生接著講出來的話,往往簡要而精辟,于是很多學生漸漸喜愛聽馮先生的講座。
說起馮先生的口吃,立刻聯想到同樣口吃的顧頡剛先生。張中行六十年后依然清晰記得第一次看見顧先生的情景:“一個中年教授站在臺上兀自著急,掃一眼學生,欲言又止,只動嘴唇不發一語,轉身在黑板上狂寫不止……”顧先生期期艾艾,文章卻淋漓飛揚,胸中千萬丘壑,腦中百萬甲兵,下筆如有神,汩汩不停休。
口吃者往往說話簡潔,或者轉化為深邃精練的書面文字,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好的作為。民國的先生們,好幾位雖非口吃,實屬口拙。沈從文站在講臺上,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他呆呆地半天說不出話。好不容易開了口,匆匆忙忙十來分鐘講完了一小時的內容,他只得窘迫地轉身,在黑板上書寫:“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作家卜乃夫回憶起周作人,說“他給我的最深印記,卻是他的躊躇不決。他未開口之前,總是用手抓頭,考慮一下,開口則有點吞吞吐吐,輔助詞用得很多。”陳介石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和中國通史,也是以筆代口,先把講稿油印出來,等到上課,登上講臺,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奮筆疾書。下課鈴一響,他把粉筆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寫的跟講義上所寫的,雖然大意相同,但是絕不重復,相互補充渾然一體,顯見得備課時是很花了一番工夫的。
“敏于行,訥于言。”幾位先生可見一斑。他們將智慧內斂于心,而不輕易表露于外,謹言慎行,自省克己,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靜水流深而澤被后世。今人愛夸夸其談,常巧言令色,以能言善辯為能事,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本領。所以,其實今人不如少一些熱鬧喧嘩,多一些安靜沉默,轉而向內心的求索和行為的實踐吧。
(莫難摘自《邢臺日報》201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