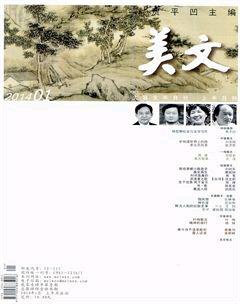書·影
陳若星
懷念昨夜迷蒙的街燈
——存在主義的電影折射
一位好萊塢劇作家吉爾,厭倦了每天只寫劇本的生活,開了一家名為“出自從前”的懷舊商店,并以此為題材創作了一部小說。
商店的名字叫“出自從前”,出售的物品由回憶構成,有些對某一代人而言是平淡無奇,甚至低級庸俗的東西,僅僅由于歲月的流逝,它們的狀態就發生了質變,一下子變得既神奇迷人,又有點兒做作可笑。
吉爾迷戀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巴黎的小巷、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石板路。吉爾常說的話是:想象一下20年代的這座城市,20年代的巴黎,在雨中……
在吉爾的心目中,那個時候,沒有全球變暖,沒有電視,沒有人肉炸彈,沒有核武器,沒有大毒梟……。
于是,吉爾來到了巴黎。
在午夜巴黎,吉爾偶然間坐上了一輛標致老爺車,來到一家酒吧。歌舞歡騰的酒吧中,吉爾的驚喜一個接著一個。怎么也沒有想到,在這里,他邂逅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布努埃爾、畢加索。第二晚,在畢加索的公寓中,他又見到了斯坦因、達利,以及畢加索的情人阿德里亞娜。
來自波爾多地區的法國姑娘阿德里亞娜有著攝人心魄的美麗,吉爾愛上了她。可阿德里亞娜卻心在彼岸,她向往并沉醉于19世紀90年代,迷戀著那時迷蒙的街燈、幽雅的小店鋪……
阿德里亞娜總說自己生不逢時,在她看來,美好時代是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么的敏感多情,那些街燈、小賣亭、馬和馬車,還有‘馬克西姆酒吧。”
又到巴黎午夜時,吉爾與阿德里亞娜乘著一輛華貴的馬車,駛入19世紀90年代的馬克西姆酒吧。在那里,兩人瞬時被一位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所吸引,他們是:高更、勞德雷克、德加……
攀談中,高更說道,這個時代(當然是高更所處的19世紀90年代)是空洞的,沒有想象力的,要是能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好了。高更向往著能與提香和米開朗琪羅并肩作畫的機會。
這是美國獨立制片入伍迪·艾倫影片《午夜巴黎》的主要故事。
伍迪·艾倫通過影片中人物的述說,闡釋了他關于懷舊的理念:懷舊就是拒絕,對痛苦現實的拒絕。
那是些活在過去的人們,那些人認為他們要是活在早先的時光,他們會活得更加幸福。
認為一個人生活在別的時期,總是好于他現在身處的時期,這是一種“黃金時代情結”。
我想逃避我的現在,就像你想逃避你的一樣,都想找到“黃金時代”。
我們都懼怕死亡,并質疑在宇宙中我們身處何方。藝術家的使命,不是向絕望屈服,而是找到一方解藥,來對抗存在的虛無。
實際上,伍迪·艾倫是用他的《午夜巴黎》,向社會,向觀眾,也向薩特,交了一份存在主義的答卷。
薩特的存在主義,主要是關于人的存在狀態的學說。存在者的困境在于總是處于被遮蔽的狀態,去蔽就是一種主動的讓存在顯現的過程。人是在時間中生存的,每個人都是向死而生,無一例外,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與時間的無限性的對峙永遠存在。
那么,懷舊就是一種去蔽,它讓人把過去和現在連接起來,使人的存在不致于處于一種無根基的飄浮狀態。
同時,有學者認為,懷舊也是人類千百年來總結出的一種回避思想危機的有效措施:人類無數次憧憬的黃金時代與世外桃源,都是對于當下社會失范困境的一種主動撤出,以此回避同流合污的沉淪危險,并有力捍衛了社會秩序與正義的存在價值。懷舊作為個體的一種消極自由,保證了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堅持一種走向上的道路的努力。因為你所懷念的總是一些經歷時間磨洗而歷久彌新的人類美德。
難怪伍迪·艾倫這樣說自己:“我參加了一次存在主義的考試。我一個答案都沒寫,結果得了100分。”
相逢
——讀《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
的遐想(代序)
人的一生之中,會有許許多多的、各種各樣的相逢。
有的人寒窗下相逢,成為一同苦讀的同窗;有的人辦公室中相逢,成為共謀事業的搭檔;有的人于海外、異鄉、陌路中相逢,他們或擦肩而過,失之交臂,或從此相識;或一面之交,或從此同道,或結為知音……
各種各樣的相逢,各種各樣的情景;無數的友誼,無數的情懷。
與孝英老師的相逢,我視其為持續30余年的一瞥;或者說,是長達半個世紀的回眸。
(一)
先說持續30余年的一瞥。
上個世紀的80年代初,我正在西北大學歷史系讀書。一個周日回家,適逢家中來了一對父母親的客人。
當時家中只有里外兩間房。我躺在里間的大木床上看書。陽臺外的庭院里枝葉婆娑紛披、小鳥啾鳴,空氣中浮動著那個年代的星期天特有的那種懶洋洋、慢悠悠,溫馨的、溫暖的、清新的氣息,讓每個人的心情都很好、很放松。不時還有蒸熟了的大米飯飽滿的清香和炒菜中油鹽蔥姜沖鼻的氣味。
這時,一個磁性的男中音在外屋響起,父母親也十分客氣地迎和著,聽來是受歡迎的客人。那個男中音說話時,唇齒間帶著一種細碎的南方口音。漸漸地,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是開始了一次口若懸河的演講。
演講的大意是,“男中音”去參與了一次無論對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對他個人來說都是久違的外事活動。在這次高規格的外事活動中,當“男中音”聽到他同樣是久違了的俄語時,感到了極度的蕩氣回腸、心曠神怡。
不知不覺中,我開始仔細地、認真地聽起了外屋的談話。通過談話我獲悉,“男中音”大學時代主修的專業便是俄語。
但究竟是什么樣的迷戀,竟能讓這個人達到如癡如醉的境地?
我第一次得知,一種語言,可以使人“蕩氣回腸”,可以令人“心曠神怡”。
這是一種多么奇特的感覺與體驗!
這是一種多么不同尋常的人生!
好奇心驅使我輕輕地坐起身來,來到里外間相通的門口,悄悄撩開懸垂的珠簾向外看去,原來是一位面龐白皙清瘦、頗為玉樹臨風的青年,旁邊是他的夫人,安靜地聆聽他高談闊論。他們倆一同坐在我家木頭餐桌旁的木椅子上;我的父母,則坐在兩把白色的藤椅上,不時地頷首微笑,看來他們非常欣賞這位青年。
后來,我知道了這位青年就是父母經常提起的那個陳孝英,是他們所在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的同事,文學研究所的青年才俊。
再后來,我更知道了,一個人,對一種語言的迷戀,其實是植根于對那種語言所承載起的文學、藝術等文化形態迷戀的基礎之上的。
(二)
接下來,便不得不說到那個長達半個世紀的回眸了。
這個回眸,從孩提時代,到少女時代,再到青年時代,相隨相伴,揮之不去,永無止息。
曾經,穿上了一條人造棉的、上面綴滿著細碎花朵的連衣裙,母親說,這條裙子叫“布拉吉”,源自俄語。這條“布拉吉”,腰身收束,裙裾擺幅很大,懸垂感很強,穿上身,既婀娜,又飄逸。
曾經,我和小伙伴們的勵志故事,是卓婭與舒拉,是古麗婭,是普通一兵,是保爾·柯察金。
曾經,父母“下放”前,賣掉了一架子車又一架子車的書,留在書架上、書柜中的,是于我如珍寶一般的蘇聯與俄羅斯文學:《葉甫蓋尼·奧涅金》《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普通一兵》《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復活》《戰爭與和平》《罪與罰》《櫻桃園》,以及《靜靜的頓河》……
曾經,屋外的“文革”如火如荼;躲在屋內的我,只知一本又一本地,在雪后熒光色的臺燈下、在午后榆樹的濃陰里、在大雁塔苗圃的灌木草叢中、在夏雨淋瀝的窗前,如饑似渴地“饕餮”著。
曾經,一個個夏日的傍晚,樹陰下、花叢中、小河邊、谷垛旁,我和我的女伴們吟唱著《草原》《紅莓花兒開》《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太,陽慢慢落山,微風徐徐吹來,花香陣陣,一片清涼。
曾經,無數次相聚的休息日與午后,伙伴們都是在吟誦著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蒲寧、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度過;激動之時,大家開始討論起冰天雪地中的莫斯科保衛戰、狙擊手屢立奇功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還有列寧格勒的圍困、庫爾斯克的鋼鐵絞殺、塞瓦斯托波爾的炮臺與潛艇,以及無名烈士墓前的長明火。一個個經典的戰役,一幅幅令人熱血沸騰的圖景,陪伴著我們許多、許多年……
曾經,我也為《青年近衛軍》中蘇聯青年英雄的群像而深深地陶醉和震撼:
“美麗的夏日的頓涅茨河畔,映著月光的深色河水,河面上一朵珍珠般的百合花,在這樣一幅風景畫般的絢麗背景上,出現了一個從柳樹叢里探出身來的姑娘,‘她(鄔麗亞)梳著兩條烏黑的起著波紋的發辮,穿著雪白的上衣,長著一雙這樣美麗的,由于突然從內部放射出來的強烈光芒而睜得大大的、溫潤而烏黑的眼睛,使她自己就很像這枝倒映在暗色的河水里的百合花。”(《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33頁)
“‘站在邊門后面的紫丁香叢中間,她‘打扮得好像是預備上俱樂部去似的。她那總是保護著不讓太陽曬到的玫瑰色的小臉,有著微軟整齊的波紋并且卷成一個個圓圈的金發、好像象牙雕成的小手和仿佛剛剛修剪過的發光的指甲,以及穿著輕便的奶黃色高跟鞋的小小的勻稱豐滿的腳——這一切都顯出仿佛劉勃卡(劉巴的愛稱)馬上就要登臺跳舞和唱歌似的。”(《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35頁)
曾經,這也是我的夢想:
“我多么愿意再活一次,以享受頭一次捧讀《戰爭與和平》的幸福。”(《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174頁)
曾經,我也仿佛看到:
“他(列夫·托爾斯泰)由一簇犁下逃生的牛蒡草萌生了創作《哈吉穆拉特》的最初靈感;又從對一只烏鴉的觀察中悟出了‘人人均有翅膀,人人都應高翔的人生哲理。他寫作進入亢奮狀態,踱步思考時撞到箱子上碰疼了膝蓋,還笑嘻嘻地吟詩自嘲;離家出走后,棲身于修道院客棧,終日沉溺于無法解脫的痛苦之中,竟然還一如既往,字斟句酌地推敲論文,并在寫有‘肥皂“咖啡‘指甲刷之類需從家里寄來的物品清單底下一連記下了四個創作的新題材……”(《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177-178頁)
曾經,在出訪俄羅斯歸來后,陜西省作協副主席、安康市作協主席張虹女士發給我短信:“不管別人如何,我們心靈的收獲太大了!”從而勾起了我內心強烈的共鳴。
曾經,我在寫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文化參贊遲潤林先生的E-mail中說道:
“到過一些國家,但從未有過像抵臨俄羅斯這般,心潮起伏,激蕩難平,在飛機即將降落與飛離俄羅斯大地時,那樣的淚流滿面,不能自已……”
而遲潤林先生則在回信中說道:“看到您對俄羅斯如此鐘情我也很高興。對我們的國家,對那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俄蘇文學藝術熏陶下成長的中國人來說,這種俄羅斯情結恐怕注定要陪伴其一生了。”
這種長達半個世紀的回眸,是在涅瓦大街,在涅瓦河波羅的海人海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故居,在十二月黨人廣場,在無名烈士墓前無法抑制的哭泣、流淚;是自己的心靈對宏大華美、充滿著寬厚包容悲憫之心的俄羅斯文學的回報。
當我在尋找人生真諦時,它告訴我,要追求光明、博愛;當我在思索人生態度時,它告訴我,要樂觀、堅強、永不屈服;當我在學著待人接物時,它告訴我,應當真誠、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這樣長達半個世紀的回眸,便使得我與孝英老師的視線,不可避免地相逢在了一起。
(三)
這樣的相逢,使我們找到了那么多共同喜愛的話題、共同追慕的情調、共同陶醉的色彩,與共同如癡如醉的精神家園。
我們因此,在某時某刻,會打通彼此的心靈隧道。
架起這橋梁的,便是使我們得以彼此溝通的那一種文化的、文學的力量。
那時,雖然我們還未曾相逢,不曾相識,但是,我們卻共同喜愛著,那親切而遙遠的圣彼得堡、莫斯科、圖拉;我們共同將雅斯納亞·波利亞納——列夫·托爾斯泰莊園,奉為我們的精神高地;我們共同沉醉與迷戀著,涅瓦河畔的普希金故居、頓河兩岸的肖洛霍夫家鄉、波羅的海海邊的白樺琳……
那時,雖然我們還未曾相逢,不曾相識,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樣共同的喜愛,是在曾經枯寂、清冷、困惑的日子中,給予我們以精神撫慰,給予我們饑渴的對美感的追求以綿綿不絕養分的眷戀。
那時,雖然我們還未曾相逢,不曾相識,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樣的魂牽夢縈,是在我們狂熱地追求著美麗、力量、前進等目標與理想的日子中,給予我們以導引的感恩。
因此,我慶幸,在30年以后,我和孝英老師又一次相逢;我慶幸,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回眸后,我們因俄羅斯文學而相知。
(四)
暮春初夏的五月,當孝英老師的新著《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的清樣呈現在我面前時,我無法抑制心頭的驚喜。當晚徹夜不眠,將它從頭至尾通讀了一遍。窗外夏雨霖鈴,我一頁頁地翻閱著書稿,思緒也打開了回憶的閘門,半個世紀的回眸,如同電影鏡頭一般,一幕幕地在眼前閃現。一個久久縈繞于心頭的謎團終于得到破解:我面前這位卓越的俄蘇文學翻譯家和研究者,是怎樣實現華麗轉身,成為中國喜劇美學大廈的奠基者的?構建和支撐這座宏偉大廈的基石究竟是什么?他們(孝英老師和喜劇美學)究竟是靠什么完成這一神奇的越境“喜相逢”的?感謝《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給了我一把解秘的鑰匙。
“薩沙!”半個世紀前,那位格魯吉亞的金發少女娜杰日達(愛稱娜佳)這樣輕喚著她為孝英老師起的俄文名字。(《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202頁)
“薩沙!”30年前,那位來自美國的俄裔美婦人娜杰日達(愛稱娜佳)也同樣如此對他呢喃著。(《我遙遠而親近的俄羅斯》第172頁)
記憶深處,根據俄羅斯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克的史詩巨著《日瓦戈醫生》改編的同名影片中,在一座被廢棄的曾經非常美麗典雅的莊園里,日瓦戈的愛人拉拉,用她湖藍色的美麗明眸,憂郁而深情地凝視著,低聲呼喚著主人公日瓦戈的愛稱——“尤里!”
回蕩于20世紀歷史和文化長廊中的那一聲聲深情呼喚,或記錄了令人心醉神迷的跨國度相逢,或定格了讓人肝腸寸斷的跨時空相望,歷史和文化交匯在人性的高地,將瞬間鑄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