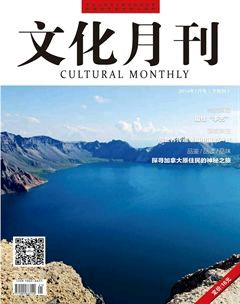東蕩子:探尋世界的光明
大藏

東蕩子簡介
東蕩子,原名吳波。1964年9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東蕩村(東蕩洲),木匠世家。1987年開始寫詩,1988年正式發(fā)表作品;2006年獲中國年度最佳詩歌獎,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2013年獲得“詩歌與人”詩人獎和廣東魯迅文藝獎,著有詩歌集《王冠》、《阿斯加》、《不愛之間》、《九地集》(自印)、《如此固執(zhí)地愛著》(合著)。
2005年起擔任《增城日報》主編。2013年10月11日因心臟病發(fā)作,搶救無效突然辭世,終年49歲。東蕩子認為,詩人在詩歌中的建設,在于不斷發(fā)現(xiàn)并消除人類精神中存在的黑暗。
東蕩子像流星一樣隕落,廣東的詩友們都感到一種深切的缺席——不僅因為少了他的爽朗歡笑和高談闊論,更因為他被截然中斷的詩歌生命,一夜之間使我們失去了最寶貴的精神標榜。這樣的缺憾,相信不僅對廣東,對整個漢語詩歌界都是巨大的,這種損失必將在未來的時空中逐漸顯現(xiàn)。所幸,暨南大學出版社在今年的3月出版了《東蕩子的詩》,作為一名東蕩子詩歌的衷心熱愛者,我遺憾的心情才稍稍得到了一點慰藉。
在廣東的詩歌圈,東蕩子一直都是詩歌和詩歌精神的標榜。我有幸認識他并接觸到他的詩歌,親聆他對詩歌的卓絕宏論。讀東蕩子的詩歌,時常為他在精練成熟的語言背后巨大的容量與深廣的關懷所嘆服,他深邃的思想與愛形成一個向上的引力場,不斷引人探入生存的洞穴與命運的波濤。
東蕩子注重以簡單直截的語言切入價值與意義本身,有意與世俗生活保持距離,他摒棄流行詩歌膚淺的逢迎與反叛,張揚個體獨立的自由、尊嚴、愛與美和智慧的理想。比起一個身份莫測的詩人稱謂,東蕩子更像一個微言大義的寓言家,從樸素的中國生存哲學出發(fā),彰顯了當今詩人所能進掘的靈魂高度和深度。他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個體存在的黑暗,然后他堅硬、閃亮如烏金般的語言開口言說,執(zhí)著地追問并無限逼近另一世界的光明。這使他的詩歌最終獲得了某種超驗性,一種自然渾成的神圣感,它來自于東蕩子對詩人及詩歌本質的深刻體認。作為一個真正的人詩合一者,他異類般的思想源于動蕩漂泊的生存命運體驗及深廣的終極關懷情懷,這與他光輝的詩歌形成了血肉相連的同構。
在當下嚴峻的文化語境下,如何重新認識詩人和詩歌的本質,詩人如何從個體生存和命運的根部出發(fā),讓詩歌重構一個可能的完美世界,東蕩子以他堪稱杰作的詩歌文本,給當代詩壇和公共社會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間。
對詩人及詩歌本質的深刻體認
什么樣的人是詩人,什么樣的詩歌才稱得上真正的詩歌?這個問題,只有在接觸了東蕩子及其詩歌,他離世后又持續(xù)深入地閱讀其文本后,我才有了越來越清晰的回答。
整個青年時代,東蕩子都顛沛奔波在謀生的路上,他當兵、教書、經(jīng)商、做記者……干過十數(shù)種短暫職業(yè),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正是這種如西西弗神話般徒勞的遷徙,他才在父親終于質問他“到底想干什么”時,脫口而出“我想做詩人”。這樣的堅定干脆的回答,源于他深切痛感個體生命的虛無與黑暗,從而轉向形而上的價值思索。
詩人在被時代和生存不斷邊緣化、內向化的過程中將不斷地自我發(fā)現(xiàn),對詩歌本質的深化認識應該也是如此。而東蕩子認為,對詩歌的認識便是對人自身的認識,詩歌是到目前為止“更為強力、和平地解放肉體寄托精神的方式”,詩歌是人的理想,“它作為人已依賴的一種精神形式,一直幫助著我們對美和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并幫助我們企圖實現(xiàn)靈與肉的自由和愉悅的完美結合。”生性豪爽樂觀的東蕩子,顯然淡化了生存環(huán)境與命運的蹇劣強加給生命個體的黑暗和無能為力,而注重從理想觀念形態(tài)出發(fā)來認識詩人,承擔傳統(tǒng)倫理美學價值上的詩歌屬性,所以他說“詩歌的最高境界也仍然是人的最高境界”,詩歌是一個動詞。
如果說東蕩子是基于“外部”概念層面來定義和認識詩人和詩歌本質,那么他還從“內部”的生命與精神個體本身的成長角度,對詩人使命和詩歌價值進行消解繼而突圍,最終實現(xiàn)了其人類詩學體系的烏托邦建構。其中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時代和生存帶給東蕩子的深刻烙印或傷痕——這些在以東蕩子、世賓、黃禮孩等為首的“完整性寫作”群體眼里的“黑暗”,在東蕩子那里,歸劃為詩人個體對強勢外界的認知弱化與詩人品格、氣質、胸懷等的欠缺,他認為“消除黑暗是詩人的天職”,要實現(xiàn)詩歌與人的自然結合,“要想獲得光明而獨立的品質,必須先消除自身的黑暗。”為此,他特別提倡自身的修煉與教育。
在一個詩意被掠奪、人類不斷走向墮落的今天,東蕩子無疑具有一種極其罕見而高貴的理想主義情懷,他的詩歌理想與詩學理念,已遠遠超出了一般詩寫者對詩歌和詩人本質的簡單探尋。他對“詩人”的認識和要求很多時候是基于廣義的“人”而提出來的,因而在詩歌寫作中很自然地推及到了他對人類的自由、尊重、愛、良心與品格等終極人文目標的建構。這種高邁的價值和理想,在他有限華年的詩歌寫作中始終矢志不渝地堅守著。正如詩評家龍揚志所說,“東蕩子的詩歌創(chuàng)作能喚醒我們關注主體尊嚴和思想獨立對于人類的重要性。”正是這種基于對詩人與詩歌本質的探索之上深廣的終極關懷情懷,使他的詩歌在同時代詩壇中散發(fā)出異常高邁、超拔與光明的超驗性,一種自然渾成的神圣格調,因此詩評家洪治剛才說,“這種‘真正的光明不是一種廉價的道德吁求,而是他對詩歌本質的理解和守護。它蘊含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東蕩子在他的詩歌中不僅僅是一個“詩人”,而是一個大寫的“人”,因此,東蕩子獨特的詩歌經(jīng)驗與詩性氣象,也就具有了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研究價值。
“這個時代隱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不僅僅遮蔽萬物的真相,也遮蔽發(fā)現(xiàn)真相的詩歌與詩人。正如《詩選刊》的授獎詞所說,東蕩子“是一位應該更多被詩歌界關注的詩人”,已有對他的評介和研究還遠遠不夠。在詩性萎靡的時代,東蕩子身上具有氫彈般集聚的生命詩性能量,而“他的詩歌語言是從這個世界的高處輻射出來的”(見第八屆“詩歌與人·詩人獎”授獎詞)。我們有理由說,東蕩子就是這個貧乏時代和詩歌所能找到的最合適的人,就像布羅茨基的《黑馬》所寫的,“它在我們中間尋找旗手。”詩歌選擇了東蕩子,而不是他選擇了詩歌。這是一個“世界之夜”與詩歌、詩人之間的相遇,其中蘊含著東蕩子對詩人(乃至于人本身)和詩歌本質的深刻而卓絕的理解。
生命·體驗·思想與詩歌語言的同構
海德格爾說:“在一貧乏時代的詩人,必須特別用詩聚集詩的本性。”只有真正本色的詩歌,才能抗衡一個物質財富急劇增長而經(jīng)驗越來越匱乏的時代,在這方面,東蕩子提供了超越感性的純粹詩歌文本,讓我們在高度異化的環(huán)境中回歸人性,贏得美與愛,恢復尊嚴與創(chuàng)造力。
東蕩子的詩歌,是一種肉體與生命、靈魂與思想、慈悲關懷與堅定信仰等和他的詩性語言形成多極同構的卓越文本。其最基本的源頭便是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地闖蕩所蘊蓄的生存經(jīng)驗與命運體驗,這是一個無比深邃而異常豐富的海洋,東蕩子有幸“進入了詩歌的腹地——光天化日下的黑暗”(詩評家燎原語),他的生命、靈魂、信仰和慈悲心懷都浸浴其中,它構成了東蕩子參透社會人生、體悟世間萬物的基礎。正是這樣,使東蕩子成為一個最深入事物真相也最接近世界本原的人,一個最有能力采擷異域的思想、靈感、情懷、聲音與色彩融入到詩歌語言中的人。正如詩人張紹明所說,“他的詩歌是一滴海水映襯大海,返照人類的心靈。”他用自己豪邁的生命消隱了海水的咸味,消除了詩歌中的黑暗,讓他的詩歌如烏金般堅硬、閃亮,閃耀出永恒的人性光芒。
東蕩子是一個極富言說勇氣的人。他在《旅途》中寫道:“大地啊/你允許一個生靈在這窮途末路的山崖小憩/可遠方的陽光窮追不舍/眼前的天空遠比遠方的天空美麗/可我灼傷的翅膀仍想撲向火焰。”蒼涼的大地上,他一面對原野發(fā)出“天問”,一面“灼傷的翅膀仍想撲向火焰”。這無疑是一首帶著海水咸味的詩,靈與肉、思想與詩性尚處于凝煉階段。在《暮年》里,“黃昏朝它的眼里奔來/猶如我的青春馳入湖底//我想我就要走了/大海為什么還不平息。”詩人的悲憤讓他對著大海發(fā)出了追問,它更是他對生命世界的反詰,這種對存在和真相無窮追問的過程,便是東蕩子消除自身生命黑暗的過程。沉甸甸的“命運的語言”,已經(jīng)將富有穿透力的思想、飽滿的意象和強烈的情感完美融合。在《樹葉曾經(jīng)在高處》一詩中,他從樹葉的飄落聯(lián)想到所有生命有尊嚴的“歸去”,傳達了東蕩子對于生命價值的尊崇,闡明了萬物消逝、生命消亡的哲理。“大地并非沉睡/眼睛已經(jīng)睜開,它伸長了耳朵/躁動并在喧嘩的生命,不要繼續(xù)讓自己迷失/大地將把一切呼喚回來/塵土和光榮都會回到自己的位置/你也將回來,就像樹葉曾經(jīng)在高處/現(xiàn)在回到了地上。”他用對生命的悲憫情懷和高邁超拔的精神理想,使詩歌成為堅守光明立場的終極關懷的完整寫照。而在《它熬到這一天已經(jīng)老了》這樣一首詩中:“死里逃生的人去了西邊/他們去了你的園子/他們將火燒到那里/有人從火里看到了玫瑰/有人捂緊了傷口/可你躲不住了,阿斯加/死里逃生的人你都不認識/原來他們十分驚慌,后來結隊而行/從呼喊中靜謐下來/他們已在你的園子里安營扎寨/月亮很快就會墜毀/它熬到這一天已經(jīng)老了/它不再明亮,不再把你尋找/可你躲不住了,阿斯加。”東蕩子利用“阿斯加”這個虛擬對應物和由火、玫瑰、傷口、月亮等組成的象征森林,營構了充滿奇幻色彩的寓言世界,田園牧歌的意境中充滿了命運感傷的氣息,散發(fā)出雋永悠遠的神性光芒。
東蕩子說:“我堅信從自己身上出發(fā),從他人身上回來,我將獲得真正的光明。”這是他作為本色詩人一生踐行找尋世界的光明可能性的偉大理想,也是對未來后繼詩人們的殷切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