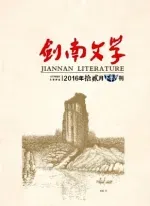《朗讀者》與德國文化精神
本文將從哲學角度分析《朗讀者》與德國文化精神問題,揭示文學作品中蘊含的哲學力量。
德意志人民是一個非常善于進行哲學思考的民族,哲學像他們的信仰一般指引著思考與人生。德國這片土地養育了許多哲學界的大腕兒——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恩格斯、狄爾泰、胡塞爾、海德格爾、卡爾·施密特、漢娜·阿倫特、哈貝馬斯,等等。在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中,德國哲學研究占據了絕大的比重。當然,這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官方哲學是有關系的。但也從某種層面證明了國人對德國哲學的濃厚興趣。海涅曾說:“德國哲學是一項重大的、關系到全人類的事件。”的確,德國是一個盛產思想的國度。康德曾經對哲學做出了“世界概念”的哲學和“學院概念”的哲學的區分。在我國,哲學研究主要局限在了學院職業之中,而這個最哲學的民族產生的哲學卻是隸屬于“世界概念”哲學的。
《朗讀者》的作者——施林克作為一位法律工作者,對于人學也做出了他的判斷與理解,并將其付諸于其小說之中。
所以在《朗讀者》中,米夏經常可以跳出自己的身體,俯視自己和其它人,然后進行思考。小說中,米夏父親也作為一個哲學教授的形象出現。
小說對于“身體”與“精神”關聯的描寫,也體現著德國人的哲學思考。世俗之身在社會中行走,與周邊的一切,尤其是人,發生著相互作用的關系。也許盧梭所倡導那種本初純真的靈魂只是一種美好的期愿。但本質的發現的確能夠幫助世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感知更多、更深。生命的體驗對于每個獨立的個體來說,都是不一樣的,但共性卻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在試圖搞清楚他人的生命體驗時,也是對自我思想的再次審核和深化。
《朗讀者》中,米夏以回憶的方式敘述曾經過去的往事,用一種反觀自我的視角重新體味著當時自己的思想動態和如煙往事。文中曾經出現過兩次《奧德賽》的朗讀,一次是在米夏15歲時,一次是在他年至中年時。“回歸”與“出發”,在小說和電影中都有一定的體現。基于這種哲學性的溯源思考,米夏再次與漢娜產生聯系時,選擇了這部作品作為多年后他再次為她朗讀的文本。米夏在多年后再次閱讀《奧德賽》這個故事,與他在中學時代所感受到的已經不再相同。人不可能兩次掉進同一條河流,有怎么能夠返回曾經的那個故鄉呢?所以成年的米夏認為,“奧德賽回來,不是為了留下,而是為了重新出發。”而海德格爾也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不是著作 (Werke),而是路(Wege)。至于是一條通向何方的路,只能聽者自己意會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條路,每個個體的生命體驗也是一種獨特的軌跡,有的寬些,有的窄些。無數條路錯綜復雜,構成了奇妙的哲學世界。對自我視線范圍內所看到的路進行觀照、思考,就是一種沉思、思辨的文化哲學。
錯誤,每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無法完全避免。“納粹”并不是只有在德國的土地上才能成長,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發生這樣悲劇的可能性。我們能做的就是在錯誤發生之后可以摒棄傲慢的自以為是的態度,站在公共理性、公共情懷的角度上對其進行反思。而德國的嚴謹、反思是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的。作為曾經犯過類似錯誤的日本從未表現出德國對于二戰的反思態度。德國政府在戰后多次表示出懺悔之意,向受害國家賠款。1970年,勃蘭特訪問波蘭雙膝跪拜猶太人紀念碑,并不僅僅一場政治秀。德國能夠做到真正的自我審視、正視過去,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實現的。在這里,筆者并不想把這些當做歷史學、社會學,或者有關政治的案例,筆者更愿意將其歸為哲學范疇。個體能夠實現脫離“愚蠢的見識”,對事件進行深思已然是難得的品質,而德國則是作為一個民族不斷實踐著這種關乎整個人類和每個個體的終極思考,這不能不讓我們感到一種讓人無法不為之動容的哲學力量。
(江西南昌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