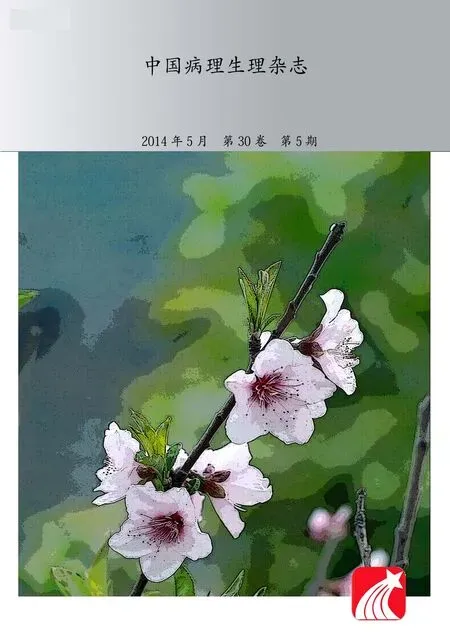IL-33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與中國南方漢人炎癥性腸病臨床表型相關*
張青森, 楊慶帆, 陳白莉, 何 瑤, 陳旻湖, 曾志榮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消化內科, 廣東 廣州 510080)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種病因尚不清楚的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羅恩病(Crohn disease,CD)。近年來,炎癥性腸病的發病率明顯上升[1-2]。然而,其發病機制仍未明確,目前認為是由遺傳、環境和免疫等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白細胞介素33(interleukin-33,IL-33)是新近發現的炎癥因子,具有抑制和促進炎癥的雙重作用[3-4],與多種免疫及過敏性疾病相關[5-6]。研究發現,其在IBD患者腸、黏膜和血清中明顯異常表達[7-8],并在IBD炎癥、黏膜愈合及纖維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9]。Latiano等[10]近期發現IL-33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rs3939286增加意大利人IBD發病風險,而關于IL-33基因多態性與中國人群IBD的關系尚無報道,本研究旨在探討IL-33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與中國南方人群IBD發病及臨床表型間關系。
材 料 和 方 法
1 研究對象
將我院 2003年~2012年IBD診治中心確診的365例IBD患者 (CD 250例,UC 115例),以及同期在我院健康體檢的622名性別、年齡匹配的健康人(無免疫系統相關病史)納入本研究。IBD診斷標準參考2012年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推薦標準[11],基于臨床表現、消化內鏡及組織學檢查作出臨床診斷,確診病例為經病情觀察符合CD/UC病程經過或通過手術取得病理診斷者。臨床資料通過查閱我中心IBD數據庫獲得,包括患者人口學資料及臨床分型特征,即性別、發病年齡、癥狀、吸煙史、家族史、腸外表現、肛周病變、臨床特征等,IBD臨床分型采用蒙特利爾分型標準[12],見表1。本研究已通過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臨床研究倫理委員會批準,標本采集獲得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

表1 炎癥性腸病病人基本資料
2 方法
2.1基因組DNA獲取 采集患者及健康對照每人2 mL外周血,利用天根血液基因組織DNA 提取試劑盒 (北京天根有限公司) 提取基因組DNA。操作步驟參見試劑盒說明書。
2.2SNP挑選及分型檢測 本研究選擇的8個標簽SNP(Tag-SNP)是綜合考慮已有文獻對于IL-33與疾病關系的報道以及SNP位點在IL-33基因的具體位置而確定的,前者基于IBD與多種免疫相關疾病存在基因重疊,后者基于突變點是否可能影響IL-33的表達及功能(http://www.ncbi.nlm.nih.gov/SNP/snp_ref.cgi?chooseRs=doublehit&locusId=90865&mrna=NM_001199640.1&ctg=NT_008413.18&prot=NP_001186569.1&orien=forward&refresh=refresh)。各位點的功能特性、最小等位基因頻率及與疾病的關系情況見表2。SNP檢測采用基質輔助激光解吸電離飛行時間質譜技術(MALDI-TOF MS),由深圳華大基因有限公司完成。

表2 8個SNP的基本信息
2.3相關評判標準 內鏡下黏膜愈合情況依據CDEIS評分分為愈合、部分愈合和未愈合3個等級;愈合定義為CDEIS評分<3分和(或)內鏡下未見潰瘍;部分愈合定義為CDEIS評分3~6分和(或)內鏡下腸道黏膜輕度炎癥、小糜爛、淺潰瘍或者潰瘍較前好轉;無效定義為CDEIS評分較前下降<5分,潰瘍仍然存在,較前無明顯消失或者變淺[11,13]。英夫利昔單抗臨床療效評估依據CDAI[11],臨床有效定義為CDAI下降≥70分,臨床緩解定義為CDAI下降雖<70分但CDAI<150分,臨床無效為使用英夫利昔單抗治療10周時患者臨床癥狀未改善且CDAI評分>150分。
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根據Hardy-Weinberg遺傳平衡定律,采用2檢驗分析CD、UC及對照組樣本的群體代表性。各SNP位點在病例組與對照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頻率的比較采用 Pearson2檢驗;基因型及等位基因與IBD臨床特征間關系采用單因素和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優勢比(odds ratio,OR)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其中OR值經性別和年齡校正。數據以均數±標準差(mean±SD)表示。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 一般情況
本研究病例組共納入365例IBD患者,均為中國南方漢族人(表1),其中CD 250例,UC 115例。CD患者平均年齡(32.7±12.3)歲,其中男性160(64.0%)例;UC患者平均年齡(38.0±13.6)歲,男性共68(87.0%)例。對照組共622名,平均年齡(31.4±8.0)歲,男性400(64.3%)例。CD及UC組與對照組間的性別和年齡構成比均無顯著差異(P>0.05)。
2 IL-33各SNPs基因型在IBD患者及健康人群中的分布
挑選的8個SNP在CD、UC及對照組中基因型分布頻率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具有群體代表性。進一步分析比較發現,這8個SNP位點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頻率在病例及對照組中均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3。

表3 各SNP的基因型在CD、UC及對照組中頻數及頻率分布情況
3 IL-33各SNPs基因型與IBD臨床表型的關系
rs10118795和rs7025417的基因型與CD患者腸外表現相關。rs10118795 含等位基因T的基因型(包括CT和TT)是腸外表現的保護因素(P<0.05, OR=0.513, 95% CI: 0.281~0.938),見表4;而rs7025417 CC基因型的CD患者出現腸外表現的風險更高(P<0.05, OR=1.363, 95% CI: 1.006~1.846),見表5。

表4 rs10118795基因型與CD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表5 rs7025417基因型與CD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rs10118795及 rs10975519與CD患者肛周病變相關,而rs10975509跟CD患者初診時病變部位相關。rs10118795 含C等位基因的基因型(CC和CT)降低肛周病變風險(P<0.05, OR=0.480, 95% CI: 0.232~0.994),見表4;而rs10975519野生純和子CC顯著增加肛周病變風險(P<0.05, OR=2.054,95% CI: 1.053~4.009),見表6。對于rs10975509,其與上消化道型CD高度相關,含G等位基因的基因型(GA和GG)增加上消化道型CD風險(P<0.05, OR=3.570, 95% CI: 1.328~9.600),同時該SNP 的A等位基因是回結腸型CD(P<0.05, OR=0.613, 95% CI: 0.377~0.996)的保護因素,見表7。

表6 rs10975519基因型與CD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表7 rs10975509基因型與CD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在SNP與英夫利昔單抗治療療效關系分析中,共納入29名長期行英夫利昔單抗治療CD患者,我們分析了8個SNP位點基因型與10周、30周內鏡黏膜愈合情況及臨床療效的關系。rs10118795、rs10975509和rs7025417基因型與英夫利昔單抗治療后CD患者30周黏膜愈合相關(分別為P<0.05、P<0.01和P<0.05),見表8,但進一步分析未能明確某一個基因是30周黏膜愈合的危險或者保護因素。8個SNP與英夫利昔單抗治療臨床療效無關。

表8 SNP與CD患者英夫利昔單抗治療30周黏膜愈合情況的相關性
同時,對這8個SNPs與UC發病及臨床表型的關系的分析未發現相關性(P>0.05)。
討 論
IBD作為一種發病率逐年增加的腸道非特異性炎癥性疾病,其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遺傳、免疫、環境等多種因素參與到IBD發病中。在遺傳方面, IBD國際基因協作組通過GWAs及基因芯片技術已經發現有關IBD的163個基因位點[14],盡管如此,仍有約30%常見變異型未被包括在內。許多研究顯示,炎癥因子及其受體基因的SNP與IBD疾病易感性相關,例如很多IL-1家族成員,如IL-1β[15]、IL-1RA[16]、IL-18等[17],它們的基因SNPs均與IBD疾病易感性相關。IL-33是IL-1家族的新成員。研究發現,其對炎癥具有雙向調節作用:一方面,可進入核內抑制基因轉錄[3],最終抑制炎癥信號通路;另一方面,可通過與跨膜ST2(ST2L,需IL-1RAcP輔助)[4]作用激活炎癥通路,從而促進腸道炎癥;此外,IL-33還可促進IBD炎癥慢性轉化并參與腸黏膜愈合、上皮修復及纖維化過程[18]。
本研究選擇了IL-33基因的8個SNP位點,研究其與中國南方漢人IBD間的關系。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這8個SNP位點并不增加IBD發病風險,但我們發現rs10118795、rs7025417、rs10975509和rs10975519影響CD的臨床表型。
rs10118795、rs7025417和rs10975509均位于轉錄因子結合位點(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TFBS),TFBS是與轉錄因子結合的DNA序列,它們與轉錄因子相互作用調控基因的轉錄過程,因此這些位點的變異可能影響IL-33的表達,從而影響疾病表型。我們研究首次發現這3個SNP位點與CD相關。rs10118795 T等位基因是腸外表現的保護因素,且C等位基因攜帶者出現肛周病變的風險降低;而在rs7025417,攜帶基因型CC的CD患者出現腸外表現的風險更高;rs10975509則與CD病變部位相關,AA基因型的患者出現上消化道型CD風險更高,同時數據顯示該SNP GG基因型增加出現回結腸型CD的風險。最后,我們還發現這3個SNP的基因型與英夫利昔單抗治療后CD患者30周黏膜愈合相關,但進一步分析未發現哪一個基因是30周黏膜愈合的危險或者保護因素,可能是樣本量不足所致。
rs10975519和rs1929992在日本人花粉癥中有報道[19],前者與花粉癥發病無關,而后者CC型基因增加該病發病風險。本研究并未發現rs1929992與中國IBD發病及臨床表型相關,但rs10975519 CC型增加CD患者出現肛周病變機會,據報道[19]rs10975519位于IL-33基因外顯子區域,可出現錯意突變,并與周圍堿基形成剪切增強子或剪切沉默子,由此可能影響IL-33的表達水平或者mRNA穩定性。
rs11792633和rs7044343均為內含子,前者與漢人及白種人阿爾茲海默病發病相關,其T等位基因為該疾病的保護性因素,而后者只與白種人阿爾茲海默病發病相關[20],但本研究未發現它們在IBD中的作用。
由于這8個SNP位點存在高度連鎖不平衡,所以未進一步做單體型分析。另外,本研究中納入進行IL-33 SNP與英夫利昔單抗治療療效關系分析的樣本數目過少,因此,它們之間的具體關系有待繼續論證。
IBD的遺傳背景十分復雜,作為一種多基因疾病,不同的人種、國家甚至地區間均存在遺傳易感性差異,本研究分析了IL-33與中國南方漢人IBD遺傳易感性的相關性,發現了與中國南方人群相關的tSNPs,其中rs7025417跟CD臨床表型相關,然而Latiano等[10]研究表明,rs7025417跟意大利IBD的發病及臨床表型均無關,這進一步說明不同種族存在著遺傳易感性差異;此外,IL-33與其他人群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以便全面認識IL-33與IBD的關系。IL-33基因多態性與其表達是否相關,其多態性參與調節IBD疾病進展的具體機制仍有待研究。
[參 考 文 獻]
[1] Zeng Z, Zhu Z, Yang Y, et al. Incidenc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a deve-loped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3, 28(7):1148-1153.
[2] 楊慶帆, 陳白莉, 張青森, 等. 殺菌/通透性增加蛋白基因Glu216Lys多態性與中國漢族人群炎癥性腸病無關[J]. 中國病理生理雜志, 2013, 29(4):718-723.
[3] Carriere V, Roussel L, Ortega N, et al. IL-33, the IL-1-like cytokine ligand for ST2 receptor, is a chromatin-associated nuclear factorinvivo[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7, 104(1):282-287.
[4] Palmer G, Lipsky BP, Smithgall MD, et al. The IL-1 receptor accessory protein (AcP) is required for IL-33 signaling and soluble AcP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soluble ST2 to inhibit IL-33[J]. Cytokine, 2008, 42(3):358-364.
[5] Prefontaine D, Lajoie-Kadoch S, Foley S, et al.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IL-33 in severe asthma: evidence of expression by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J]. J Immunol, 2009, 183(8):5094-5103.
[6] Matsuyama Y, Okazaki H, Tamemoto H, et al. Increased levels of interleukin 33 in sera and synovial fluid from patients with active rheumatoid arthritis[J]. J Rheumatol, 2010, 37(1):18-25.
[7] Kobori A, Yagi Y, Imaeda H, et al. Interleukin-33 expression is specifically enhanced in inflamed mucosa of ulcerative colitis[J]. J Gastroenterol, 2010, 45(10):999-1007.
[8] Seidelin JB, Bjerrum JT, Coskun M, et al. IL-33 is upregulated in colonocytes of ulcerative colitis[J]. Immunol Lett, 2010, 128(1):80-85.
[9] Kunisch E, Chakilam S, Gandesiri M, et al. IL-33 regulates TNF-alpha dependent effects in synovial fibroblasts[J]. Int J Mol Med, 2012, 29(4):530-540.
[10] Latiano A, Palmieri O, Pastorelli L,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IL-33,IL1R1 and risk f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PLoS One, 2013, 8(4):e62144.
[11] 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炎癥性腸病學組. 炎癥性腸病診斷與治療的共識意見(2012年·廣州)[J]. 胃腸病學, 2012, 17(12):763-781.
[12] Silverberg MS, Satsangi J, Ahmad T, et al. Toward an integrated clinical, molecular and ser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report of a Working Party of the 2005 Montreal World Congress of Gastroenterology[J]. Can J Gastroenterol, 2005, 19 (Suppl A):5A-36A.
[13] Hebuterne X, Lemann M, Bouhnik Y, et al. Endoscopic improvement of mucosal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leocolonic Crohn’s disease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certolizumab pegol[J]. Gut, 2013, 62(2):201-208.
[14] Franke A, Mcgovern DP, Barrett JC, et al. Ge -nome-wide meta-analysis increases to 71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rohn’s disease susceptibility loci[J]. Nat Genet, 2010, 42(12):1118-1125.
[15] Nemetz A, Nosti-Escanilla MP, Molnar T, et al. IL1B gene polymorphisms influence the course and severit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Immunogenetics, 1999, 49(6):527-531.
[16] Stokkers PC, van Aken BE, Basoski N, et al. Five genetic markers in the interleukin 1 family in relation to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Gut, 1998, 43(1):33-39.
[17] Aizawa Y, Sutoh S, Matsuoka M, et al. 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18 gene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with susceptibility to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Tissue Antigens, 2005, 65(1):88-92.
[18] 楊慶帆,曾志榮. 白細胞介素33在IBD炎癥進展和黏膜愈合中的作用[J]. 胃腸病學, 2013, 18(2):118-121.
[19] Sakashita M, Yoshimoto T, Hirota T, et al. Association of serum interleukin-33 level and the interleukin-33 genetic variant with Japanese cedar pollinosis[J]. Clin Exp Allergy, 2008, 38(12):1875-1881.
[20] Yu JT, Song JH, Wang ND, et al. Implication of IL-33 gene polymorphism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 Neurobiol Aging, 2012, 33(5):1014.e11-1014.e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