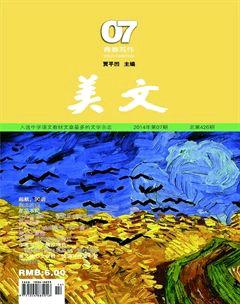有片熱土,喚作故鄉(xiāng)
張迎亞
有這樣一片熱土,灰褐棕黃,以糧食和財富恩澤十里八鄉(xiāng);有這樣一片熱土,油流滾滾,用平凡和偉大詮釋隱忍剛強。這片熱土很大很大,“天下至中的原野”是蒼生黎民賞賜她的無上尊稱;這片熱土很小很小,在我的唇齒間,她僅有這么一個私密而羞澀的乳名——“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地處中原,1975年濮參1井鉆至2600多米深時,油流噴薄,聲震平野,令祖國四方的石油漢子為之請纓掛帥,奔赴“疆場”。十余載光陰荏苒,油梁馱起晨光,鉆塔目送夕陽。當中原大地一點點褪去最初的荒蕪,我的父母80年代末輾轉至此,在魯豫兩省交界處那座小小采油廠里執(zhí)起教鞭,為中原教育事業(yè)奉獻他們的忠誠與熱望。
1990年秋,我降生在這片熱土。最初幾年由奶奶帶著,我漸漸熟悉了礦區(qū)里簡樸的陰灰色居民樓,廠門口人流熙攘的服務公司以及徒駭河東岸,那蔭庇著數十家商戶的白鐵皮板房。那時,父母初登三尺講臺,經驗少,課時多,常常熬紅了雙眼,站腫了雙腿,才滿心憂慮地收起教案,離開課堂。于是,我唯一的娛樂空間,落在了父親的自行車后座,他載著我,在廠門外交錯的阡陌間緩步徐行,自在徜徉——
惠風和暢。我瞇眼四望,田野里一架架宏偉的鋼鐵機器毅然挺立,老馬一般的“頭”慢慢低下,又抬起,像在品味食槽里的青草,謙卑馴良。爸爸說,那叫“磕頭機”,石油工人就用它們把地下的原油一汩汩搬出石縫,重見日光。我幼嫩的心中充滿驕傲,竟認為這遠近屹立的橙黃色“老馬”,是家鄉(xiāng)獨有的炫目景象。
進入90年代后半期,這片熱土在勘探開發(fā)、掘油采氣的快車道上前行,生產經營形勢連年向好。那時,中原的中小學教育仍歸油田統(tǒng)一管理,爸媽執(zhí)教的中學師資齊備,精于教研;學生也是清一色的“石油娃”,篤思勤學。一所遠離基地的前線初中,屢屢在全局20所余中學的中招成績冊上名列前茅,一度成為方圓數百里的教育制高點,榮光無上。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在這片繁榮安和的熱土生息綿延。仲春時節(jié),礦區(qū)道路兩旁的楊樹柳樹散播它們的種實,漫天似雪,不舍晝夜;初夏清晨,父親的學生輕輕叩門,送來了自家院里新成熟的櫻桃,一粒粒安臥盆中,燦若珠貝;秋收農忙,我看見一隊隊“紅工裝”和農民一道勞作在田間地頭,金燦燦的稻谷顆粒歸倉;寒冬深夜,我偶遇剛制伏一場井噴的作業(yè)隊伯伯,牛仔藍作業(yè)服上污泥斑斑,凝凍的原油附著在滴塑手套,塑成一副鋼鐵盔甲,銳不可當。
四季交迭,我日日行走在這片因油而生、因油而興的熱土,脾性多少受到感染,誠然純粹,隱忍倔強。這于我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至今仍未想過,也無需去想。這是故鄉(xiāng)賦予我的秉性,一生難改,貴如典藏。
2012年夏,我結束了四年大學學業(yè),陰差陽錯回到這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我拿起采訪本,執(zhí)起筆,開始經常面對堅守各個崗位的工作者,謙卑而專注地問一些話語,記一些言行。我時常覺得,自己正躲在“記者”這副幸運而安全的面具之下。這副面具保護我不動聲色、細致入微地觀察這片熱土,十余載年少時光里曾忽略的一切細節(jié),正字字句句躍然紙上——
兒時田野里那一座座圍墻低矮、裝備林立的院落,原來叫做計量站,深褐色的原油在這里被精確計量、初步處理,由外輸管線流向四方;郊游時偶遇的紅白兩色鋼鐵高塔原來叫做鉆塔,它承載一根根鉆具頓挫升降,一口口深達千米的油井被寸寸開鑿;父母口中叫慣了的“礦區(qū)”不知何時改稱為“社區(qū)”,綠蔭如蓋,家富民安,我與之交談過的每一位居民都感覺似曾相識,他們仿佛從我的童年走來,都說著謙和的話語,都帶著淳樸的容貌。
我時常感覺自己言行遲緩,來不及記錄下這片熱土一切的深情款款、澎湃激昂。但至少我已啟程,我正用這片熱土賦予我的一切,報恩般書寫她的歡喜和悲傷。或許有天我會停止,但只要聞見那濃郁的油香,只要聽見抽油機沉穩(wěn)升降的清響,我都將默念一遍腳底熱土那私密的乳名——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