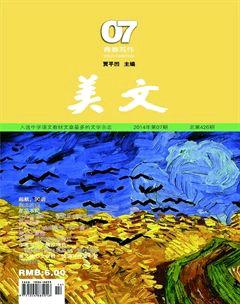我心中的文學
史浩霞
文學在我心中首先是最好的知心朋友,一個供我發泄和傾訴情感的對象,更多的時候它會充當一張白色的宣紙,像一個潑墨者那樣,我常常需要借助筆記本或者電腦把這些躍然或者潛伏于思維之淵,或者內心之空的“色彩”以及“線條” 描摹和勾勒出來,讓這幅潑墨畫實現畫境與心靈波濤“顛簸”后的某種契合與平衡,二者達到和諧的時刻往往是文學與作者之間配合默契,關系微妙甚至是“物我合一”的“坐忘”之境。
這種境界如同心靈在大風大浪中顛簸前行,所有的郁積都如一只只單薄的小船在黑暗的夜晚中前行,文字的巧妙就在于它能在某個突然的時刻,充當某一束照亮黑暗的光,而文學則會讓這束光變幻出多種色彩,在某種形而上的“浪漫氛圍”中,繃緊的心靈如水流般緩緩疏解,或者實現某種宣泄的澎湃,最后于一處光明之境抵達某種徹底的安寧;抑或是于縱橫阡陌中迷路的行者,突然明確某個方向時內心瞬間變得澄明,如佛祖在菩提樹下靜坐之后洞觀人世的大徹大悟。
此種感覺,經歷過的人都會體會到它的美好。
于我,寫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內心的需要。我的“飽滿的”抑或是“堵塞的”內心需要并渴望這種宣泄和表達。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學更像是我的心靈之音的發聲器。
最開始接觸文學大概是小學的時候。這個階段更多的是模仿。朱自清的《匆匆》,老舍的《養花》不知道被我在作文中引用過多少次。記得小學二年級時的一次升級考試,作文題目就是寫自己熟悉的小動物,我寫了我們家的貓,記得當時特別高興,因為我在作文里套用了老舍的《養花》中的 句子:“有喜有憂,有笑有淚,有花有果,有香有色,這就是養花的樂趣。”只是我只取了這句中的前兩句,只把“養花”改成了“養貓”而已。就這點小聰明已經把我樂壞了,一路上父親用自行車載著我,我興高采烈地一遍遍講述著我作文的內容,陽光在微風中蹦跳的歡快節奏一陣陣加速著我們前進的車輪。
到了初中,文學就多了些“創造”。記得那時校長給我們講如何將文章寫得詳略得當,重點突出。他用他的攝影作品來為我們展開分析。那是一幅關于一個陜北老漢的攝影作品,老漢圍著白色的頭巾,嘴里叼著一個銅制的大煙鍋,煙鍋上還吊著一個黑色的繡花煙袋,他的臉在正午的陽光中輪廓分明,一雙眼睛深陷而布滿皺紋,像是某種煙霧籠罩的枯井。而他身后,遠處是土山,幾棵老槐樹,大門,土圍墻以及一只老母雞。正如我重點突出人物一樣,寫作也如攝影,要找準重點,回想起來這堂課對我的一生都極具意義。
只是初中的時候,我們大都只寫散文、日記。而那時我認為我寫的東西很少能實現文學層面的意義。比如心情極糟的時候寫的日記只有“煩死了!”幾個字,更糟的情況下會沒有文字,只是“單純”的線條意義上的亂涂亂畫,簡直能達到把紙劃破的程度。但是很多情況下還是需要借助文字來表達某種“心聲”,大抵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我習慣于在文字層面掩飾自己的痛苦,那時我總是喜歡借助一些事物,通過一定的象征手法來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內心。別人自然會看得一陣云霧,只有自己最清楚,亦能達到某種發泄。
我常常喜歡把文學和“心學”聯系到一起,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文學也是“心學”,它是一種心的學問。文學首先需要一顆感知敏銳的心靈,一雙善于發現美的眼睛。我想這是一個優秀的文學創作者的基本素質。而這種素質往往具有一定的先天性,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無法改變。但是后期的積累也尤為重要。一個優秀的文學創作者除了有一顆敏感的內心遠遠不夠,博覽群書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寫出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土壤,大凡優秀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等等這些縱橫交錯的時空網絡之中的。而躋身于茫茫作品文海中,讓作品能夠遺世獨立,往往還需要作者自身的實踐或者經歷,而正是作者經歷其中,才會對人,對事、對社會、對歷史、對生活甚至某種信仰和價值觀產生一定的獨立見解。這跟寫作者跋涉和沉淀的過程亦非常重要。
所以一個優秀的作者必須學會閱讀,善于讀書,勤于思考。
大學,可能是大二上半學期開始接觸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開始寫詩歌、散文、小說,開始開通博客,關注征稿信息,開始投稿,直到較多的發表。這對于寫作者來說當然是一個肯定,但于這種事關“名利”的追逐中我們需要保持那份最初的文學心,切不可只圖一時的發表而過焦過躁,只是一味的寫而忽視閱讀和積累。堅持在大量的閱讀和積累的基礎上進行寫作,我覺得這樣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你在寫文時的底氣,就像我在一首詩中寫的那樣:陜北的山是我堅強的后盾,我想,閱讀和積累必是文學最為堅強的后盾。
對于文學,我還很年輕,我還在路上,我能做的只有且讀且寫,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