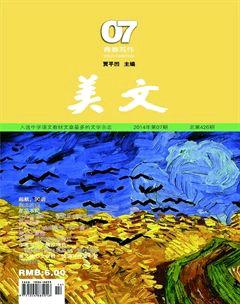那些記憶中的炊煙歲月
史浩霞
在記憶的某個角落,炊煙總會和著青天飛翔,以緩慢抑或“強勁”的節奏。
小時候,曾經把炊煙的舞姿想象成各種樣子,緩緩的盤旋狀的像藤蘿,這時我就會進一步去想:天空中會不會真的生長著綠色的藤蘿呢?在風中不斷分散又聚合的,我曾把它想象成浴血的鳳凰,或者從煙囪中冒出的小宇宙,這樣想著,煙囪又成了霍金筆下的“黑洞”——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出口。思緒就這樣一直隨著炊煙在上升的姿態變換節奏,一會兒發現煙囪中冒出了濃濃霧靄;一會兒發現煙囪中飛出了巫婆的鬼臉;一會兒又發現煙囪中升起了朵朵白云和綿羊……
總之,煙囪成了我眼中的萬花筒,我想要什么,它就能變出什么。這時的炊煙是神奇而可愛的。在藍天下,隨太陽升起,隨大紅公雞的鳴叫悠悠地發音,緩緩地鳴叫,在夕陽日暮下淺淺地升騰,裊裊婷婷般隨著暮歸的鴉雀和羊群降落樹梢,淌過溪流,又隨上升的夜暮飛離枝頭,像更高的星空和月光飛去……這樣的節奏和美,現在想來仍像甘醇的美酒,久久令人回味。
長大后,發現炊煙就是炊煙,它只是一種有色有味的氣體,可以隨著風向變換各種姿態和節奏。控制他的生命的并不是日出或者日落,而是人類的慣常的饑餓。那不停的在風中變換的姿態也并非能生出多少“傳奇”或者想象,姿態也只能是姿勢變化所呈現的不同形態,并非具有幻想般的氣質和境界。煙囪也只是煙囪,只是供炊煙冒出的口,就如人行走的道路或者門。并非幻想意義的黑洞或者滋生宇宙和另一個世界的窗口。但獨自面對著漆黑的煙囪,我還是能在這個現實的黑洞中發現幻想的節奏——我那形象思維的幻想的小宇宙。
此時的炊煙沒有了兒時的魔力,它已變得蒼老而瘦弱,就像我的村莊和母親。此時的炊煙漸漸被鎮子里建起的幢幢高樓所湮沒,變得渺小和慘淡了,就像兒時暈散在村莊夜空的點點燈火,總讓人想到弱不禁風或者捉襟見肘的形象,大有秋風掃落葉之悲涼。炊煙似乎慢慢變懶了,雞叫的時候它沒有醒來,日落的時候,它也沒有升起。我驚奇地問母親:“為什么炊煙不按時上班了?”,母親笑著說:“現在高科技了,都用電磁爐了,省時省力又環保,一會飯就做好了……”可不知怎的,我老覺得鐵鍋炒的菜香。母親說她也這么覺得。
除此之外,天空似乎也在變小,變矮,變得沒有活力了。這樣想著,我不禁啞然失笑:“難道天空也會像母親那樣變老嗎?老成駝背的石拱橋,老成干癟的河流和乳房,老的四季不變,雨雪不分,長發斑白嗎?”
又想到近些天盤旋天空的霧霾,想到自己置身的城市,少見炊煙而遍布“炊煙”與“濃霧”的城市,行走在車水馬龍中的我,湮沒在幢幢高樓中的我……是的,我已身處遠方,離故鄉和炊煙越來越遠了……
我身處的城市是一個遠方,而故鄉的炊煙又是另一個遠方,它們是我的遠方。而我的遠方,我確信炊煙和天空都不會失去記憶。
村莊的上空依舊會升起炊煙,升起各種思維和記憶的姿態。隨著日出和日落的節奏,變換而又諧和。變換出想象和溪流,變換出歲月和記憶的酒;諧和即為和諧:一種縈繞在心頭的神圣與寧靜。而那無限流動著的,是高天里的闊云,山莽間的羊群和道路;至于凝固,我想它是一種狀態:如炊煙輝映天空,萬里無云周山靜;如夕陽掛枝頭,家家戶戶燈火通明;又如老樹扎根泥土,任爾東西南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