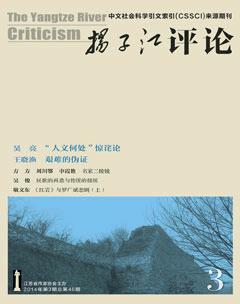艱難的偽證
王曉漁
艱難的偽證
王曉漁
韓少功先生把《革命后記》稱作“艱難的證詞”,認真讀過,深感對之作出評論是艱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章中的問題實在太多,幾乎每段都有存疑之處,無論在事實還是在邏輯層面,都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如果一一討論,可能篇幅會比原作多出許多。比如文章用300字講到解放軍進入上海的情形,王彬彬先生用了2000多字做了補充①,篇幅是前者的七倍。二是雙方辯論空間是高度不對稱的,韓少功表達自己觀點的空間,遠遠大于反駁其觀點的空間。這里所說的空間不是篇幅,而是指“尺度”。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很多證據無法出示。所以,本文只能“避重就輕”,重點分析這份證詞無法自洽之處。
沒有“前傳”,何來“后記”
“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關鍵詞,從辛亥革命到“國民大革命”到共產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貫穿始終。即使改革開放,也被視為“新的偉大革命”。但是,“革命”又包含著不同的含義,比如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如果放到世界范圍內,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也有著根本區別,阿倫特專門撰文分析兩者差異②。抽象地討論“革命”,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討論者理解的“革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你說革命有暴力,他說有“天鵝絨革命”;你說革命之后有烏托邦,他說革命之后有革革命;你說革命是革天命,他說革命是革人命。
《革命后記》主要聚焦于“文革”,“文革”和革命是什么關系?韓少功以修辭游戲的方式回避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表示“文革后記”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革命后/記”,“文革”不屬于革命;一種是“革命/后記”,“文革”屬于革命。但是,這不等于韓少功沒有自己的立場,他沒有把題目定為《文革記》,而是命名為曖昧的《革命后記》,正文時常把“文革”視為革命一部分,傾向于“革命/后記”的論述。
革命只有“后記”,沒有“前傳”。“文革”是如何發生的?《革命后記》很少涉及。30年代的肅反、40年代的整風、50年代的反右,這些革命的“前傳”都被略過了。但是,沒有“前傳”,何來“后記”?“文革”不是在1966年5月16日憑空產生的,有著漫長的演進過程。韓少功在《革命后記》開篇表示,自己的全部記憶僅僅涉及“文革”,“充其量寬延至前后的三十年,即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后半場”。如果《革命后記》是一本回憶錄,自然沒有問題,可是個人回憶在整篇文章里的篇幅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個人感想,用感想代替記憶,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判斷。整篇文章有200多處注釋,包括很多歷史類著作,內容遠遠超出了個人回憶的范疇。
最后討論“革命能否帶來公平”時,韓少功以“抒情的必然性”的方式簡短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他講到一位老大姐自陳,游擊隊在黑燈瞎火中常會來睡上一把,但老大姐不覺得這是羞恥。這時,韓少功表示:“在隨時都可能掉腦袋的那年月,擁抱是對每一個生命的憐惜,更像戰友之間悲傷的提前訣別。”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像這位老大姐一樣“思想進步”?女性是否有權利反對這種獨特的訣別?如果有女性反對,會不會變成“反革命”?在韓少功那里,這些問題似乎不存在。
韓少功接著講到革命中的很多“污垢”,然后總結:“革命就是狂飆,就是天翻地覆,就是破壞與剝奪,就是不得已的恐怖暴力,也是走投無路之后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必有誤傷,必有冤屈,必有污穢,必有兇狠,必有失控和混亂……”這種邏輯把必然性等同于正當性,因為必然發生,所以必須接受。因為隨時都可能掉腦袋,所以必須隨時睡上一把?必然性是不是虛構的?必然性屬實,就等于正當性嗎?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就成了“凡是發生過的,都是合理的”。韓少功似乎覺得這樣不太妥當,表示“與其說這一切值得夸耀,毋寧說更值得悲憫”。誰來悲憫?需要悲憫的是誰?韓少功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接著寫出一段抒情的文字:“正是一種令人淚流滿面全身發抖喘不過氣來的痛感,才能擴展人們對艱難和悲壯的理解,使致敬一刻像大海那樣深廣而寧靜。”
沒有超越的“超越左右”
在《革命后記》中,韓少功似乎采取了超越左右的立場。他對“文革”有稱贊也有批評,他批評左右合營“代價公司”,他認為“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個趔趄的連體人,栽進了同一個坑”。“超越左右”是當下思想界難得的共識,但這并未促成不同觀點之間的溝通,因為言說者都認為自己是“超越左右”,對方陷入派別之見。“超越左右”成為政治正確,用于自我合法化。
“左”與“右”,是一對錯綜復雜的概念。在中國的語境里,“左翼”不等于“左派”,“右翼”不等于“右派”。簡而言之,“左翼”帶有褒義,多指權力的批判者;“左派”屬于中性兼有貶義,多指權力的附庸者甚至是主導者;“右翼”帶有貶義,多指國家主義者,“右派”屬于中性兼有褒義,多指持不同意見者。
韓少功使用褒義的“左翼”和貶義的“右翼”,講到“左”多為“左翼”如何,講到“右”則是“右翼”如何,這一詞語的選擇已經說明了他的立場。“左翼”的命名將“左”正當化,“右翼”的命名將“右”污名化,“超越左右”只是占據道德高地。這樣說像是繞口令,不妨以《革命后記》為例。韓少功指出,稱贊“文革”的一方懷念當年的“平等”,批評“文革”的一方斥責當年的“平均主義”,“雙方大體上確認了當年的一種‘平’”,所以是“雙頭的連體人”。這個邏輯非常奇怪,仿佛只要有了“平”字,不管雙方理解的“平”是不是有差異,不管雙方對“平”持何種態度,雙方都是一樣的。于是,反對“平均主義”,被等同為反對“平等”。這是“超越左右”嗎?
“平等”和“平均主義”不能完全等同,即使同樣冠以“平等”之名,也存在根本差異。孟德斯鳩說過:“在共和政體下,人人平等;在專制政體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體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為人就是一切;在專制政體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為人一錢不值。”③在奧威爾的《動物農場》里,“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④批評“文革”的“平均主義”,正是批評那種人人接受奴役的平等,批評“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平等。批評者認為“文革”是“平均主義”,與稱贊者認為“文革”是平等的烏托邦,兩種觀點截然不同,韓少功卻將兩者混同起來。
在韓少功那里,毛澤東“鼓勵學生鬧事和工人奪權,容許造反派自由結社、散傳單、燒檔案、封報館、扛機槍、占領官府大樓、全國免費大串聯”,被稱為“零障礙和無限度的‘民主’和‘自由’”。他表示:“一個西方記者如果此時在中國人面前說教‘民權’,肯定覺得自己班門弄斧。”韓少功使用的“鼓勵”和“容許”兩詞,已經說明那些行為只是“奉旨造反”,與“民主”、“自由”、“民權”沒有關系。但韓少功把“奉旨造反”等同為“民主”、“自由”、“民權”,成功地把后者污名化。
韓少功表示,“把‘平等’污名化”,某些知識精英“比黑道走得更遠”。他似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們若不是缺少一種屬于自己的人渣辭典,那就是他們經常不知自己在說什么,對自己找不到北。”不知這個說法是否適用于“把‘民主’、‘自由’、‘民權’污名化”的某些知識精英?我所關心的是,“把‘平等’污名化”的主要是誰?是某些知識精英,還是那種以“平等”之名建造等級金字塔的烏托邦實踐?
選擇性記憶
與其他贊美“文革”者不同的是,韓少功對“文革”有稱贊亦有批評,經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敘述模式。把一個已經被否定的對象改寫成“理性中立客觀”的五五開,這是最為高明的辯護方式。
韓少功這樣講述“‘文革學’不大提及的一面”:“一方面是暴虐,一方面卻不乏熱情、爽朗、忠厚甚至純潔——至少就大多數人而言,與通常的土匪、黑幫、軍閥、占領軍、綠林亂黨不同,他們的暴力與物質利益毫不相干。即便在暴尸街頭之際,也鮮有人哄搶商店、打劫銀行、收取保護費、輪奸婦女、綁票勒索、吃飯不給錢、瓜分古董與金條等抄家所得……這些案情哪怕在當今對‘文革’最大規模的揭露之下也極為罕見,幾乎聞所未聞。”
“即便在暴尸街頭之際,也鮮有如何如何”,這種句式讓人讀得心驚膽戰,“暴尸街頭”這種恐怖的景象在“即便”之下,變得無足輕重。這里暫且不去引用歷史文獻,一一列舉韓少功筆下“烏托邦”的虛幻,韓少功自己提供了反證。他講到自己認識的一位姑娘,揣著五塊錢出門,兩個月后回來,夸耀衣袋里還有七塊。“吃飯不給錢”在串聯中非常常見,韓少功為何“幾乎聞所未聞”?或許,在他看來,不是“吃飯不給錢”,而是“吃飯不要錢”。“吃飯不給錢”是道德敗壞,“吃飯不要錢”說明社會風氣良好。至于經濟學常識“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韓少功是不用考慮的。那位姑娘的兩塊錢來自何處?韓少功說,“不是借自沿途的紅衛兵接待站,就是來自好心人的捐助”。那位姑娘后來有沒有歸還紅衛兵接待站的借款?韓少功沒說。
對于自己描述的“烏托邦”,韓少功也覺得過于絕對,補充說,“當然,搶軍帽或撬單車或有所聞,極少數人渣趁火打劫一類也不能排除,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會有”。通過“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場災難被描述成五五開,又通過“大多數人……,極少數人渣……”,五五開又變成了三七開,三分“人渣”,七分美好。在韓少功的描述下,“大多數中國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較少,他們享受‘領導階級’的地位優越”、工人和農民“一般沒有挨批斗的經歷,沒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區”。此前的三年大饑荒呢?此后農民為何又要冒著坐牢危險私自簽署包干協議?
韓少功表示自己“無意粉飾什么,只是指證圣徒化與警察化的一樣陰陽臉”。如果像阿倫特那樣探討“平庸的惡”,可以彌補反思“文革”中的不足。但是,《革命后記》呈現出的景象,更像是利季婭筆下的蘇聯:在1960年代,“報上直接或間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來越多。比如,當然,斯大林處決了很多無辜的老布爾什維克,但他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科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這就像,’一次阿赫瑪托娃說,‘承認他是吃人的惡魔,但口琴吹得好。’)”⑤
韓少功反對對“文革”的“宮廷化”、“道德化”和“訴苦化”。我同意這些觀點,贊同更多從制度和文化的角度進行反思。但在《革命后記》中,不乏稱贊好人好事的“宮廷化”,也不乏動輒痛斥“人渣”(不僅趁火打劫者被視為“人渣”,與韓少功觀點不同者也被視為“人渣”)的“道德化”,更不乏對美國的“訴苦化”。韓少功認為從“離婚、薪水、疾病、稿費、房產、后人吃啥喝啥”討論領袖沒有意義,是“長舌婦和民間神探”,但在討論大饑荒時,他卻引用了一段“據說”:“據說,正是在這一年的某日,毛澤東在衛兵面前失聲痛哭,決定不再吃肉,與全國人民共度難關,直到自己患上水腫病,一年后瘦了十多斤。”記載與之不同的《毛澤東遺物事典》⑥,卻被略過了。這讓人懷疑,韓少功反對的只是對“文革”持否定態度的“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
類似的選擇性記憶比比皆是,以致韓少功并不諱言“選擇性記憶”。他講到現場觀看中央芭蕾舞團《紅色娘子軍》的情形,“鼓掌者們在久違的溫暖前夢醒,在一種卑賤者解放的絢麗天地里暈眩和飄飛”。他對樣板戲的造神宣傳和革命圖標化一筆帶過,然后說:“這些觀眾面對悲愴的樂浪,激越的旗幟,純潔無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陽光造型,就沒有一次熱淚盈眶的權利?”最后,他說,“哪怕它也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可是針對知識分子們對“文革”的回憶,韓少功又說:“他們要做的是理解、溝通、說服以及協調共進,不是強加于人和視而不見,滿足于悲情的自產自銷,成為另一個祥林嫂。”既然是“悲情的自產自銷”,又怎么是“強加于人”?
在韓少功的選擇性記憶里,“文革”前夕,美國水深火熱,“夜不閉戶和路不拾遺在中國很多地方卻成為尋常”。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聽起來很美好,有時卻是家徒四壁、路有餓殍的代名詞。
反西方的西方中心
美國(以及“西方”),是韓少功的心結。在講述“文革”為主的《革命后記》里,美國出現的次數幾乎不亞于中國。對“文革”作全面辯護是困難的,韓少功放棄了這個打算,而是表示“文革”有錯,但美國也有錯。
講到“文革”禁區,韓少功稱“不失為一種務實的敲槌禁聲”,理由是美國以法案方式擱置“抽屜問題”,歐洲在種族、排猶主義上“封殺異議,絕無自由”。韓少功認為“文革”與冷戰對手形成同構,“差不多就是美國麥卡錫運動的鏡像,一種逆向的高倍數放大”。他稱歐羅巴人曾經參加燒死女巫的起哄,為何不能理解中國“文革”中的雙重人格?韓少功還批評美國電子監聽大網“鬧得四面八方都隔墻有耳”,質疑“美國的‘大腳偵緝隊’是不是也要挨門查戶口”。在他看來,美國和英國在三四十年代嚴打金融自由和厲行計劃分配,幾乎是上門打劫神圣私產;媒體市場化和“水軍帖”一樣,“一手遮天并無太大區別”;在美國惹惱非裔或猶太裔,“警察立馬拎著手銬上門”。中國那些要死要活獻身革命者,“一般來說并無槍口威逼,不是迫于美國那樣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隊伍、最多的監禁場所、最昂貴的司法開支”。韓少功還列出這么一組數字:美國因為槍支管控不力導致的死亡率“接近兩個‘文革’”,陷入歐債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希臘自殺率“遠超‘文革’”,空氣污染導致的死亡率“竟是‘文革’的數十倍”……
這些描述有太多歧義。禁止討論“文革”與反對種族歧視是一回事?這就像莫言先生把言論審查和機場安檢等同視之。一個國家(或地區)歷史上出現過錯誤,就意味著他們要理解這個錯誤?美國有戶籍制度和居委會?大腳偵緝隊挨門查戶口從何說起?政府介入市場,就是“上門打劫私有產權”?美國警察拎著手銬上門之前,需要哪些程序?中國沒有發生過“反右”?“文革”中“受害者”的死亡率可以等同于其他死亡率?
韓少功的這些觀點似乎是在“反西方”,卻又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因為西方也有問題,所以“文革”的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經常表現為兩種形式:當有人主張學習西方之長處,他會說西方也有短處;當有人說中國有問題,他會說西方也有問題。比起“以西方之是為是”,這種“以西方之非為是”是更為隱蔽也更為徹底的“西方中心”。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反西方”思潮常常來自西方,是西方自我反思的產物。可是,韓少功把“他者的內部反思”當做“批評他者的武器”。這就像那個著名的笑話,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在廣場上批評美國總統,蘇聯人說,這有什么,我們也可以批評美國總統。
韓少功講述了自己訪問西方國家的創傷記憶,入境處移民局官員查驗了他的護照、簽證、訪問邀請書、旅館預訂信息之后,然后問:“有錢嗎?給我看看。”韓少功感到自己受到歧視,深感屈辱,從此明白:“一條入境閘口黃線分割的,不僅有不同制度,還有富與窮、貴與賤、高等物種與低等物種、掏得出綠票子與掏不出綠票子的。富國不是雷鋒,也沒義務當集體雷鋒,對數以億計的窮棒子展開臂膀微笑熱擁。”
韓少功與移民局官員的分歧,究竟由何而生,我無法確定。讀到這段,我想起自己入境某西方國家時,入境處官員查驗過一系列證照之后,也問過攜帶多少現金。我當時沒有聯想到自己被歧視,也沒有想到這與“富與窮、貴與賤、高等物種與低等物種、掏得出綠票子與掏不出綠票子”有什么關系,只是告訴對方攜帶的現金在不申報的金額范圍之內,就過關了。
雖然過關沒有遇到問題,但我從來就沒有認為富國都是雷鋒,也不會把西方國家視為“民主烏托邦”。民主從來沒有宣稱自己是烏托邦。民主的優點不在于它是完美的,而是承認自己是不完美的,因而建立“糾錯”機制。民主不是“人人都是雷鋒”,也不是“六億神州盡舜堯”,那種理想國的景象只能出現在嚴厲的思想改造之后。韓少功的“創傷記憶”,說明他此前對于“西方”和“民主”有著烏托邦的想象,以至于一旦在現實中面對任何“不完美”之處,價值體系立即走向過去的反面。
與“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相似,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民主烏托邦”:先把民主認定為烏托邦,一旦民主出現任何問題,就得出“反民主”的結論。烏托邦思維卻是自始自終沒有放棄的,韓少功認為五七指示“描繪出一幅比《禮運篇》更為具體和清晰的圖景”,是“實現人類全面發展的美好前景”,“不幸的是,多年后人們覺得這些說法日益飄渺”。為何有著那么美好的藍圖,現實中卻有著那么多的災難?藍圖與災難是什么關系?談到災難就是悲情,就是只講到一方面沒講到另一方面,就是缺乏深入反思?
韓少功引用薩繆爾森的“合成謬誤”,指出某種在微觀上看來對的東西,在宏觀上并不總是——反之亦然。這種提醒非常必要。如果說《革命后記》有什么價值,那就是它從各個可能的角度試圖為“文革”做出一份“艱難的偽證”,這份“偽證”因為逼真具有了精神病理學樣本的價值。
我并不贊同“告別革命”論,但革命如何被激活?需要激活的是哪種革命?革命如何對待自己的過去?《革命后記》沒有提供具有說服力的回答。
【注釋】
①王彬彬:《替韓少功補個注釋》,《南方都市報》2014年5月25日。
②[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③[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93頁。
④[英]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動物農場》,董樂山、傅惟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頁。
⑤[俄]利季婭·丘可夫斯卡婭:《捍衛記憶》,藍英年、徐振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頁。
⑥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毛澤東遺物事典》,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