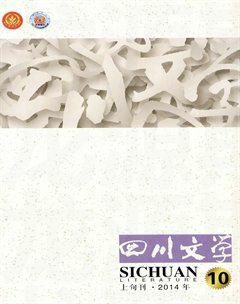我愛著,我悲傷
2014-07-13 04:57:34楊獻平
四川文學
2014年10期
◇楊獻平
我和妻子凌晨趕回家里。從西北到北京,再到邢臺,一路火車。凌晨兩點,一直蜷縮在面包車上等我們的姐夫眼睛惺忪,在昏黃燈光下與我們相互找見,一句話也沒說。司機抄近路,面包車在春天的冀南平原凌晨拼命穿越。呼呼風聲外,村莊和山崗接連不斷。四點多到家里,我邁進門檻,燈光昏黃,氛圍肅穆,父親躺在舊時炕上,身上衣衫整潔,腳蹬一雙清代官靴,頭上戴著一頂瓜皮帽,臉上蒙著馬頭紙。親戚們坐在炕上,形成一個半圓圈。袖著手的妗子說:不要哭了啊獻平,等天亮了再哭!我走到父親頭邊,想掀開看看父親。卻又不敢。母親替我掀開,說恁爹右眼一直沒合上。小姨媽說:俺姐夫是在等你們兩口子!前天晚上,馬上就不行了,叫獻平。俺為了哄他,叫聚平假裝從門口進來,說是你趕回來了。誰知道,恁爹看了看說不是獻平,是聚平。
我鼻子酸了一下,想哭。也明知道,小姨媽說這話,也含有催淚成分。可我就是哭不出來。憋了一會兒,哭聲都到嗓子眼兒了,也還是沒哭出聲。我嘆息一聲,坐在凳子上。
這是2009年3月10日凌晨,父親已經故去27個小時了。冷空氣還在南太行鄉村逗留,不一會兒,腿腳就凍麻木了。第二天一大早,按照老家風俗,要趕在陽光落地前,把左邊的門板(男左女右傳統)拆下來,再用凳子和磚頭架在屋子中央,然后把父親肉身從炕上抬過來。我和弟弟,還有幾位幫忙的叔伯和堂兄弟,分別抱了父親的頭腳和身子,一起用力,把父親安放在屋子中央的門板上。……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