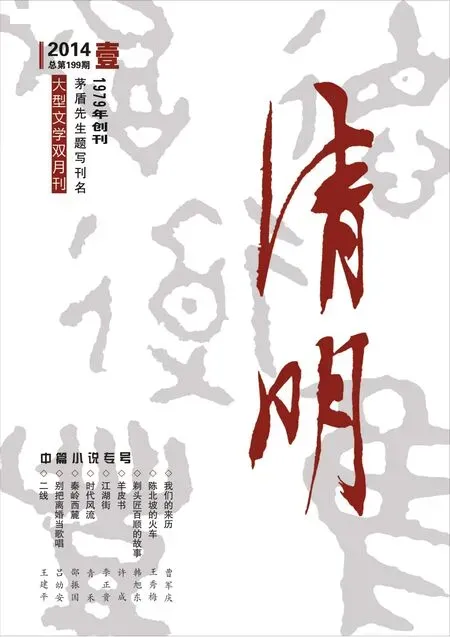剃頭匠百順的故事
韓旭東
剃頭匠百順的故事
韓旭東

一
寫這篇小說之前,我一直想寫的是煙葉王韓伯良的故事,是一個(gè)電話改變了我的想法。
夏天,我在玉米地里鋤草,接到了一個(gè)電話,浙江海門打來的。浙江那個(gè)地方,我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我在家做針頭線腦一樣的生意,更沒有業(yè)務(wù)和那邊有往來,能是誰呢?
電話里說,我是賢粹。
哦,想起來了,賢粹啊。
賢粹和我一樣,姓韓,賢這個(gè)字是我們的輩分,粹是名,就像我身份證上的名字韓賢志是一樣的。我們都是從一個(gè)名叫二韓的村子里走出來的。
賢粹小我一歲,一九九〇年的春天,我和賢粹一起出門打工,我去了北京,賢粹和一伙人去了浙江。一九九〇年北京開亞運(yùn)會(huì),我被北京警察驅(qū)趕回了老家。而賢粹一去浙江十多年都沒有音訊。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都還年輕,我偶爾會(huì)想,賢粹會(huì)在哪里呢?他人還好嗎?這樣的想法也就是在腦子里一閃而過,我結(jié)婚生子,被生活的重負(fù)壓得喘不過氣來,別說賢粹了,就是有美女從我跟前走過,我都懶得抬眼皮看她一眼了。
二〇〇四年,我借了幾十萬塊錢在街上開了一個(gè)家電門市部,生意冷落得讓人絕望。好在那個(gè)時(shí)候我對(duì)寫小說有著滿腔的熱情,我天天趴在電腦上搗鼓文字,并不是十分在意生意的好與壞。就是這個(gè)時(shí)候,有人找我,白白凈凈的一個(gè)男人。我不認(rèn)識(shí)他,對(duì)方卻開口了。
哥,你不認(rèn)識(shí)我了?我是賢粹啊。
我的天,實(shí)在是嚇了我一跳。
我說賢粹,你是賢粹?
我是賢粹。
就這樣,離開二韓十五年之后,賢粹回來了。
賢粹在南方承包工程,多大的工程他沒說,在吃飯的時(shí)候賢粹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一邊和我舉杯一邊抹眼淚。我知道,這都是思鄉(xiāng)的淚水,這都是喜悅的淚水。
賢粹說他在浙江的時(shí)候,一個(gè)人會(huì)對(duì)著電腦,反反復(fù)復(fù)地輸入二韓人的名字,他想在網(wǎng)上看到有關(guān)二韓的信息,有關(guān)二韓人的信息。終于有一天,他在網(wǎng)上看到了我的一點(diǎn)文字,那些文字里,我提到二韓,提到二韓里的某個(gè)人,某些事,他才確信,我就是二韓的韓賢志。
我說,要這么麻煩嗎?浙江又不遠(yuǎn),咱村子里每年都有人去浙江打工,來來回回的,方便。
賢粹搖頭說,哥,我是發(fā)過誓的,不混出個(gè)模樣,絕不回來。
哦。
我能從賢粹的言談舉止以及他的衣著扮相看得出來,賢粹應(yīng)該混得不錯(cuò)了,他既然回來了,應(yīng)該是混到了他心里想要的那個(gè)模樣了。
賢粹在二韓住了一周,走的時(shí)候,丟下一筆錢給村長(zhǎng),要村長(zhǎng)把村南頭的路給鋪一下。那條路是我們村子里往外走的唯一通道,幾百年的土路了,如今還是土路,賢粹從浙江開車回來,因?yàn)橄掠辏囎又荒芡T阪?zhèn)子上,剩下的六里路,要像我們當(dāng)初上學(xué)一樣,用腳步去丈量。
賢粹回了浙江,路依然沒有修。賢粹也沒有問過。
賢粹打電話來,不是說路的事,這個(gè)事他似乎忘了。或許他沒有忘,他是不想去計(jì)較了,他把錢丟下來,就已經(jīng)足夠了,剩下的事,都和他無關(guān),他是懶得問了。
賢粹說的事和我有關(guān),和我的小說有關(guān),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賢粹說,哥,你寫的那個(gè)《張大蘭的春天》,怎么到現(xiàn)在也沒有個(gè)結(jié)果呢?
我說,你在哪看到的?
《張大蘭的春天》是我發(fā)在一個(gè)發(fā)行量不大的文學(xué)雜志上的,別說發(fā)行量不大了,就是發(fā)在大刊上,還有誰去看小說?沒想到賢粹做了老板,還有閑情關(guān)心小說。
賢粹說,你哪能讓張大蘭一個(gè)女人受這樣的煎熬呢?她應(yīng)該有性生活,有她應(yīng)該得到的幸福。
是的,我在《張大蘭的春天》里,寫了張大蘭的丈夫褲襠里有了毛病,張大蘭一直盼著把丈夫的毛病給治好,張大蘭想了很多辦法,也用了一些偏方,但是,我并沒有寫出結(jié)果。
賢粹說我不厚道。賢粹說,你這樣寫,不僅張大蘭著急,你不是讓我這樣的讀者也跟著著急嗎?
賢粹這樣說,我明白了賢粹打這個(gè)電話的用意。賢粹關(guān)心的不是張大蘭幸福不幸福,張大蘭給丈夫治病這一段,是和賢粹家有關(guān)系的,我在寫那篇小說的時(shí)候,是有顧忌的。別人家的私事,你是不能隨便寫的,萬一牽扯到人家不高興的事了,人家找上門來,喝酒的散碎銀子沒有掙到不說,還落下一堆麻煩,不值得。
賢粹在電話里和我聊小說,聊二韓,我聽得出來,他是想讓我寫一寫有關(guān)他家里的事情。說實(shí)話,我的文字里幾乎沒有提到過賢粹這個(gè)家庭里的人和事,沒有提到的原因,一是賢粹的父親以及他祖上的事跡實(shí)在是乏善可陳,如果不是賢粹現(xiàn)在發(fā)達(dá)了,有關(guān)他這個(gè)家庭在二韓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jì)的;二個(gè),賢粹的父親在二韓剃了幾十年的頭,剃頭匠的生活,我就是再善于發(fā)掘,也發(fā)掘不出讓賢粹看到了之后感到滿意的故事,我怎么去寫?沒法寫。
但是,現(xiàn)在不一樣了,現(xiàn)在的賢粹發(fā)達(dá)了,我寫了那么多有關(guān)二韓的人,有關(guān)二韓的事,居然沒有提到賢粹這個(gè)家族,賢粹是不能接受的。
賢粹說,你應(yīng)該把張大蘭丈夫的毛病怎么治好的寫下來,這個(gè)事你肯定是知道的,你知道了,怎么不寫呢?
我在電話里沉吟了一下,說,賢粹,照實(shí)寫嗎?
賢粹也在電話里沉吟了一下。顯然,我這樣問,賢粹有了顧慮。賢粹是這樣給我說的,哥,你是作家嘛,你看著寫吧。
事隔兩個(gè)月,我依然沒有動(dòng)筆,中秋節(jié)前,我收到一份快遞,賢粹寄來的,浙江海門的特產(chǎn),一件繡衣,上面繡了我夫人的名字,不僅有山有水,還彩霞滿天的。禮物太貴重了,這會(huì)讓我備受壓力,這小說我還能寫好嗎?試試吧。
如果不是和賢粹通了這個(gè)電話,有關(guān)賢粹家的事,我會(huì)在以后的文字里或多或少地寫上幾筆,畢竟,我對(duì)賢粹這個(gè)家族的歷史還算是了解的,只要我的文字去忠實(shí)地記錄賢粹家族的歷史,忠實(shí)于賢粹家族的歷史生活,不去為了迎合讀者的閱讀趣味而胡編亂造,我相信即使賢粹看到這些文字,他也是無話可說的。現(xiàn)在的問題是,賢粹主動(dòng)提出要我寫寫他的家族并且告訴我看著寫吧,我還能無所顧忌嗎?
二
還是從賢粹的父親百順說起吧。
百順是個(gè)剃頭匠。有關(guān)百順跟誰學(xué)的手藝,到底是自學(xué)成才,還是投了師傅,在二韓的爭(zhēng)議很大。有人說百順沒有老師,百順去趕集,看到街頭有剃頭匠,給人剃個(gè)腦袋就能掙一毛錢,百順跑到城里買了一套家伙就干上了。持這種說法的人也不是沒有依據(jù),百順爹的腦袋就能證明這個(gè)說法,以前百順爹剃頭也是每個(gè)月等后村的侯七來剃一刀,二韓人的腦袋都是侯七在剃。侯七在二韓剃一年頭,二韓人按照人口算,一年下來一共給侯七不足一百塊錢,準(zhǔn)確的數(shù)字是七十一塊八毛錢,村會(huì)計(jì)韓來福的賬本上有記錄。侯七在二韓剃頭,吃飯是輪流來的,一年到頭從第一生產(chǎn)隊(duì),吃到第六生產(chǎn)隊(duì),往復(fù)循環(huán),誰家也跑不掉。剃頭的錢也不用侯七挨門挨戶地去要,到年底了,村里核賬,直接從賬面上扣除。這一年來福到年底結(jié)賬,百順爹有說法了,百順爹說,來福,這個(gè)剃頭錢你不能扣我這么多了,我有三刀沒有讓侯七剃。
來福看著百順爹的腦袋說,你這個(gè)頭不是侯七剃的,那是誰給你剃的?
百順爹說,你別管誰剃的,我就是沒讓侯七剃。百順爹指著自己的腦袋說,你仔細(xì)看看,侯七剃過這樣的頭嗎?
百順爹說的這樣的頭是指發(fā)型。
的確,來福承認(rèn),侯七在二韓是沒有剃過這樣的發(fā)型,侯七剃過的腦袋,從腦門子挨著往后剃,留在腦袋上的頭發(fā)茬子不足一厘米。百順爹的腦袋不是,百順爹腦門上的頭發(fā)留得很長(zhǎng),從鬢角到腦袋后面打掃得干干凈凈的。這樣的腦袋在二韓就顯得有點(diǎn)與眾不同了,如果不是百順爹這樣說,來福還真沒有注意到他的腦袋。來福有點(diǎn)奇怪,這些年二韓人的腦袋都是侯七打理的,百順爹不會(huì)為了一個(gè)腦袋去誤工請(qǐng)假到街上剃頭吧?再說,這一點(diǎn)賬面上體現(xiàn)得很清楚,百順爹出工是滿勤。
來福說,不管是誰給你剃的頭,這個(gè)賬你要認(rèn)吧,錢不給侯七,也是要給別人的。
百順爹說,不用給錢。
來福不高興了,來福最討厭愛占小便宜的人,來福計(jì)算過,一個(gè)人剃一次頭,不足一毛錢,一年下來也就塊兒八毛的,你怎么能張口說不給人錢。
百順爹說,是不用給的,這個(gè)你不要操心,保證沒有人找你要錢。
來福又往百順爹的腦袋上仔細(xì)瞅了瞅,這一瞅不要緊,來福像是有了新發(fā)現(xiàn)。百順爹的發(fā)型似乎在哪里看到過,在哪里呢?來福想了想,是的,見過,在電影里,前些天放的那個(gè)電影叫什么來著?里面有個(gè)壞蛋,斜挎著盒子槍,領(lǐng)著鬼子進(jìn)村,那個(gè)人就是這種發(fā)型。
有了這個(gè)新發(fā)現(xiàn),來福緊張了。
來福問,最近你家里是不是來了什么人?
來福是黨員,警惕性高,階級(jí)敵人隨時(shí)都可能混進(jìn)我們的人民群眾中。
百順爹沒有想這么多,百順爹以為,會(huì)計(jì)來福和侯七家是親戚,沒找侯七剃頭,來福是不高興了。
百順爹說,剃個(gè)頭像審賊一樣,不就是沒找侯七嗎?
來福不是這樣想的,來福家一屋子人,都是等著結(jié)賬的。來福說,今天不結(jié)賬了,明天吧。
來福說不結(jié)那就不結(jié),在二韓,除了韓伯祥之外,就是來福說了算。
當(dāng)然,來福是虛驚一場(chǎng),韓伯祥對(duì)百順爹的腦袋早就有所覺察,作為一個(gè)大隊(duì)里的領(lǐng)頭人,別說一個(gè)人的腦袋有別于他人,在他管轄的范圍之內(nèi),哪怕是一棵草長(zhǎng)出異樣來,韓伯祥也記在心里,要不怎么當(dāng)這個(gè)大隊(duì)書記。
百順爹的腦袋是百順給打理的,那么,百順有沒有投師傅呢?
有一個(gè)版本說百順是有師傅的。
說百順有師傅,也是有根據(jù)的。百順眼看快三十了,還沒有娶到媳婦,百順爹為這個(gè)事,每逢年底,都要把自己家養(yǎng)的雞送到媒人何六女人家里。百順爹對(duì)何六女人說,有點(diǎn)毛病不打緊,只要下雨知道躲雨,是個(gè)女人就行。問題是,但凡知道下雨往屋子里躲雨的女人,都不愿嫁到百順家。不愿嫁給百順,不是說百順人長(zhǎng)得丑,百順除了腦袋習(xí)慣性地偏在左邊之外,渾身上下真沒有什么毛病。也不是說百順家窮得揭不開鍋,要說窮,誰家不窮?在二韓,一天三頓煙囪能正常冒煙的,沒有幾戶人家。不嫁給百順是因?yàn)榘夙樇規(guī)纵呑尤硕际菃蝹鳎苋似圬?fù)都不說了,萬一到了百順家沒能給這家人留個(gè)后,這個(gè)責(zé)任承擔(dān)不起。何六女人對(duì)百順爹說,你簽個(gè)字,不生男孩,你別抱怨我,別抱怨女方,我就給你當(dāng)這個(gè)媒人。
百順爹不簽字,也就沒有女人嫁過來。
等到了這一年把秋季莊稼收了,把麥子種下了地,快接近年底的時(shí)候,百順爹找到韓伯祥,說是給百順請(qǐng)假,百順要走親戚了,要去河南他姨娘家。
百順家一年到頭在生產(chǎn)隊(duì)干活,基本都是滿勤,這個(gè)時(shí)候要請(qǐng)假,韓伯祥不能不放人。
韓伯祥還跟百順爹開了個(gè)玩笑,說你也真是的,想他姨娘了,你去,你叫百順去接,百順能接來嗎?
百順爹不幽默。百順爹說,不是去接他姨娘,是去看看。
韓伯祥沒有開玩笑的興致了,說,去吧去吧。
誰知道百順這一去河南兩年沒回。
百順三十了,是個(gè)大勞力,一個(gè)大勞力不在自己生產(chǎn)隊(duì)干活,跑到外面沒有了音訊,韓伯祥不高興了。韓伯祥給百順爹下了最后通牒,百順要是不回來,二韓的戶口就給他銷掉。
韓伯祥這個(gè)人很少生氣的,今天把話說到這個(gè)份兒上,看來是真的動(dòng)怒了。
百順爹連忙給河南那邊去信。百順爹在信上說,娶沒娶到女人都不打緊,要趕緊回來,要是回不來,戶口給銷掉了,也等于二韓沒有百順這家子人了。
百順是春天回來的,百順回來的時(shí)候,身后真的跟著個(gè)妮子,一開口就是河南腔。
百順爹高興,管她是河南人還是河北人,是個(gè)女人就行。
二韓人也以此為依據(jù),認(rèn)為百順在河南學(xué)會(huì)了剃頭的手藝,這種推測(cè)應(yīng)該是靠譜的,畢竟,二韓人對(duì)百順還是有所了解的,百順從小到大離開二韓就這么些日子,這個(gè)手藝在外邊學(xué)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問題在于,百順這個(gè)手藝是跟誰學(xué)的呢?他的師傅是誰呢?百順不說,誰也不知道真相,所有的版本都是二韓人推測(cè)出來的。
三
因?yàn)榘夙樣刑觐^的手藝,韓伯祥決定今后二韓人的腦袋就交給百順收拾了。
韓伯祥這個(gè)人毛包胡子,半個(gè)月不光臉,離遠(yuǎn)看,你看不出個(gè)鼻子眼來。侯七一個(gè)月來一次,如果趕上農(nóng)忙,或者是陰雨天來不了,韓伯祥都恨不得找把鐮刀把自己臉給光了。問題是,鐮刀割莊稼行,割胡子就不行了。
侯七每次晚來兩天,韓伯祥就給侯七臉子看。韓伯祥說,你算過日子嗎?今個(gè)是幾了。侯七自知理虧,訥訥地說,下次,下次一定按時(shí)來。韓伯祥說,你以為你跟來福有親戚啊,你跟來福有親戚,你也不能白拿錢吧?雖然這樣說了侯七,遇到特別的日子,侯七還是不能按時(shí)來,如果有合適的人選,韓伯祥早就想換人了。現(xiàn)在好了,百順會(huì)剃頭,乖乖,這多好,多方便。
韓伯祥到百順家,要百順給他剃頭,百順說自己不會(huì)剃頭,他沒有給人剃過頭。
韓伯祥不高興了,問百順,你爹的腦袋是不是你剃的?
百順說,是。
韓伯祥說,你能給你爹剃,不能給我剃,我和你爹的腦袋有什么不同?
百順說,俺爹是俺爹,你是你。
韓伯祥鬧不明白了,是,你爹是你爹,我是我,不是一個(gè)人,問題是,我剃頭給你結(jié)賬的,就像侯七一樣,不白干。
百順說,叔,我真沒給人剃過頭。
韓伯祥說,你爹不是人?你能給你爹剃,怎么就不能給我剃,怎么就不能給二韓人剃?
韓伯祥是真生氣了,一屁股坐在百順家的屋子里,對(duì)百順說,剃。
韓伯祥生氣,百順爹是看在眼里了,百順爹勸百順,剃,給你叔剃。
百順說,我真不會(huì)剃。
百順爹說,你咋不會(huì)呢?你看看你給我剃的多好,就照我這個(gè)樣子剃。
韓伯祥也說,對(duì),就照你爹的那個(gè)樣子剃,剃成什么樣我都不怪你。
只能剃了。
百順操起家伙在韓伯祥的腦袋上拾掇起來。只一袋煙的工夫,百順說,叔,好了。
百順家沒有鏡子,給韓伯祥剃成什么樣子,韓伯祥也不知道。頭剃了,臉還沒有光,對(duì)韓伯祥來說,光臉才是最關(guān)鍵的部分。
韓伯祥對(duì)百順爹說,嫂子呢?你讓嫂子燒點(diǎn)水,我光臉。
百順娘就去燒水。等把水端來,百順說,叔,光臉你得睡下。
韓伯祥沒明白百順是個(gè)什么意思,就看看百順。
百順說,叔,你睡倒。
韓伯祥用詫異的眼光看著百順,他想不通,為什么光臉要睡倒。
韓伯祥問,睡哪里?
百順指著旁邊一個(gè)槐樹做成的簡(jiǎn)易床說,你就睡床上吧。
韓伯祥快五十歲的人了,第一次聽說光臉要睡在床上。韓伯祥問,能不睡嗎?
百順說,我給人光臉都是睡倒的。
哦,韓伯祥想殺豬捅屁股各有各的殺法,百順叫睡倒咱就睡倒。
韓伯祥躺在床上,百順把熱毛巾焐在韓伯祥的臉上,過了一會(huì),百順搬個(gè)小凳子坐在床頭,開始給韓伯祥光臉。
要說百順這光臉的手藝真不賴。百順從韓伯祥的脖頸開始下刀,刀子經(jīng)過之處,韓伯祥都能聽到哧哧的聲音,重要的是,百順的手輕,不像侯七。侯七一年給韓伯祥光十二次臉,其中有六次會(huì)把韓伯祥的臉劃傷。劃傷了,侯七也是一臉的惶恐,對(duì)著傷口呸呸呸地吐口唾沫,然后給韓伯祥說,書記,唾沫是止血的,不會(huì)發(fā)炎。侯七口臭,唾沫當(dāng)然也是一股子臭味。
韓伯祥說,日你娘,你能換個(gè)消炎的方子嗎?
還是百順的刀子用得好,韓伯祥還沒有享受徹底,百順說,叔,好了。
好了嗎?韓伯祥用手在自己的臉上抹了一把,果然是干干凈凈的。好,真好!韓伯祥忍不住夸贊道,你個(gè)狗日的百順,還說不會(huì),這比龜孫侯七的手藝強(qiáng)多了。
韓伯祥回到家,對(duì)著鏡子照了一圈子。要說百順剃頭的手藝,算不上多高明,韓伯祥的頭剃出來的模樣跟百順爹的沒啥區(qū)別,都是從鬢角剃到腦袋后面,腦門子上留下一大片,像是沒有收割的莊稼。韓伯祥滿意的是自己的這張臉,太干凈了,太清爽了。自己這個(gè)樣子,不知道姜美芳看了會(huì)有什么反應(yīng)。
姜美芳是大隊(duì)的婦女主任,和韓伯祥兩個(gè)好不是一天兩天了,這個(gè)事不用瞞,一個(gè)大隊(duì)的人都知道。姜美芳老是嫌韓伯祥的胡子光不凈,一張胡子邋遢的臉往姜美芳的小臉上湊,都把人扎得沒地方躲。今天這個(gè)樣子,姜美芳還嫌扎嗎?當(dāng)然,也不光是姜美芳嫌扎,連自己的老婆張大蘭也嫌扎。韓伯祥知道,張大蘭嫌扎,那是矯情,一年到頭的,能扎她幾次?她巴不得韓伯祥去扎她呢,韓伯祥顧不上她。想到張大蘭,韓伯祥扭頭看了一眼,張大蘭就在旁邊,在納鞋底。
張大蘭說,侯七來了?
韓伯祥說,沒來,是百順剃的。
張大蘭說,咱西邊的百順?
韓伯祥說,還能是哪個(gè)百順?
張大蘭說,我前天還和百順媳婦拉呱呢,你猜猜百順的手藝是跟誰學(xué)的?
韓伯祥說,你知道他跟誰學(xué)的?
張大蘭說,跟妮子的爹。
韓伯祥哦了一聲,怪不得呢,跟他岳父學(xué)手藝,那還不把十八般武藝都教給他了。
張大蘭說,你猜猜妮子的爹是干什么的?
韓伯祥說,還能干什么,剃頭的唄。
張大蘭笑了,說剃頭的不錯(cuò),你猜猜是給什么人剃頭的?
韓伯祥說,剃頭還分人嗎?誰的頭不是一樣剃。
張大蘭說,妮子的爹在殯儀館是專門給死人剃頭的。
韓伯祥聽了,手里的鏡子啪地掉在了地上,好長(zhǎng)時(shí)間才回過神來,摸摸自己的臉,問張大蘭,這是真的?
韓伯祥感覺腦袋涼颼颼的,用手一摸,腦門子上滲出密密的細(xì)汗。韓伯祥回味百順給他剃頭時(shí)兩個(gè)人的對(duì)話來。
韓伯祥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很不適應(yīng),不時(shí)地動(dòng)一下。
百順說,叔,你別動(dòng),你一動(dòng),我就哆嗦。
韓伯祥說,你哆嗦什么?
百順說,我在那邊干活的時(shí)候,人都不動(dòng)。叔,你也別動(dòng),就當(dāng)自己睡著了。
想到這里,韓伯祥就覺得張大蘭這話不假了。
這個(gè)狗日的百順,我得去問個(gè)清楚。
四
韓伯祥知道,自己直接去問,估計(jì)問不出結(jié)果,韓伯祥自然有韓伯祥的辦法。
韓伯祥坐在大隊(duì)部自己的辦公室里,耐心地卷一支紙煙。紙是好紙,韓伯祥的抽屜里有五卷《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已經(jīng)卷煙卷完了,韓伯祥已經(jīng)開始用第二卷了。煙當(dāng)然也是好煙,是二韓大隊(duì)的煙把式韓伯良手選的。說韓伯良是大隊(duì)的煙把式是不準(zhǔn)確的,在去年縣里召開的煙葉交流會(huì)上,主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張副縣長(zhǎng)在會(huì)堂里重點(diǎn)表揚(yáng)了韓伯良,號(hào)召全縣的煙葉種植試點(diǎn)公社向韓伯良學(xué)習(xí)。韓伯良是縣里的典型,他種的煙當(dāng)然是全縣最好的。在二韓,很多人家的自留地種糧種菜,只有韓伯良用自留地栽煙。韓伯良的煙葉不是在火炕上燒干的,韓伯良把煙葉片子掰下來,用繩吊子扎好,在太陽底下曬,那些煙葉片子曬干了都有二尺多長(zhǎng),最重要的一點(diǎn),韓伯良的煙葉不僅味道醇厚,而且火旺,不像其他人家的煙葉,吸著吸著火沒了,滅了。張副縣長(zhǎng)就喜歡韓伯良的煙吊子,每次到砂礓鋪?zhàn)庸鐧z查工作,都不會(huì)忘了來二韓,到韓伯良家拿兩把子煙葉走。
韓伯祥把煙葉卷好了,刺啦擦一根火柴,吸一口。
青煙繚繞中,百順站在墻角,頭低著,百順不知道大隊(duì)書記韓伯祥單獨(dú)找他為的是什么事。
當(dāng)然不會(huì)從剃頭說起。韓伯祥問的是兩年前的事。
韓伯祥說,百順,你說說,兩年前為什么一定要去河南?
百順說,俺大叫我到河南找個(gè)女人。
就為了找個(gè)女人嗎?
百順說,你都看到了,我不是把女人領(lǐng)來家了嗎?
韓伯祥說,據(jù)我了解的情況,你當(dāng)初去河南的目的不是找女人吧,你是有另外的目的。
百順說,叔,我能有啥目的?俺家的情況你是知道的,俺大俺娘天天為我找媳婦的事發(fā)愁。
韓伯祥說,那你看看這是什么?
韓伯祥從抽屜里拿出一個(gè)紙片片,是一張“豐收”牌的煙紙盒子。
百順接過來,煙紙盒子上用鉛筆畫了一個(gè)歪著腦袋的小人,在小人的下面,另外畫了三道子豎杠。
韓伯祥說,這個(gè)小人是誰,你說說。
百順的臉騰地紅了。
看到百順臉紅,韓伯祥心里樂了,狗日的,你以為你跑了,這個(gè)事就了結(jié)了,就能煙消云散了?
煙紙片子是馬翠花的賬本。馬翠花是寡婦,丈夫二賴子死得早,給馬翠花留下三個(gè)丫頭。憑馬翠花一個(gè)人的工分,肯定養(yǎng)不活三個(gè)孩子,馬翠花只能另辟蹊徑,開發(fā)自身資源,在二韓,除了韓伯祥和三歡子,沒和馬翠花睡過覺的男人沒有幾個(gè)了。韓伯祥不和馬翠花睡覺,不是說韓伯祥不喜歡女人,也不是說韓伯祥身為黨員和干部自律性強(qiáng),覺悟高。韓伯祥除了要對(duì)付家里的女人張大蘭之外,他還要肩負(fù)著和婦女主任姜美芳睡覺的任務(wù)。對(duì)韓伯祥來說,和女人睡一次覺畢竟不是喝一杯酒那么容易,畢竟也是體力勞動(dòng)。韓伯祥體力不夠,就眼睜睜地看二韓的男人去和馬翠花睡覺。三歡子和韓伯祥不一樣,三歡子小時(shí)候光著屁股跟他爹出去討飯的時(shí)候,小雞雞被狗咬了,三歡子沒有小雞雞,馬翠花當(dāng)然也不會(huì)去找他。二韓的男人沒有錢,和馬翠花睡完了,馬翠花是要記賬的。馬翠花不識(shí)字,只能根據(jù)每個(gè)人的體貌特征給畫個(gè)像。馬翠花有這方面的天賦,比如大隊(duì)會(huì)計(jì)來福臉上有八個(gè)麻子,馬翠花就觀察得很仔細(xì),左邊三個(gè)右邊五個(gè)畫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到年底了,馬翠花去問來福要錢,當(dāng)時(shí)也不是來福沒有錢,來福不是一個(gè)賴賬的人,問題是來福媳婦在跟前,這就不好承認(rèn)了。來福說,翠花,你是不是弄錯(cuò)了,你這畫像上是第一生產(chǎn)隊(duì)的韓有才吧?
翠花才不理會(huì)來福這一套呢,弄完了不給錢,想白占便宜,想得美。
馬翠花說,來福,你看清了,雖然韓有才也是八個(gè)麻子,韓有才是左邊五個(gè),右邊三個(gè)。馬翠花還把韓有才的畫像找出來和來福的對(duì)比一下。
那個(gè)時(shí)候的來福恨不得找個(gè)地縫鉆進(jìn)去。
百順的賬其實(shí)也已經(jīng)結(jié)了,結(jié)這個(gè)賬的時(shí)候,百順不知道,是百順爹給結(jié)的。因?yàn)轳R翠花跟來福要錢,來福兩口子剋架了,來福媳婦把來福的臉都給抓爛了。韓伯祥知道了這個(gè)事,自己先偷偷地笑了一陣子,晚上帶著婦女主任姜美芳找到馬翠花,問馬翠花手里還有幾本賬。
馬翠花說,多了。馬翠花還說,到年底了,這些孬熊弄完了,就想賴賬了。誰賴賬我就跟誰沒完,我沒好日子過,他們也過不好年。
韓伯祥知道,這個(gè)事真要是解決不好,二韓人的這個(gè)年別想過安穩(wěn),二韓人的年過不安穩(wěn),他韓伯祥就不能安穩(wěn)。
韓伯祥說,翠花,這樣好不好,你把賬本給我,我們來幫你要。
馬翠花不給,馬翠花說,騙鬼呢,你怎么要?
韓伯祥說,你歸個(gè)總,看看一共有多少,我一筆都不會(huì)給你冇了。
馬翠花說,不用看,一共是四百七十四筆,我自己要回來一百三十四筆了,還剩三百四十筆。
韓伯祥說,行,就三百四十筆,年底給你結(jié)清。馬翠花說,價(jià)格不一樣,有的是一碗糧食,有的是一個(gè)雞蛋,還有韓小寶子的,他是答應(yīng)過年殺豬的時(shí)候給我一斤豬肉的。
乖乖,這就麻煩了。
韓伯祥想了想,給馬翠花商議,說這樣行不行,咱按工分給,你把幾筆大賬找出來,一個(gè)雞蛋,一碗糧食,咱扣他三分,要是一斤豬肉這樣的,咱照六分扣他的,可好?
馬翠花說好。
韓伯祥把煙紙片子拿到大隊(duì)部的辦公室里,一張一張地看,每個(gè)煙紙片子上都畫個(gè)小人,雖然上面不著一字,韓伯祥也分得清是哪一個(gè)。當(dāng)天晚上,韓伯祥就招呼開會(huì),開一個(gè)大隊(duì)的黨員干部會(huì)議。這個(gè)會(huì)沒有提前打招呼,大家都不知道會(huì)議的議題是什么。
韓伯祥沉著臉。看該來的人都來了,韓伯祥說,因?yàn)槭虑楹車?yán)重,我這個(gè)書記也拿不定主意了,我把大家請(qǐng)來,大家看看怎么辦。
韓伯祥把煙紙片子拿出來,一張一張?jiān)跓粲跋乱蠹铱础i_始還有人到跟前去看,去辨認(rèn),后來都不去了,都把腦袋低了下來。
韓伯祥說,咱是來開會(huì)的,不是來吊唁什么人的,要說話。
還是沒有人說話。
韓伯祥說,大家都不說,我只能把這個(gè)送到上面去,咱叫上面的人來處理。
來福撐不住了,惶惶地走上前,說,不能往上面送,送到上面咱二韓就全軍覆沒了。
韓伯祥心里笑,這個(gè)時(shí)候你還跩,還說全軍覆沒這樣的屁話,我能不知道送到上面的后果嗎?我要是不想到這個(gè)后果,我還開什么會(huì)。
韓伯祥說,那怎么辦,大家說說。
來福說,還,咱大家都還,好不好?
后面的應(yīng)付說,還,都還。
韓伯祥說,怎么還,都回家拿雞蛋,端糧食去嗎?
大家又面面相覷了。
韓伯祥說,這么著吧,扣工分吧,誰少馬翠花多少錢,誰心里明白,這在馬翠花的賬面上也體現(xiàn)得很清楚,你賒一次賬就扣三分給馬翠花,這樣可好?
大家又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三隊(duì)的隊(duì)長(zhǎng)韓毛堂站了起來,韓毛堂說,書記,我賒了十多次了,一下扣幾十分,俺女人會(huì)鬧的。
韓伯祥惱了,狗日的,你也知道女人會(huì)鬧,那你說怎么辦?
來福站了起來,來福說,直接這么扣工分,肯定會(huì)有意見,我想了一個(gè)辦法。
韓伯祥說,你講。
來福說,要過年了,你知道咱大隊(duì)離街上遠(yuǎn),一個(gè)冬天都不能洗個(gè)澡,咱在牛房里燒幾大缸熱水,來個(gè)衛(wèi)生大掃除,叫上這些人來洗澡,以這個(gè)名義扣工分,你看可好?
韓伯祥問,大家說呢?
好,就說洗澡,就這么辦。
百順當(dāng)然沒有來洗澡,韓伯祥看到有一張歪著腦袋的圖片,著實(shí)琢磨了一會(huì),這會(huì)是誰呢?韓伯祥首先想到的是二隊(duì)的三荒子,三荒子每每和人爭(zhēng)論的時(shí)候,都是歪著頭跟別人講,好像他手里攥著理一樣。但是,韓伯祥看到另外一張煙紙片子的時(shí)候,很快把這一張給否定了。另外一張煙紙片子上也畫了一個(gè)歪著腦袋的人,這個(gè)人嘴是張著的,眼睛睜得很大,還有唾沫星子從嘴里噴出來,這個(gè)才是三荒子。那么前面一張會(huì)是誰呢?韓伯祥睡在大隊(duì)部的值班室里,旁邊睡著的是姜美芳。
韓伯祥說,主任,你起來看看,你看看馬翠花這個(gè)畫的是誰?
姜美芳用個(gè)小拳頭在韓伯祥的胸膛子上捶了一下,咱不是說好了嗎?睡覺的時(shí)候沒有書記,也沒有主任。
韓伯祥說,這不是在值班室嗎?咱在值班室說話,就得書記主任地稱呼著,要是窗外有人聽,就以為咱們是在工作,你說是吧?
姜美芳說,你確實(shí)是在工作呀,你一個(gè)晚上都在看馬翠花畫的連環(huán)畫,你看連環(huán)畫比跟俺睡覺興趣都高。
韓伯祥說,就這個(gè)圖,我琢磨一個(gè)晚上了,你幫我看看,你看看這是哪個(gè)?
姜美芳就在燈影下端詳了一陣子,她也說到了三荒子。
韓伯祥拿起另一張說,三荒子在這里。
姜美芳說,是不是百順?
韓伯祥從被窩里坐起來,對(duì),是百順,日他娘,這不是百順還能是誰?狗日的孩子,這個(gè)事他也能做。
姜美芳說,百順也快三十的人了,他弄這個(gè)事,有什么好奇怪的?
韓伯祥說,這孩子看上去多老實(shí),平時(shí)連話都不會(huì)說,居然也會(huì)和馬翠花睡覺。
韓伯祥沒有把百順的這張賬單拿出來,百順和別人不一樣,百順一家人為了給百順娶個(gè)女人,費(fèi)盡了心思,如果這個(gè)時(shí)候把百順和馬翠花睡覺的事捅出來,百順這輩子想娶個(gè)女人就沒有指望了。韓伯祥去找百順爹,韓伯祥把這個(gè)事的來龍去脈一說,百順爹感動(dòng)得就差跪在地上給韓伯祥磕頭了。百順爹說,兄弟,你救的不是百順一個(gè)人,你是把俺這一家人都救了啊,這個(gè)事要是傳出去,你說我們這個(gè)臉往哪里擱?誰還愿意跟俺百順過日子?別說扣九個(gè)工分了,你就是扣九十個(gè),九百個(gè),俺也沒有話說。
五
今天韓伯祥把這個(gè)賬單拿出來,把百順給唬住了。韓伯祥說,你說說,除了在家里和馬翠花有關(guān)系,你跑到河南都干了什么?
韓伯祥這樣問,是想打探他學(xué)手藝的那點(diǎn)事。百順理會(huì)錯(cuò)了,百順以為韓伯祥問的,是百順除了和馬翠花睡過覺之外,到河南又和哪些女人睡過覺。韓伯祥手里捏著百順的七寸,百順就更老實(shí)了,只能從頭交代。
百順說他在河南過了兩年,一共和七個(gè)女人睡過覺。
百順說七個(gè)女人時(shí)是低著頭說的,他沒有看到韓伯祥因?yàn)轶@訝而張大了的嘴巴。其實(shí)百順說七個(gè)女人,是打了埋伏的,七個(gè)女人是百順能說得出來名字的女人,還有幾個(gè)百順根本不知道她們姓什么叫什么。
百順去河南,去他姨娘家,從家里背著三十斤麥子、四十斤紅薯干子,腰里揣著借來的二十八塊錢和十二斤國家通用糧票。當(dāng)然,也有韓伯祥給他開的大隊(duì)證明信,沒有這個(gè)證明信,說不定百順帶著的這些糧食在半路上就被別人給沒收了。
姨娘家住在山窩窩里,山窩窩里有十幾戶人家,都看到百順是背著糧食來的,都看到百順?biāo)棠镌诖孱^就迎著百順了,百順姨娘和他男人忙著把百順肩上的糧食接過來,一臉喜氣地往家里走。
百順是來找女人的,百順姨娘說。
小山窩不平靜了,與其讓妮子在家里餓肚子,不如跟著這個(gè)安徽人過日子呢,至少,這個(gè)安徽人家里有糧食。
先到百順姨娘家的是姨父的弟弟,百順不知道怎么稱呼姨父的弟弟,是不是也應(yīng)該叫姨父呢?他拿不準(zhǔn),如果不稱呼姨父,又該怎么稱呼呢?既然是姨父的弟弟,應(yīng)該叫二姨父才對(duì)。這樣想,百順就叫了出來。姨父和姨父的弟弟都把眼睛睜大了,這孩子不會(huì)是腦子有問題吧?如果是腦子有問題,大老遠(yuǎn)的,又是坐火車,又是坐汽車的,他一個(gè)人能來到這里嗎?如果腦子沒有問題,這樣的關(guān)系怎么能稱呼是姨父呢,而且是二姨父,那么他二姨在哪里呢?誰見過呢?雖然疑惑,也沒有去給百順糾正過來,或許安徽都是這么稱呼的吧。
當(dāng)天的晚飯,百順就在二姨父家吃了。二姨父一家人吃的是菜團(tuán)子,菜是野菜,里面摻幾片子麥麩子皮。當(dāng)然,百順的待遇要好一點(diǎn),百順的饃饃麥麩子多,野菜少,但是,百順還是咽不下去。百順在家里嬌生慣養(yǎng),雖然不是錦衣玉食,但凡家里好吃的、好穿的,都給了百順,百順不吃了,姐姐和妹妹們才能看上一眼。今天這個(gè)菜團(tuán)子把百順給難住了,百順吃了一個(gè)菜團(tuán)子,喝了一碗能照出人影子的稀飯,要回到姨娘家睡覺去。二姨父沒讓,二姨父說床鋪都安排好了。
百順在二姨父家住了三個(gè)晚上,三個(gè)晚上都是二姨父家的丫頭春苗陪著的。春苗小,十七歲,因?yàn)槌圆伙柖亲樱麄€(gè)人瘦得跟貓一樣。春苗陪百順?biāo)桨胍梗那牡嘏榔饋恚诎夙樀目诖锩鳌0夙樀目诖锷抖紱]有,錢和糧票被姨娘收走了,姨娘說替他保管著。春苗餓得不行了,會(huì)把百順叫醒,問百順,你口袋里怎么不裝幾片子紅薯干子呢?
百順口袋里沒有吃的,春苗不再愿意陪百順?biāo)X了。
二姨父問百順,能不能把你背來的紅薯干子分一份過來,你姨娘家一半,俺家一半?
百順把二姨父的想法說給姨娘聽,姨娘嚇了一跳,說,百順,你可別傻啊,你要是真把紅薯干子背過去了,他家立馬會(huì)把你趕出來。你把紅薯干子放這里,他想著,他才會(huì)留你吃飯,留你睡覺,你才能把春苗領(lǐng)回家。
因?yàn)榘夙槻荒鼙尺^來紅薯干子,二姨父一樣把百順給趕了出來,狗日的,白睡了俺家春苗不說了,還吃了俺家三天的菜團(tuán)子。
百順是早上被二姨父趕回來的,百順回到姨娘家,姨娘一家五口人正在吃飯。這幾天百順在二姨父家白天吃菜團(tuán)子,晚上摟著瘦弱的春苗睡覺,人已經(jīng)瘦得像蛻掉了一層殼。百順看到姨娘家的窩頭,伸手去拿一個(gè),姨娘慌張地給百順奪了下來。
姨娘把百順拉進(jìn)里面的屋子里,問百順怎么回來了?
百順說是二姨父趕出來的。
姨娘問,那春苗呢?春苗不是愿意跟著你的嗎?春苗不是都跟你睡覺了嗎?
百順說,春苗嫌我口袋里沒有吃的,不愿意跟我睡覺了。
姨娘就把臉拉了下來,恨恨地說,這個(gè)死丫頭,活該餓死她。
姨娘還對(duì)百順說,春苗不愿意跟你過日子,有愿意跟你過日子的,那個(gè)丫頭比春苗長(zhǎng)得好。
百順現(xiàn)在不急著找女人了,百順只想先吃飽肚子。
等百順從屋子里出來,姨娘飯桌上的窩頭已經(jīng)沒有了,姨娘一家人從飯桌上離開了。
天還沒晌午,姨娘就把百順領(lǐng)到了另外一戶人家里。
這家人姓陳,百順喊這家男人是陳姨父。
百順在陳姨父家的第一頓飯吃的是玉米面饃饃,黃澄澄的那種,看上去就很誘人。百順吃了三個(gè),吃得陳姨父家的女人眼睜得老大。三個(gè)饃饃百順肯定是吃不飽的,但是,百順不好意思再吃了,陳姨父家六口人,蒸了四個(gè)玉米饃饃,百順看到陳姨父一家喝的是菜湯,吃的是曬干的南瓜條子。百順不知道南瓜條子好吃不好吃,他在吃完三個(gè)玉米饃饃之后也伸手去拿了一根南瓜條子。百順咬了一口南瓜條子,在嘴里咀嚼了半天才就著一碗菜湯咽了下去。南瓜條子沒有鹽,也沒有油,像是一根填在嘴里的柴火棒子。
陳姨父家的閨女叫陳二云,二云的模樣看上去比春苗更像個(gè)丫頭。春苗沒有胸,從上到下是一條直線。二云雖然穿著一件很破舊的藍(lán)棉襖,可她的胸脯鼓了出來,有點(diǎn)馬翠花的意思了。
在百順的印象里,馬翠花那樣的女人才叫女人。馬翠花不僅胸脯大,馬翠花的奶子還有奶水。百順雖然只跟馬翠花睡過兩次覺,但是,馬翠花給百順記了三筆賬。
馬翠花說,你睡覺的時(shí)候吃奶了,你知道奶水有多金貴嗎?天天吃窩頭喝稀飯是沒有奶水的。
馬翠花每天是要喝一碗鹽湯的,有了這碗鹽湯,馬翠花的奶子才有奶水。
百順和馬翠花睡覺的時(shí)候還不知道吃奶,是馬翠花讓他吃的。
百順吃完了奶,辦完了事,馬翠花說你得從家里端一碗半糧食。
百順問,不是說好了是一碗糧食的嗎?
馬翠花說,你不是吃奶了嗎?吃奶能是白吃的啊?
后來隔了一些日子,百順忍不住了,又去找了一次馬翠花,又吃了一次奶。
加上上一次,就是三碗糧食了。馬翠花說,要畫三道子豎杠。
百順說三道子就三道子。
百順和陳二云睡覺,以為陳二云的奶子也是有奶水的。
沒有。
百順問陳二云的奶子是不是假的,為什么馬翠花的有奶水,你的沒有?
二云問,哪個(gè)馬翠花?
百順說,二韓的馬翠花。
二云問,馬翠花有孩子嗎?
百順說,有。
陳二云說,有孩子當(dāng)然有奶水了。
百順問二云,沒有孩子就沒有奶水了嗎?不是天天喝點(diǎn)鹽水就有奶水了嗎?
二云還是丫頭,二云跟著百順?biāo)X就已經(jīng)羞得抬不起頭了。
二云把自己縮在被窩里,不再和百順討論奶水的事。
和二云睡過兩個(gè)晚上,百順以為,這個(gè)二云合自己的心意。二云不是春苗,春苗雖然和百順?biāo)^三個(gè)晚上,可春苗不動(dòng),弄得百順很累,很乏味。二云就不是了,二云在第二個(gè)晚上就知道回應(yīng)了,雖然回應(yīng)得很勉強(qiáng),不像馬翠花的幅度那么大,總算有了動(dòng)靜。因?yàn)槎坪茫夙樉突氐揭棠锛遥棠锇炎约罕硜淼募t薯干子分一份給二云家。
姨娘沉下臉,問百順,是二云問你要的,還是二云的爹娘問你要的?
百順說,是我自己要給的。
姨娘就用指頭在百順的腦門子上戳了一下,問百順,你是餓憨了,還是睡覺睡過了頭,你就指望幾斤紅薯干子帶個(gè)女人回家嗎?
百順說,我是看二云好,二云適合我,我就想給她家紅薯干子了。
姨娘說,你個(gè)百順真是沒長(zhǎng)腦子,跟你睡兩個(gè)晚上就適合你了,春苗跟你睡三個(gè)晚上,他爹怎么把你趕出來了?
百順說,二云比春苗好。
姨娘說,我明天再給你找一戶人家,讓你再睡幾天,看看到底哪個(gè)女人適合你。
百順說,不睡了,就二云了。
姨娘就吵百順,說二云好,二云哪里好,二云那個(gè)地方香嗎?
百順低下頭不吱聲了。
六
如果不是韓伯祥打罷,估計(jì)百順會(huì)把他和七個(gè)女人睡覺的經(jīng)過前前后后都說一遍,是韓伯祥不讓他說的,韓伯祥根本沒有心思聽百順講自己找女人的經(jīng)過,這些故事對(duì)韓伯祥來說一點(diǎn)也不新鮮。在韓伯祥看來,二韓的男人隨便抓一個(gè)過來,只要不抓住沒有了小雞雞的三歡子,任何一個(gè)男人的故事都會(huì)比百順的故事精彩得多。
韓伯祥說,你就講講你帶來家的這個(gè)妮子,你是怎么認(rèn)識(shí)她的,又是怎么把她帶回來的?
大冷的天,百順講得一腦門子的汗,給別人講自己和女人睡覺的事,實(shí)在是難以開口,好在韓伯祥給他省略了四個(gè),不然還不難為死這個(gè)百順。
百順?biāo)炅说诹鶄€(gè)女人已經(jīng)是到河南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了。河南的春天跟皖北的春天并無二致,陰天下雨,晴天也出太陽,有區(qū)別的是百順這個(gè)人。這個(gè)時(shí)候的百順已經(jīng)一無所有了,百順被一個(gè)名叫蘭子的寡婦趕出了門。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里,當(dāng)初蘭子收留他,認(rèn)為百順是個(gè)勞力,如果生產(chǎn)隊(duì)能讓百順跟著上工,一是多多少少可以補(bǔ)貼家用,二個(gè)自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跟男人睡覺去掙碗飯吃了。偷偷摸摸地去跟人睡覺不僅吃不飽肚子,別人還在背后指指戳戳的,不好。收留了百順就不一樣了。跟百順?biāo)X名正言順。誰能知道百順一個(gè)六尺高的男人不好用呢?蘭子說百順不好用,不是說百順在床上不好用,經(jīng)歷過馬翠花的男人有幾個(gè)是不好用的?百順不好用,是說農(nóng)活這個(gè)方面,百順不會(huì)使牲口犁地,不會(huì)趕牲口拉車,不說這些大活,拿把鋤頭耪地你該會(huì)吧?還不會(huì)。那我蘭子要你干什么用,就留著晚上睡覺嗎?對(duì)蘭子來說,啥都稀缺,就是不稀缺男人。蘭子對(duì)百順說,你走吧,你從哪里來,還回哪里去,個(gè)雞巴男人,白白地跟你睡了一個(gè)星期不說了,我還倒貼七天的伙食。
百順能去哪里呢?回姨娘家,姨娘眼皮都不抬了。姨娘在納鞋底,姨娘用大針穿過鞋底子,手拉麻繩子的聲音刺啦刺啦響。姨娘說,百順,你來河南幾個(gè)月的時(shí)間了,女人也找好幾個(gè)了,為啥沒有一個(gè)愿意跟你走的呢?
百順說,二云是愿意的,你不讓帶。
百順對(duì)二云念念不忘。
姨娘說,百順,你摸著你的良心說話,我什么時(shí)候不讓你帶二云了?是二云不愿意跟你走吧?二云要是愿意跟你走,她能跟另外一個(gè)男人跑嗎?
是的,二云跟男人跑了。
百順跟著姨父在山窩窩里拉石頭,拉了兩個(gè)月,回來就聽說二云走了。百順去二云家看過,陳姨父說,你這孩子,這個(gè)時(shí)候還來俺家干什么?
百順想說是來看看二云的。
陳姨父說,你在俺家住了兩天就不回來了,是二云對(duì)不住你,還是俺和她娘對(duì)不住你?
沒有誰對(duì)不住百順,平心而論,來到河南這些日子,對(duì)百順最好的就是陳姨父家,是二云。百順本來是想把自己帶的糧食送一些給二云家的,姨娘不同意,姨娘第二天就讓百順跟著姨父去山里拉石頭了。這一去,也沒有給二云個(gè)交代。
姨娘給百順說,兩條路給你:一,上山拉石頭,掙了錢,你一半,俺一半,等你攢足了路費(fèi),你想走,你就走;二,立馬就回你的安徽。
百順說,我?guī)淼穆焚M(fèi)不是你給保管著嗎?你把錢給我,我現(xiàn)在就走。
姨娘說,百順,你說這個(gè)話不怕遭老天爺報(bào)應(yīng)嗎?是的,你是給我錢了,這幾個(gè)月你不吃飯嗎?你去這個(gè)女人家睡覺,去那個(gè)女人家睡覺,能是我一句話你說去就去的嗎?我不給人錢,誰好好的閨女會(huì)跟你睡覺?
百順不去拉石頭了。百順跟著姨父拉了兩個(gè)月的石頭,掙了二十一塊八毛錢,錢被姨父領(lǐng)走了,連零頭八毛百順也沒有見到,百順只能回家,回安徽去。
百順轉(zhuǎn)身離開了姨娘的家。百順轉(zhuǎn)身轉(zhuǎn)得很堅(jiān)決,這個(gè)轉(zhuǎn)身很有二韓男人的血性。是的,百順只能轉(zhuǎn)身,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只能靠自己走回安徽了。
百順在山窩窩里辨不清方向,只能跟著路走,路往哪里拐,他就往哪里去。他這樣走了三天,渴了,捧一捧山溝溝里的水喝一口;餓了,尋著人家要一口。山窩窩里能有幾戶人家呢?大多數(shù)時(shí)候百順只能吃樹葉、啃樹皮。這個(gè)時(shí)候的百順很有一點(diǎn)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熱愛生命》小說里描述的那個(gè)淘金者的味道了。當(dāng)然,百順不知道杰克·倫敦,他也沒有讀過《熱愛生命》。百順憑著對(duì)活下去的渴望,一步一步走出了山窩窩。
山外的天是廣闊的,土地是遼遠(yuǎn)的,走出山窩窩的百順不禁回頭望了一眼。那個(gè)時(shí)候,黃昏的日頭像一只鬼魅的眼睛,若隱若現(xiàn)地在西山口的云層里瞅著百順。日頭不僅若隱若現(xiàn),還恍惚著,一會(huì)是一個(gè),一會(huì)又變成了兩個(gè)。再看,一個(gè)西山口到處都是日頭,到處都是鬼魅一樣的眼睛。不僅是西山口了,在百順的身后,每一個(gè)山峰、每一片樹叢,但凡有陰影的地方,都藏著一個(gè)鬼魅。他們悄悄地集結(jié)在一起,陰影的面積越來越大,慢慢地向百順覆蓋過來。百順想到了老家,想到了一個(gè)叫做二韓的村莊,百順沒有恐懼,這個(gè)時(shí)候的百順甚至有了二韓人的幽默了,是不是這個(gè)山窩窩里的女人我還沒有睡完,老天爺要把我留在這里呢?有了這個(gè)想法的百順是幸福的,他心滿意足地閉上了眼睛。
百順當(dāng)然沒有死,百順是又累又餓,昏過去了。那個(gè)年月,遇到路旁死個(gè)人這種情況,基本是就地埋了。要不就是被野狗吃了。百順是幸運(yùn)的,百順趕上了當(dāng)?shù)卣诰倦A級(jí)敵人壞分子的運(yùn)動(dòng)。每個(gè)大隊(duì)都有指標(biāo),百順暈倒所在地的這個(gè)大隊(duì)正在發(fā)愁,到哪里去揪階級(jí)敵人呢?美帝那么遙遠(yuǎn),想抓到一個(gè)是不現(xiàn)實(shí)的;去臺(tái)灣聽說要過海,過海是要會(huì)鳧水的,山窩窩里的人還沒有見過海,更別說鳧水了,都是旱鴨子,真下了海,階級(jí)敵人沒有抓到,自己的小命卻沒有了,看來這條路也走不通。剩下的都是本村的人了,一個(gè)一個(gè)窮得叮當(dāng)響,哪個(gè)是階級(jí)敵人呢?好在他們遇到了百順,村里的人高興了,幾個(gè)人用擔(dān)架把百順抬到了公社,這就是階級(jí)敵人。公社也在為抓階級(jí)敵人犯愁,居然有村民抓到了一個(gè),趕快用吉普車送縣城去,公社書記一再交代,要快啊,千萬留個(gè)活口,別死在了路上。縣領(lǐng)導(dǎo)對(duì)這個(gè)事很重視,是不是階級(jí)敵人是要審查的,好幾個(gè)公社都是用死人來濫竽充數(shù),這次又來一個(gè),氣都不喘了,你怎么判定他是階級(jí)敵人呢?縣領(lǐng)導(dǎo)手一揮,抬走,抬走。公社的人問,抬哪里去?縣領(lǐng)導(dǎo)沒有好氣地說,殯儀館。
殯儀館很忙,殯儀館的大煙囪正呼呼地冒著青煙。如果不是這么忙,估計(jì)百順到了這個(gè)地方,直接就給扔火爐子去了。百順沒能趕上,要去天堂的人很多,前面還排著長(zhǎng)隊(duì)呢,按半個(gè)小時(shí)燒掉一個(gè)人來計(jì)算,兩個(gè)爐子一起燒,沒有七八個(gè)小時(shí),是燒不到百順的。百順很放心,睡得香甜,他甚至還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里的天空鋪滿了彩霞,許多叫不上名字的鳥兒自由地飛翔。
百順是被一陣陣哭聲給鬧醒的,那哭聲撕心裂肺震耳欲聾,百順夢(mèng)中的鳥兒在哭聲中嘩啦啦地四散飛去。
百順睜開眼,動(dòng)動(dòng)身子,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喊聲,天爺啊,有鬼。
百順當(dāng)然也怕鬼,百順噌地坐了起來,也跟著叫,鬼,鬼,鬼在哪里?
你狗日的沒死,你狗日的沒死你冒充什么死人?你看看你把這些人嚇成什么樣了,好好的人差點(diǎn)沒被你嚇?biāo)馈?/p>
沒死的百順無處可去,就在殯儀館里干上了。不會(huì)使牲口犁地的百順會(huì)收拾死人,在殯儀館里的一年多,百順給死人凈面,整容。一些有模有樣的人物,要換衣服。給死人換衣服這個(gè)活不好干,死人都硬邦邦的,穿不好穿,脫不好脫的,沒有一點(diǎn)技巧,你還真干不好。一般來說,死人要穿的衣服,里里外外好幾層。你不能一層一層地去給死人穿,那樣給死人穿衣服能把活人都給累死。百順把死人要穿的衣服先穿在自己身上,從里到外,整理好了,再脫下來,套在死人身上。給死人穿衣服只是收拾死人眾多內(nèi)容里的其中一項(xiàng),對(duì)那些有頭有臉的人來說,臉上的活才是最重要的。剛到殯儀館的百順,開始只能干給死人穿衣服洗臉這樣的活,整容的活是殯儀館里的老師傅沈一刀來做。沈一刀有個(gè)很破舊的皮包,沈一刀的工具都是放在皮包里隨身帶著。到了用的時(shí)候,百順能看到,沈一刀拿出來的任何一個(gè)工具,不論是剃刀、剪刀還是光臉的刀子,都泛著藍(lán)瑩瑩的光。百順老是有用手摸一摸的欲望,卻總是沒有機(jī)會(huì)。雖然摸不上那些工具,百順還是愿意看沈一刀干活。殯儀館里那么多的死人,他們死的樣子一個(gè)比一個(gè)難看。沈一刀對(duì)死人似乎是視而不見的,他走到死人跟前,揭開薄薄的單子,只輕輕地一撩,一個(gè)你無法想象的面容就呈現(xiàn)在眼前。對(duì)那些怒目圓睜的死者,沈一刀會(huì)伸出手來,從死者的腦門子往下抹一把,死者的眼睛就閉上了。當(dāng)然也有閉不上的,這個(gè)時(shí)候的沈一刀會(huì)把他的手掌在死者的眼睛上停留一會(huì),輕輕地蠕動(dòng)一下,嘆息一句,閉上吧,知道你肯定是有冤屈的,你不是第一個(gè),也不會(huì)是最后一個(gè),到天堂里就好了,那里干凈。百順不知道沈一刀說這話是什么意思,他覺得沈一刀和這些死者好像都是老朋友,沈一刀在說一些送別的話。
一個(gè)晚上,很晚了,殯儀館里安靜得讓人心生恐怖。
沈一刀在給一個(gè)老者整容,一開始沈一刀還是平靜的,穿衣服這樣的活他都沒讓百順去干。沈一刀給老者穿的衣服,每一個(gè)紐扣都給老人扣得整整齊齊的,給老人換了一雙襪子,一雙新布鞋。在給老人洗臉的時(shí)候,沈一刀的手哆嗦了,百順看得出來,沈一刀在控制著自己,他想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雖然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什么異樣來,他的心跳已經(jīng)是在劇烈地起伏著了。該給老人凈面了。沈一刀的手怎么也控制不住,哆嗦得越來越厲害。沈一刀放下刀子,用左手去握自己的右手,左手也跟著哆嗦。沈一刀知道下面的工作自己已經(jīng)無法完成了,他慢慢地站起來,轉(zhuǎn)過身去。百順從來沒有見到過沈一刀出現(xiàn)過這樣的情況。百順問,沈師傅,你怎么了?沈一刀把頭昂起來,臉對(duì)著天花板,還是有兩行熱淚從沈一刀的面頰上流了下來。
沈一刀最終沒有干完這個(gè)活,剃頭凈面都是百順干的,這是百順第一次干這樣的活。令人奇怪的是,百順?biāo)坪跆焐歉蛇@個(gè)活的材料,沈一刀只是在旁邊指點(diǎn)幾下,百順居然把活干出來了。
過了一年之后,百順和沈一刀的女兒沈小米定親了。沈一刀,百順,小米在一起吃飯,沈一刀端起酒杯說,那個(gè)老者,是沈一刀的師傅,當(dāng)年兩個(gè)人在國民黨軍隊(duì)里,他救過沈一刀的命。
百順還要說下去,韓伯祥打了個(gè)手勢(shì),不讓百順說了。清楚了,韓伯祥想知道的就在這個(gè)地方。
狗日的百順真的是給死人剃頭的。
韓伯祥問百順,以后剃頭能不能別讓我躺著?
百順說,我試試。
韓伯祥說,不是試試,是一定。
想想睡倒的樣子,太瘆得慌。
七
百順在二韓剃了三十年的頭,有兩件事為二韓人津津樂道。先說第一件吧。
是這樣的,大隊(duì)書記韓伯祥的褲襠里確實(shí)生了毛病,生毛病的原因是韓伯祥和大隊(duì)的婦女主任姜美芳睡覺,睡得正熱火朝天的時(shí)候,姜美芳的男人韓光明突然回來了。韓光明是換荒的,韓光明雖然把兩個(gè)人堵在了屋子里,他也沒有敢破門而入,畢竟,韓伯祥當(dāng)個(gè)書記,有點(diǎn)權(quán)力在手里,就是打架,他也打不過韓伯祥,還有,這是在自己家里,如果姜美芳不同意,韓伯祥能進(jìn)了屋子能上得了床嗎?但是,韓光明又不想眼睜睜地看著兩個(gè)狗男女這么逍遙自在。韓光明把手里換荒用的撥浪鼓子搖了起來,一邊搖一邊淚流滿面的,誰都能看得出光明的傷心和無奈。韓伯祥和姜美芳這個(gè)時(shí)候。出來不是,不出來也不是。另外一個(gè)原因和一個(gè)女知青有關(guān)。二韓有個(gè)名叫蘇珊的女知青被人強(qiáng)奸了,什么人干的,公安正在調(diào)查。那是年底,要過春節(jié)了,韓伯祥的女人張大蘭把家里的公狗給殺了,給韓伯祥燉了一鍋狗鞭湯。張大蘭認(rèn)為韓伯祥一年到頭都在姜美芳那里忙活,到了年底,給韓伯祥加點(diǎn)料,也讓韓伯祥在自己身上忙一次。因?yàn)楣繁逌n伯祥的確煥發(fā)了青春,韓伯祥忘乎所以,已經(jīng)和張大蘭進(jìn)行第二個(gè)回合的戰(zhàn)斗了。沒想到公安正在抓人,村子里開始有了腳步聲,有了狗叫聲。張大蘭還給韓伯祥開玩笑,說你看看,你今天一努力,把全村的狗都帶動(dòng)起來了。隨后發(fā)生的事情是誰都沒有想到的,強(qiáng)奸蘇珊的嫌疑人孫光腚跑了,公安砰砰砰地開了幾槍,韓伯祥一下子軟了下來。當(dāng)時(shí)韓伯祥還沒有覺察,等到姜美芳要,張大蘭要,韓伯祥給不了,才知道壞了,出問題了。剛發(fā)現(xiàn)問題,韓伯祥還幽默得起來,被兩個(gè)女人纏著太累了,這多好,終于有星期天了。韓伯祥四十多歲,隔三差五的星期天他是樂于接受的,如果終年都是星期天,這就是大問題了。一個(gè)晚上,韓伯祥手捧著自己的兄弟說道,你說說這些年你怕過誰?你到哪里不是硬邦邦的?現(xiàn)在我給總結(jié)了一下,這個(gè)世界上有兩樣?xùn)|西你怕,一是撥浪鼓子響,二是槍響。
這是韓伯祥自己總結(jié)的。百順不這樣看。百順早就聽說韓伯祥褲襠里出問題了,不僅百順知道,整個(gè)二韓都知道張大蘭在給韓伯祥用偏方。所謂的偏方,就是吃什么補(bǔ)什么。張大蘭像是瘋了一樣,不僅到街上去買,找親戚朋友要,發(fā)展到后來,她看到跟前跑個(gè)公狗,她都想攆上去,把狗的那個(gè)東西割下來煮了給韓伯祥吃。
雨天,是細(xì)細(xì)的雨,纏綿了多日,生產(chǎn)隊(duì)出不了工,男人們都來到百順家,都想瞅這個(gè)閑空剃頭。人多,話也就多,二韓的話題,大多和褲襠里的物件有關(guān)系,說到這個(gè)事,自然是圍繞著韓伯祥來說,自然以韓伯祥的褲襠為中心。你一言,他一語,唯獨(dú)百順不說。百順不說,不是百順對(duì)這種事羞于啟齒,在二韓莊成長(zhǎng)起來的男人,最早的啟蒙就和褲襠有關(guān)系,有什么羞于啟齒的?百順屬于那種在心智上啟蒙晚成長(zhǎng)快的男人,擱在去河南之前,百順對(duì)人情世故的認(rèn)知是淡薄的,家里的事都是聽他爹的,爹說怎么辦就怎么辦,用不著他來操這么多心。后來去了河南,上了那么多張床,經(jīng)歷過那么多的女人,看到了那么多張臉,百順在不同的面孔上看到了人情的冷暖,他自然會(huì)有自己的想法。百順不說韓伯祥的病,是他認(rèn)為說出來沒有意義。畢竟是褲襠里的毛病,一個(gè)男人,除了臉面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褲襠,人家哪里不好,你就說哪里,不管是說好還是說不好,這個(gè)話傳到韓伯祥的耳朵里,韓伯祥能沒有想法嗎?韓伯祥是書記,你讓一個(gè)大隊(duì)的領(lǐng)導(dǎo)人對(duì)你有想法,不是好事。百順不僅不說,百順甚至在心里有個(gè)計(jì)劃,他決定把韓伯祥的這個(gè)病給治一下,治好治不好很難說,但是,可以試一試。百順有這個(gè)想法已經(jīng)有很多日子了,他沒有去給韓伯祥說,他覺得說這個(gè)事最好找一個(gè)合適的時(shí)間和恰當(dāng)?shù)臋C(jī)會(huì)。
韓伯祥剃頭沒有規(guī)律,自從百順把二韓剃頭的事接過來,韓伯祥自在多了,隔個(gè)十天八天的,就來找百順,就讓百順給他拾掇一下,有時(shí)候要去公社開會(huì)了,臨走之前也會(huì)到百順這里整一下。外表上的煩心事才收拾利索的時(shí)間不長(zhǎng),沒想到褲襠里又有了煩惱,而且這種煩惱不是他韓伯祥一個(gè)人的,是張大蘭的,是姜美芳的。如果只是韓伯祥一個(gè)人的,也無所謂了,現(xiàn)在的問題是,張大蘭把責(zé)任推到姜美芳那里,說韓伯祥肯定是在姜美芳那邊勞累過度的原因。姜美芳不甘示弱,說韓伯祥吃著碗里的占著鍋里的,這下好了,都沒有指望了。一個(gè)男人在這方面讓女人沒有指望,痛苦就不僅僅在女人那里了,韓伯祥現(xiàn)在比誰都著急。
韓伯祥進(jìn)了屋子,一屋子人都不說話了,關(guān)于褲襠的話題戛然而止。韓伯祥在外面已經(jīng)聽到了,韓伯祥說,沒事,繼續(xù)說。
韓伯祥的臉上沒有笑容,熟悉韓伯祥的人都知道,韓伯祥這個(gè)人是開玩笑開慣了的,見到誰他都會(huì)說幾句,別看當(dāng)個(gè)大隊(duì)書記,社員干活干累了,在地頭休息的時(shí)候,都喜歡聽韓伯祥開玩笑。韓伯祥不僅喜歡開玩笑,還喜歡在地頭扒女人的褲子。當(dāng)然,韓伯祥的褲子也被女人扒過。不光是扒褲子,褲衩都給韓伯祥扒下來。韓伯祥無處藏身了,就往地頭的河里跳,一個(gè)地頭的人都跑到河岸上歡呼,韓伯祥只能在河里告饒。
八
今天韓伯祥不說話,臉色沉重,誰都能看出來,屋子里的人一個(gè)一個(gè)地溜走了。
韓伯祥一屁股坐在躺椅上。躺椅是韓伯祥從自己家里搬來的。韓伯祥不愿意睡倒光臉,坐在凳子上百順干不了。韓伯祥只能把這個(gè)椅子搬到百順家,有了躺椅,百順給他光臉就舒服多了。
百順從茶壺里倒了熱水,濕了一下毛巾,輕輕地搭在韓伯祥臉上。
韓伯祥閉著眼,心事重重的樣子。
屋子里沒有其他人了。
百順說,叔,你怎么不換個(gè)方子試試?
韓伯祥沒說話。
百順知道韓伯祥在聽,韓伯祥不會(huì)這么快就睡著。
百順說,我說的是叔的病,有時(shí)候是和心情有關(guān)系的。
韓伯祥還是沒有吭聲。
百順自顧自說,我聽說伯仁叔家的水羊這些年都是用你家的騷胡頭放的窩。
這不假,韓伯仁家養(yǎng)個(gè)水羊,水羊要是跑窩了,也就是發(fā)情了,都是把水羊牽到韓伯祥家。韓伯祥家養(yǎng)個(gè)大種羊,不光是韓伯仁家水羊跑窩牽到韓伯祥家,別人家的水羊跑窩也牽到韓伯祥家,也是找韓伯祥家的種羊放的窩。
百順說,聽說昨天伯仁叔把水羊牽過去,騷胡頭不愿意爬了。
韓伯祥不知道百順是個(gè)什么意思。
昨天韓伯仁是把水羊牽來了,問題是同時(shí)把水羊牽來的還有池喇叭。池喇叭牽來的水羊小,第一次跑窩,騷胡頭興沖沖地爬完了小羊,把韓伯仁家的老母羊給撂下了,看都不看一眼了。當(dāng)時(shí)是張大蘭在家里,張大蘭怎么鼓動(dòng),騷胡頭就是無動(dòng)于衷。沒辦法了,張大蘭只能讓韓伯仁先把水羊牽回家。張大蘭還給韓伯仁說了一句老牛只想啃嫩草這樣的話,惹得韓伯仁一肚子不高興。
百順說,叔,羊都知道找個(gè)新鮮的。
韓伯祥似乎懂了,又沒有完全懂。
你狗日的拿羊跟我比。
百順笑了一下,不是,你可以換個(gè)角度去想。
韓伯祥說,怎么換?
百順說,水羊還是那個(gè)水羊,騷胡頭要有變化。
韓伯祥不高興了,狗日的,你嬸子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你倒是替她安排了。
百順說,叔,不是說把你換掉,我的意思,你身體上也要有一些變化。
韓伯祥說,我是肉長(zhǎng)的,一直就是這個(gè)樣子,又不是泥捏的,揉吧揉吧再捏出來。
百順說,叔,我有個(gè)辦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試。
韓伯祥睜開眼,把目光停留在百順的臉
上。
百順說,我不敢保證行,我是看嬸子到處給你找偏方怪麻煩的,叔,你知道,有些偏方用的不好,你身體受不了。
這倒是。這些日子沒少吃那個(gè)東西,豬身上的,羊身上的,牛身上的,狗身上的,都吃過。弄到現(xiàn)在,張大蘭看見誰家殺個(gè)公雞,都跑去看看,公雞身上哪會(huì)有呢?
韓伯祥問,怎么個(gè)試法?
百順說,剃須。
剃什么須,胡子唄。我擱個(gè)十天八天的就來剃一次啊。
百順笑笑說,都剃。
韓伯祥疑惑地看著百順。
百順笑得很詭秘。
韓伯祥說,聽你的,狗日的,要是不管,看我怎么收拾你。
到大隊(duì)部里,百順把韓伯祥從上到下都收拾了。
韓伯祥不僅絡(luò)腮胡子,胸脯、胳膊、大腿、褲襠里,渾身上下都毛茸茸的。百順除了頭上給他留個(gè)蓋子,剩下的給打理得一干二凈。
收拾完了,百順說,叔,還有一句話我得問你。
韓伯祥說,你說。
如果現(xiàn)在要你去找人,你是找嬸子呢,還是找那個(gè)?百順用手指指隔壁姜美芳的辦公室。
韓伯祥說,你說呢?
百順笑了。百順說,我這個(gè)方子還有一禁。
禁什么?
一周之內(nèi),你誰都不能碰,不僅不能碰,你身上的變化也不能讓她們知道。
韓伯祥說,還有嗎?
百順說,一周之后效果最好;十天之后,次之;過了半個(gè)月,無效。
韓伯祥似懂非懂地說,知道了。
百順拎著工具出門,回頭囑咐一句,按方服藥啊。
韓伯祥不知道百順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這身上的毛跟褲襠里的病有什么聯(lián)系呢?以百順的秉性,他是不敢和韓伯祥開玩笑的,百順不是孫光腚,不是三荒子和來福,他們偶爾開一下韓伯祥的玩笑,這都是有可能的。百順不會(huì),再說了,今天把全身的毛給剃掉了,倒是利索,身上有毛的時(shí)候,虱子在褲襠里爬來爬去的,你摸半天,干著急就是摸不到,現(xiàn)在它再爬出來試試,伸手就給逮住了。
韓伯祥雖然不知道百順的葫蘆里是什么藥,但還是按照百順說的去做了。一個(gè)星期的時(shí)間,他誰都不碰,白天回家吃飯,晚上去值班室睡覺。
這期間姜美芳來過,姜美芳要在值班室擠擠。韓伯祥說,不能擠,我這兩天身體不舒服。姜美芳有點(diǎn)不高興,和你擠擠,就是陪你說說話,知道你有毛病,心情不好,才來安慰安慰你,你還身體不舒服,你月經(jīng)來潮啊。韓伯祥也不好解釋,就給姜美芳說,過個(gè)三兩天,我去找你。姜美芳說,過三兩天我就不舒服了。
說歸說,姜美芳不會(huì)真跟韓伯祥計(jì)較,計(jì)較什么呢,就是這么個(gè)男人,別看他有時(shí)候說話兇巴巴的,他心里要是沒有你這個(gè)人,他都懶得抬眼皮看你,他是在意你,他才跟你兇,他肚子里有情緒,他不在你身上發(fā)泄,他去找旁人嗎?
三天之后是姜美芳自己過來的,反正韓伯祥說了,過個(gè)兩三天。姜美芳當(dāng)然不指望韓伯祥身體上有什么變化。過來,就是說說話,男人和女人之間并不都是床上那點(diǎn)事,有時(shí)候語言上的溝通,感情上的交流,比辦那種事要溫暖得多。
韓伯祥在看書,韓伯祥給姜美芳說過個(gè)三兩天,他說過就忘了,他不是真的期待姜美芳會(huì)過來,過來干什么呢?自己這個(gè)樣子,除了讓姜美芳失望,也使自己難堪。
韓伯祥看的是醫(yī)學(xué)上的書,書里面的內(nèi)容基本都和褲襠里那點(diǎn)事有關(guān)系。專業(yè)上的內(nèi)容韓伯祥是看不懂的,韓伯祥想看的是和剃毛有關(guān)的內(nèi)容。沒有,韓伯祥找了很多這方面內(nèi)容的書,他沒有看到剃毛和褲襠有什么關(guān)系。
韓伯祥看書,姜美芳也沒有去打岔,很多時(shí)候都是這樣,姜美芳睡自己的覺,韓伯祥看報(bào)紙,有時(shí)候還要寫上幾筆。韓伯祥寫的都是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那些會(huì)議在韓伯祥看來,都是重要的會(huì)議。如果是二韓的群眾大會(huì),韓伯祥是不寫發(fā)言稿的,在二韓,韓伯祥說什么都是對(duì)的,天上地下男人女人,他什么都說。到公社就不能信口開河了,就要講個(gè)一二三四了。
韓伯祥的目光離開書,撕下一綹子紙,揉一片子韓伯良給的煙葉,他要再卷一支煙抽。韓伯祥知道姜美芳已經(jīng)脫了睡了。從搭在床頭上的衣服來看,姜美芳是脫光了。狗日的百順,是你說的一周的時(shí)間效果最好,好什么了,我這里一點(diǎn)反應(yīng)也沒有,這不是把人熬死了嗎?
韓伯祥擦根火柴,把煙點(diǎn)上,火光映紅了他的臉,他的臉上滲出密密麻麻的汗珠子。
煙抽得再多,覺不能不睡。姜美芳已經(jīng)來了,已經(jīng)脫了睡了,你還裝傻,你能裝到天亮嗎?再說了,姜美芳又不是不知道你有病,人家來了,也不是只求那點(diǎn)事,人家是圖個(gè)溫存,你還拿個(gè)什么勁呢?
韓伯祥只能一件一件地脫衣服。和姜美芳在一起跟和張大蘭在一起不一樣,如果是張大蘭,韓伯祥會(huì)和衣倒在床上,后邊的工作都是張大蘭一個(gè)人做,張大蘭要是有個(gè)什么想法,她會(huì)把韓伯祥的衣服扒了,這個(gè)娘們,比母狼都色。姜美芳雖然有想法,她還放不開,還有點(diǎn)害羞,畢竟比張大蘭小十幾歲呢。但是,溫存還是必須的,姜美芳喜歡韓伯祥抱著她睡。姜美芳說,有韓伯祥抱著,睡覺踏實(shí)。
今天的事出乎韓伯祥的意料之外了,韓伯祥像往常一樣去摟姜美芳,一開始姜美芳也是往韓伯祥身上偎的,在韓伯祥抱著姜美芳的一瞬間,姜美芳像是被熱水燙了一樣,嗷地叫了一聲。韓伯祥不知道怎么回事,姜美芳躲得越快,韓伯祥摟得越緊,姜美芳一邊掙扎,一邊叫,姜美芳的叫聲尖銳,有穿透力,這在以往是從來沒有過的,以前姜美芳的叫是輕的,細(xì)若游絲一樣,沒想到今天會(huì)這么反常。韓伯祥被姜美芳具有穿透力的叫聲喚醒了,一下子勃發(fā)了,雖然姜美芳還在掙扎,姜美芳感覺到了韓伯祥的變化,在韓伯祥進(jìn)入的時(shí)候,姜美芳安靜了下來,兩行淚水順頰而下。姜美芳一臉?gòu)珊o限纏綿地說,伯祥,你扎死我了。
九
真正讓百順剃頭的手藝能夠揚(yáng)名并且因此改變了他們這個(gè)家族命運(yùn)的人,不是韓伯祥,也不是因?yàn)榘夙樦魏昧隧n伯祥褲襠里的毛病這件事,這要從另外一個(gè)人說起了。
這個(gè)人叫常遠(yuǎn)學(xué)。
常遠(yuǎn)學(xué)是下派干部,一個(gè)年輕人,據(jù)說是地委書記章德寧的秘書。地委指示年輕人要到基層,到最艱苦的地方鍛煉,常遠(yuǎn)學(xué)就來到了二韓。
關(guān)于常遠(yuǎn)學(xué)下派到二韓還有另外一個(gè)說法。
地委書記章德寧是老干部,扛過槍,打過仗,跟日本人拼過刺刀一路走過來的,等成立了新中國,章德寧四十多了,婚姻還沒有著落。那個(gè)時(shí)候像章德寧這樣的干部很多,為了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shè),把自己的下半身給耽誤了。組織上對(duì)這些有過功勞和貢獻(xiàn)的同志很是關(guān)心,由組織出面,把這些同志請(qǐng)到各個(gè)院校給同學(xué)們講戰(zhàn)爭(zhēng),講那些血與火的場(chǎng)面,講自己英勇殺敵的精彩故事。這個(gè)學(xué)校講完,再到另外一個(gè)學(xué)校去講,把憧憬和夢(mèng)想留在那些十五六歲十七八歲的學(xué)生妹的腦海里。很多同志就是這樣收到了火辣辣的情書,那些稚嫩和火熱的語言,讓老同志不接受這樣的愛情都不好意思。章德寧也收獲了自己的婚姻,把一個(gè)十七歲的女孩吳夢(mèng)雨領(lǐng)進(jìn)了自己的生活。
夢(mèng)想和現(xiàn)實(shí)總是有差距的。
吳夢(mèng)雨一頭闖進(jìn)生活以后,啪的一聲把夢(mèng)想摔碎了。
章德寧的記憶和生活里只有戰(zhàn)爭(zhēng),有血與火,有一刀砍死一個(gè)敵人一刀又砍死一個(gè)敵人。章德寧把血肉橫飛的情景擺到飯桌上,把尸橫滿地的戰(zhàn)場(chǎng)搬到床上。不僅是生活中,在夢(mèng)里,章德寧也會(huì)突然來一句,同志們,沖啊!然后一腳把吳夢(mèng)雨踹到床下。吳夢(mèng)雨從地板上爬起來,終于學(xué)會(huì)了章德寧的一句話,你奶奶的,這覺沒法睡了。
吳夢(mèng)雨忍耐了十年,這十年吳夢(mèng)雨不是沒有離婚的想法,但她離不了。隨著章德寧的職位不斷升遷,離婚對(duì)她來說越來越渺茫。正好這個(gè)時(shí)候常遠(yuǎn)學(xué)出現(xiàn)了,常遠(yuǎn)學(xué)和吳夢(mèng)雨年齡相仿,情趣相投,這讓吳夢(mèng)雨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兩個(gè)人未必有實(shí)質(zhì)性的交往,然而有時(shí)不由自主地眉來眼去,讓當(dāng)偵察兵出身的章德寧嗅到了敵情。已經(jīng)在地方歷練十多年的章德寧在政治上已經(jīng)成熟多了,把常遠(yuǎn)學(xué)處理重了,吳夢(mèng)雨會(huì)不高興,不高興都不怕,怕就怕吳夢(mèng)雨鬧,一鬧,這個(gè)事就掀開了。如果不處理,這樣發(fā)展下去肯定要出更大的問題。還有,章德寧是位愛才的領(lǐng)導(dǎo),他看得出來常遠(yuǎn)學(xué)這個(gè)年輕人有才華,考慮今天這個(gè)事我給他留有余地,以后他就會(huì)感念我的恩情。怎么辦?就下派吧,給他找一個(gè)偏僻的地方,鍛煉鍛煉。
常遠(yuǎn)學(xué)來到二韓時(shí)值初冬,皖北的初冬滿目蕭索,曠野里一點(diǎn)綠色也找不到。
韓伯祥在帶著群眾興修水利,每年都是這樣,到了冬天,地里沒有農(nóng)活了,韓伯祥就要給社員們找點(diǎn)事做,有事做了,渾身的勁才有地方釋放。這么漫長(zhǎng)的冬季,如果讓社員都閑在家里,那么多的年輕人,男男女女的,一身的騷勁,一身的浪勁,保不齊會(huì)出多大的婁子。
這樣的場(chǎng)面常遠(yuǎn)學(xué)是見過的,在地委跟著章德寧也是經(jīng)常到鄉(xiāng)下跑的,一年四季總有一些時(shí)候到基層去看看,但像今天這樣,直接參與這樣的場(chǎng)面,他是第一次。大冷的天,男人把棉襖脫了,光著個(gè)上身,甩開了膀子干活,那些姑娘,那么單薄的身子,穿的也單薄,兩個(gè)人抬一個(gè)筐,你追我趕的。干累了,韓伯祥就招呼休息,休息是干什么呢?常遠(yuǎn)學(xué)當(dāng)然知道,就是要大家歇歇,工地上搭著簡(jiǎn)易的棚子,里面燒的有開水,負(fù)責(zé)伙房的人,把熱水抬到工地上,誰要是渴了,就自己舀上一水瓢,咕嘟咕嘟地喝上一氣,然后是下一個(gè)再咕嘟咕嘟地喝。喝完了水,還沒有干活的意思,男人要抽一支煙,說說話,女人要找個(gè)僻靜的地方,打理一下該打理的事。通常情況下,女人都是三兩個(gè)人結(jié)伴,要走到離工地很遠(yuǎn)的地方,找一個(gè)水渠,收拾自己。常遠(yuǎn)學(xué)不知道這些女人要去干什么,問韓伯祥,她們是不是回家了?韓伯祥說,不是。韓伯祥說不是,也沒有準(zhǔn)確地給常遠(yuǎn)學(xué)說這些女人在干什么。常遠(yuǎn)學(xué)戴眼鏡,斯斯文文的。就有人給常遠(yuǎn)學(xué)逗趣說,常干部,你去看看吧,她們躲在溝渠里沒有影了,你看看是不是跑了。常遠(yuǎn)學(xué)這樣的,沒有基層工作的經(jīng)驗(yàn)。經(jīng)驗(yàn)不是別人教出來的,是在實(shí)踐中慢慢積累的。韓伯祥眼看著常遠(yuǎn)學(xué)奔著溝渠走去,他也沒有阻攔,對(duì)常干部來說,這也是他來到基層要實(shí)踐的內(nèi)容之一。
在二韓,常遠(yuǎn)學(xué)看不懂的地方還有很多。常遠(yuǎn)學(xué)來到二韓的第一天,是在韓伯祥家吃的飯。一日三餐,飯都是張大蘭做,一整天的時(shí)間,韓伯祥沒有給常遠(yuǎn)學(xué)介紹張大蘭。在韓伯祥看來,這個(gè)是不用介紹的,不管哪個(gè)干部來了,都是在韓伯祥家吃,做好了,吃完了,干部走了,沒有人去問張大蘭是誰。別人不問,是因?yàn)橹缽埓筇m是韓伯祥的女人。常遠(yuǎn)學(xué)沒有看明白,他沒有看明白不是說他這個(gè)人笨,是有些事他分辨不了。在常遠(yuǎn)學(xué)看來,如果張大蘭是韓伯祥的女人,為什么韓伯祥晚上睡覺要在值班室睡?當(dāng)然,他是大隊(duì)書記,在值班室值班也是對(duì)的,問題是有時(shí)一起來值班的還有姜美芳。
最讓常遠(yuǎn)學(xué)不可思議的是,有兩次三荒子和來福跟他半真半假地開玩笑,說馬翠花肯定最喜歡常干部去她家,因?yàn)橹挥兴霉べY有現(xiàn)錢,可以不用記賬。第一次常遠(yuǎn)學(xué)沒弄清什么意思,以為是指大隊(duì)安排吃派飯的事,還傻乎乎地表示當(dāng)然要給現(xiàn)錢,惹得大家樂不可支。第二次他終于知道了他們說的是怎樣的一件事。常遠(yuǎn)學(xué)既害羞又生氣,不像話,實(shí)在是不像話。不料他更為吃驚的還是韓伯祥居然不以為然地說,一個(gè)寡婦,養(yǎng)三個(gè)孩子,都要吃飯。
真是開眼界啊。常遠(yuǎn)學(xué)心里想,回去,一定得回去,這個(gè)二韓不能住。
常遠(yuǎn)學(xué)給韓伯祥說眼看要過年了,他也要回去了。他把自己寫的基層工作報(bào)告拿出來,要韓伯祥過目一下,如果屬實(shí),韓伯祥作為大隊(duì)書記,在他的報(bào)告上簽個(gè)字,回到地委他要遞上去。
韓伯祥看著厚厚的一摞紙,說晚上看。
常遠(yuǎn)學(xué)說,我今天先到街上去,理個(gè)發(fā),來二韓兩個(gè)月了,澡洗得少都不說了,頭發(fā)都沒有理過。
韓伯祥說,理發(fā)你還去街上干什么?你看看我們二韓的百順,什么樣的頭不能剃?手藝好得不能說。
常遠(yuǎn)學(xué)說,不知道百順明天有沒有空。
韓伯祥說,給你理發(fā)還什么有空沒空的,就上午,什么活都不安排他的,就給你理發(fā)了。
常遠(yuǎn)學(xué)說,那好。
常遠(yuǎn)學(xué)從地委過來的時(shí)候,專門理過發(fā),常遠(yuǎn)學(xué)的發(fā)型是學(xué)者型的,三七開。雖然兩個(gè)月的時(shí)間過去了,發(fā)型的基礎(chǔ)還在。百順過來給他剃頭的時(shí)候,常遠(yuǎn)學(xué)說,就照這個(gè)樣子,剪短一點(diǎn),周圍修理一下。
百順說,常干部放心,會(huì)給你剃好的。
在大隊(duì)部的院子里,百順認(rèn)真細(xì)致地給常遠(yuǎn)學(xué)剃了個(gè)頭。常遠(yuǎn)學(xué)不是二韓的村民,也不是韓伯祥,常遠(yuǎn)學(xué)是上面來的干部,不認(rèn)真細(xì)致能行嗎?
剃完了,百順把圍布輕輕除去,把常干部脖頸上殘留的短發(fā)噗噗地吹去。百順說,常干部,好了。
常遠(yuǎn)學(xué)用手撫了一下腦袋,好了?
百順說,好了。
常遠(yuǎn)學(xué)說,謝謝。
百順激動(dòng)了,百順剃過那么多人的腦袋,死人就不說了,這些活著的,沒有一個(gè)給他說聲謝謝的,今天常干部說了,到底是有文化的人。
百順收拾工具,準(zhǔn)備回家。
常遠(yuǎn)學(xué)進(jìn)了屋子,屋子里有一面鏡子,鏡子是吳夢(mèng)雨送給他的,他怕把鏡子摔碎了,放在床頭,特別珍惜。
常遠(yuǎn)學(xué)把鏡子拿出來,在門外照了一下。這一照不要緊,鏡子里哪有常遠(yuǎn)學(xué),鏡子里是一個(gè)剃著蓋子頭的男人,跟二韓所有的腦袋沒有任何區(qū)別。
常遠(yuǎn)學(xué)差點(diǎn)哭出聲來。
來二韓兩個(gè)月了,常遠(yuǎn)學(xué)用地地道道的二韓話罵了一句百順:日恁娘,你這剃的是什么頭?
因?yàn)轭^剃得太難看,常遠(yuǎn)學(xué)不回去了,這個(gè)樣子到了地委還不被人給笑死啊,尤其是吳夢(mèng)雨,怎么見?
公社捎信來,地委打來電話,春節(jié)放假了,常遠(yuǎn)學(xué)也可以回去過年了。
常遠(yuǎn)學(xué)對(duì)捎信的人說,二韓的工作太忙,過完年還有幾個(gè)工程要干。常遠(yuǎn)學(xué)說的不是瞎話,的確還有幾道溝渠沒有修整完。
韓伯祥說,這不要緊,過完年,你可以再回來。
常遠(yuǎn)學(xué)說,地委派我過來,我就要把工作做完,我哪能半途而廢呢?
常遠(yuǎn)學(xué)整整在二韓工作了一年,這中間地委打來幾個(gè)電話,地委書記章德寧也來了親筆信要常遠(yuǎn)學(xué)回去。常遠(yuǎn)學(xué)當(dāng)然也想著回去,問題是自己這個(gè)樣子實(shí)在是無法見人。他曾經(jīng)讓百順給自己修理過發(fā)型,在修理的過程中,常遠(yuǎn)學(xué)把自己從前的照片拿出來,要百順按照照片的樣子給自己剃。等剃完了,常遠(yuǎn)學(xué)照鏡子,又是不倫不類。常遠(yuǎn)學(xué)徹底失望了,狗日的百順啊,你就把我埋在二韓算了。
章德寧要去省里工作了,在去省里之前,他還想著常遠(yuǎn)學(xué),為什么打這么多的電話他就是不回來呢?章德寧決定親自去二韓看看,這個(gè)常遠(yuǎn)學(xué)搞的是什么名堂。
這已經(jīng)是常遠(yuǎn)學(xué)來二韓興修水利的第二個(gè)年頭了。
章德寧來的時(shí)候,地委的、縣里的、公社的領(lǐng)導(dǎo)都隨著來了,一溜子小車在二韓的土路上卷起漫天的灰塵。
二韓的工地上紅旗招展,在二韓住了一年的常遠(yuǎn)學(xué)已經(jīng)徹底融入了二韓,不僅說的話和二韓人沒有區(qū)別,蓋子頭也和二韓人沒有兩樣了。
常遠(yuǎn)學(xué)脫去棉襖光著膀子在挖土,以至于章德寧走到他跟前,他都沒有抬頭。
章德寧的眼睛濕潤(rùn)了,他沒有看錯(cuò),這個(gè)年輕人是個(gè)人才,到哪里都能發(fā)光發(fā)熱。
就這樣,常遠(yuǎn)學(xué)常干部要回去了,要跟著章德寧去省城了。因?yàn)樽叩锰蝗唬n的很多社員留下了離別的淚水,社員紛紛走到常干部跟前,一再給常干部說,別忘了二韓,以后有空了,一定來二韓看看。
常干部上了車,群眾把車都圍住了。
章德寧被這個(gè)場(chǎng)面給震撼了。
韓伯祥走到車子跟前,再一次和常遠(yuǎn)學(xué)握了握手。韓伯祥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說,常干部,你的工作報(bào)告還在我那里,我都簽過字了。
常遠(yuǎn)學(xué)今年沒有寫工作報(bào)告,韓伯祥說的報(bào)告,還是去年的那一個(gè),那個(gè)報(bào)告費(fèi)了常遠(yuǎn)學(xué)不少心思,常遠(yuǎn)學(xué)把他來到二韓聽到的、看到的,都寫上了。他寫了大隊(duì)書記韓伯祥和婦女主任姜美芳的事,甚至把馬翠花和二韓男人的事也寫在報(bào)告里了。
常遠(yuǎn)學(xué)意味深長(zhǎng)地笑了,常遠(yuǎn)學(xué)對(duì)韓伯祥說,不帶了,你想保留就保留著吧。
車子走遠(yuǎn)了,韓伯祥還在自言自語,這么好的報(bào)告,也不讓省城的干部過目過目。
尾聲
小說寫到這里,我就該收手了,這中間,和賢粹通過幾個(gè)電話,我們聊的都是和這篇小說有關(guān)的話題。
這篇小說我寫了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期間和賢粹聊過四次,大多時(shí)候是我給他打電話,因?yàn)閷懙氖琴t粹這個(gè)家庭的故事,很多時(shí)候我拿不準(zhǔn)是不是可以這樣寫,或者那樣寫是不是更好,所以,每寫一個(gè)章節(jié),我就給賢粹發(fā)過去。
我必須要說明的是,關(guān)于常遠(yuǎn)學(xué)和賢粹這個(gè)家庭的故事遠(yuǎn)沒有結(jié)束,以至于到現(xiàn)在,賢粹說到常遠(yuǎn)學(xué)的時(shí)候,都是用掩飾不住的親昵口氣叫常叔叔。
賢粹的常叔叔曾經(jīng)在賢粹打工的那個(gè)城市當(dāng)過一把手,所以賢粹一再說,沒有常叔叔肯定也沒有我的今天,但是,他對(duì)我的好我會(huì)一輩子記在心里面,小說里就不要寫得太多了,免得有人聯(lián)想,給他帶來不好的影響。
另外一個(gè)問題是關(guān)于馬翠花的,賢粹也給我商量過。賢粹說,哥,這個(gè)故事里能不能把馬翠花那些情節(jié)去掉?
我當(dāng)時(shí)沒有說行,也沒有說不行,我給賢粹說,再想想吧。
又過了兩天,賢粹說,哥,小說是你寫的,那些情節(jié)要還是不要,你說了算。
我說,賢粹,在那個(gè)年代,哪一個(gè)二韓男人的故事能離得開馬翠花呢?
責(zé)任編輯 苗秀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