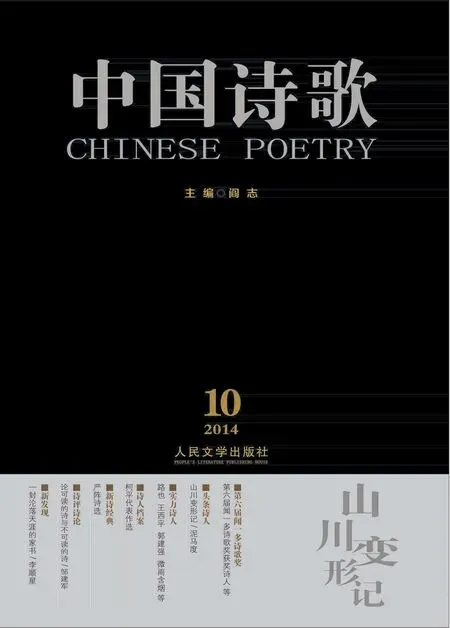霍楠楠 的詩
霍楠楠 的詩
鈍,與銳
缺口縱深
一把斧頭沉寂在柴堆旁
雪水擦亮一切
漠然的沉思呼喊
夜晚的雜念叢生
奔跑在城市邊緣的人
繼續用螢火點燃自己的身影
成功地寄走時間的銹斑
擁堵血脈的暗礁
鐘盤漫不經心的旋渦
衣襟上粗腳的針線
使繡花針失卻了閃爍的永恒
成為無數個啞然失聲的街燈
試圖在黃昏之后
不尋常地轉向另一面的月光
鋒利的恐懼
時刻提醒武器的華麗
生命皺縮成一枚核果
被一頂禮帽概括的激情
總是看見自己躲藏在
腐爛的落葉之后
春天又被大雪喚出
山峰的輪廓突現浮出的預感
無論誰攜帶著平靜的衰落
或者
爆裂的黑洞
古木
死去的一天浸淫古樹的葉脈
一首詩的溫度掙扎在枝葉的靈犀
夜深時挖掘松林深處的佛堂
快要老去的燭光被烙燒
如同厭倦了這許多的繁華
我的河流從不滋養浮夸的枯枝
而正在經過冷漠
和藐視的那場孤單
其實并不僅僅屬于你
一場安靜和上升的時空
更容易讓我雙手合十
布谷鳥可以隨處叩響巖石
巧合的是
日光已裝滿了純粹的火焰
愛,這永生者
永生是祈福樹送去的紅緞帶
你系上后就走開了
我看見的名字
是夜晚深海波動的鱗光
漫游者藏身于林中的華蓋
帶出清冽作響的山風
和向東流淌的蜂蜜
那是我們極度渴望也未獲得的甜
糖中毒也許只是個傳說
在花朵們縱向排列的蜂巢
同時會亮出鋒利的尾針
多情的顫抖
一棵樹的及時冥思
也來不及說出一行閃射而出的光
那些被落葉紛亂的文字
打亂
我轉身,帶走一盞蠟燭的風聲
掀開的杯蓋燙傷了手指
整八點的腳步聲
又被林中的小路拉回了思緒
龐大的音階安然輾轉于曾經陌生的手指
我把濡濕的光團掛上發亮的樹梢
一處未干的墨跡暈入你走音的歌喉
雨霧的另一個名字叫潮濕
花重之時,鉆出一只秋蟬的翅膀
而,打亂的另一個名字,可能是你
又見雨落
一切都被放大了,
包括憩在指尖
的雪花,
雞鳴而起的晨露
翩然歸來的赤蛺蝶
如一場濕吻
草尖的雨珠很有愛
終結昨日的亂夢
你可以抱怨這白夜的短暫
睜開眼
看滿地的碎玉和裂帛
裝修
所有的書籍藏進柜子里了
窗外的土跑了進來 書桌上
浮了一層 咖啡杯子裝滿細小的顆粒
掀開報紙的一角 一塊干凈的陸地
羅裙變暗 高跟鞋走進黃昏的博物館
鍵盤和鼠標 敲打之后還能使用
我也覆了一身
一如昨天的詞句
還在思想的霧霾里生著銹斑
保護色
你有一張面具
每個人都有一張
你無法分辨是蜥蜴還是鱷魚
它們靜止時就是樹葉 或者巨石
罌粟嵌在曼妙的軀殼里
向日葵低下沉重的頭顱
而那些多肉植物
其實就是我
為了保護自己而生出的利刺
數字與文字
白天是數字,五斗小米,
打亂有序的組合,用來供養肌體
夜晚變成了文字。一樽清酒,
拿來慰藉被生活消磨掉的邊邊角角
文字的光芒像蹲在角落的青銅小獸
數字的邏輯是被織成濃彩的錦繡掛毯
可以被幾串數字從文字里拉回
也能夠用一段文字來洗滌數字沾染的塵埃
而這些亂碼,清酒與小米的組合
若構成肖像,就會是那個時而模糊
時而清晰的小女子
動與靜
練琴 讀詩
白熾燈的綻放安撫夜色
一只蝴蝶飛到第七樂章的升調
幾把提琴拉扯馬鬃的微涼
麋鹿垂下仰望的角度
是那盞就要熄滅的燈光
正穿過
無數個窗口望出去
我忽然聽到
一顆種子包裹著彩虹
正由干裂的大地向遠處傳播
醉
穿西裝的人躺上冰冷的石塊
思想者坐在他身旁
他睜開眼睛 與同伴的目光
匯聚成九十度的夾角
之上一部手機的鈴聲
在夜色中像迷霧一樣散開
搖椅之夢
兩個句子梗在那兒了,起來,躺下,
不得伸展 被藤條的曲度托起的我,
用腳尖和手臂的動作
在河流里漂了整個下午
一地的詞語 和故事的碎片
碼起來兩組最為神秘的,
堆砌成我的城堡,即使看起來虛幻與縹緲
只允許一個人進入的時候,也必須
輕輕叩響食指
六月的雜音
坐擁書城為一個詞尋遍整座森林
深夜火車嘶鳴過平靜的草原
凝神諦聽村莊的神秘河流之永恒
時光在指縫間流淌,欲望滿布
的琴鍵,誰將奏響明日之肖邦
眺望的棱角倒伏于被擦亮的羽翼
我的名字隱身在躁動不安的音符
像零星的鐵閃爍在時間的扭結里
一瞬偶爾的失音提升了六月的幻覺
斷流與干涸,石塊的寂與硬
驚濤拍岸的草木,海鷗伏身于燈塔
找尋風的再次漲潮,或者一場雪
不動聲色的溫潤和閃電的登堂入室
沉香縷縷不能直達的神龕 為黑暗
斬獲黎明的箴言 明媚的溪流
寧靜在峽谷最深處 干枯的積郁
沉入湖底 榮耀顫抖 夢想
若隱若現 鳥鳴即起
一根白發
這根白發是如此的驕傲
這么短,卻這么挺直地
站立于我的頭頂
是白鶴立于黑暗的夜晚吧
自由地亮開雙翅 幾欲高飛
還是
更像一面白色的旗幟
迫使我向時光低頭、向歲月認輸
或許什么都沒有意義
它只是這么直楞楞地刺了出來
向生活的簡單和平靜
宣告一下自己獨特的柔軟
和不可替代的永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