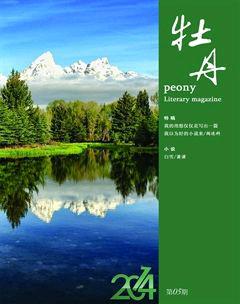拒絕三題
趙文輝,1969年出生,河南輝縣人。中專畢業后干過棉檢員、酒樓經理和副刊編輯等,現在南太行開一酒肆,兼營小說。在《北京文學》《長城》、《莽原》等刊物發表作品若干,部分被《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小小說選刊》轉載,《刨樹》入選《2011中國年度短篇小說》。出版專集10部,曾獲第一屆河南省文學獎和冰心兒童圖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
抬新娘
三十五歲上下的男人身上迸發的那種魄力是很吸引人的,特別對那些情竇初開的女孩子。一旦愛上了便發瘋發狂,全然不顧。小潔和大郭,就是這樣一種情況,但大郭拒絕了小潔的多情。在咖啡廳里,小潔緊拉著大郭的手,用眼淚訴說自己熾熱得不能把守的愛情:“我不能沒有你……”
大郭搖頭:“我有老婆和兒子。”
“我不在乎!我只要你愛我,我現在就把一切給你……”
唉,女人一旦和愛情沾上邊,要么使你聰明,要么使你瘋狂。大郭不知道該如何撲滅小潔心頭不該燃起的這團火,他對小潔說:“我很愛我的老婆,老婆也很愛我。”
“愛是可以轉移的!我的愛會讓你獲得更大的滿足和意想不到的幸福!你老婆的愛,小巫見大巫,滾一邊吧……”
這個女孩真是要燃燒起來了。大郭正一籌莫展時,手機響了。老婆打來的,問他怎么上班時間不在辦公室?大郭心騰了一下,回答說我辦點事一會兒就回去。老婆又說:“咱家客廳的開關繩斷了,咱們下班后抬新娘?”大郭回答:“嗯,抬新娘。”關了手機,一臉幸福的笑。小潔在一邊聽見了,問:“啥叫抬新娘?”
大郭說“抬新娘就是……”,忽然打住了,他有了主意,就對小潔說:“你把咱辦公室的錄像機拿出來,我錄給你看。”小潔一臉不解。
這天下班后,大郭先老婆一步進了家,把錄像機選了角度支好。這時門嘭嘭響了,大郭問:“誰?”門外答:“張惠妹!”開了門,“張惠妹”嘻嘻笑著進來,問大郭:“兒子還沒回?”正說著,門嘭嘭又響,他倆會心一笑問:“誰?”門外答:“劉德華!”開門進來的是他們十五歲的兒子。大郭朝墻上的開關努努嘴,兒子立即明白了,歡呼道:“抬新娘,抬老爸!”大郭找來燈繩,老婆和兒子蹲下來四只手交叉一搭,大郭跨上去,老婆兒子齊嗨一聲站了起來。大郭在上邊干活,老婆兒子在下邊唱:“抬、抬,抬新娘,新娘梳了兩條辮;抬、抬,抬新娘,新娘蒙了一塊布……”
唱著唱著兒子問:“接好了沒有?”大郭回答:“好了。”兒子沖他媽一擠眼,兩人齊唱:“抬新娘,新娘跌了個屁股墩……”一松手,大郭叭嘰一下跌在地上。開心的笑旋即溢滿了客廳。
這笑聲深深刺疼了小潔的心。她看完錄像,大郭告訴她:“最早的時候,是我們抬兒子玩,這兩年兒子長大了,特別有力氣,就和他媽抬我玩,或者和我抬他媽……有一次,我往墻上打釘掛鏡子,沒有梯子又找不到高椅子,這時兒子靈機一動,說咱們抬新娘。就這樣,以后,我們家接開關繩、打釘、換窗簾布,都不用梯子凳子。抬新娘成了我們一家三口的固定節目,如果我離開這個家,墻上有活了,沒了我,她娘倆該傷心成啥樣?我想都不敢想。”小潔低下了頭,大郭又說:“這樣溫馨的生活,哪個男人愿意背叛?你呢,會愛上一個背叛幸福的男人嗎?”
小潔嚶嚶地哭了,雙手捂著臉,離開了這個給她講“抬新娘”的男人。
一個名字把你擊退
男人和女人是一對情人。
兩人經常在女人家里幽會。女人的丈夫在海南做生意,剩下她一個人,空穴來風的事也就有了可能。更主要的是,十年前女人曾經暗戀過男人,還為他寫過一本帶淚的小詩。那時女人是一個業余作者,男人則小有名氣,女人悄悄愛上了男人,做過無數次令人臉紅的夢。然而此夢悠悠,十年后女人的丈夫為她買下一個書號,在女人的詩集發行式上,男人作為特邀嘉賓應約而來。之后不該發生的事情也就發生了。
女人很羨慕那個成為男人妻子的女人,當年她就猜想甚至嫉妒過那個女人。她很想知道,那個女人是干什么的,又是一副什么模樣,究竟憑什么魅力吸引住了男人。女人問男人,男人搖搖頭,說你問這些有啥用?女人卻堅持要問,有時兩人正做著事,女人突然問:怎么樣,和你那位滋味一樣吧?結果弄得男人很別扭,事也做得極不漂亮。或是做完事又問:你那位一定個子很高嬌嬌不群吧?男人特煩。
后來女人弄清了男人的住處,萌生了一個念頭,要去男人家里看看。她把自己的發型弄亂,梳成兩條短辮,找出一件舊衣服換上,打扮成一個中學教師。如果男人的妻子問她,她就回答自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前來拜師的。她想象不出自己的突然降臨會使男人如何大吃一驚,真逗!
于是她在一個黃昏來到了男人家樓下。
幾個六七歲的小男孩正在彈溜溜球,女人彎下腰拍拍手,小孩們立即停下來。女人向他們打聽男人的住處,幾雙黑亮黑亮的眼睛相互瞅瞅,問:她打聽誰家?一個小男孩站出來,一挺胸說:我家!是我爸爸的名兒。
女人一看,這個小家伙還真有男人的輪廓。女人歡喜地拉住小男孩的小手,問:你叫什么名字?旁邊幾個小家伙搶著回答:他叫黃愛郭!女人覺得小男孩的名字挺有意思,又問他為什么起這個名字?小男孩挺能說:爸爸姓黃,媽媽姓郭,爸爸愛媽媽……女人聽了,心里突然沉了一下。
正要上樓,小男孩忽然掙脫女人的手,“媽媽媽媽”叫著跑開了。女人一看,小男孩奔向了一個年輕的女人。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人,只一眼,女人就發現她的臉上有著獨特的自信和從容。年輕媽媽伸出雙手,小男孩跳入她的懷中,臟兮兮的小手勾住年輕媽媽的脖子,然后甜甜地親她,無言地……望去,就像果子懸掛枝頭一樣。
小男孩親完媽媽說:有阿姨找爸爸!
女人已經悄悄離開了。她一邊走一邊默念小男孩的名字,“黃愛郭、黃愛郭”,一種深深的疼碎在她的心房,彌散開來。
后來男人又去找女人,女人拒絕了他。
再后來女人和丈夫一起去了海南。endprint
煙蒂上的舞蹈
嫁給了林,便嫁給了擔心。露就有抹不完的淚。
林像個大孩子,天真又冒失。和露結婚兩年,露一直沒懷孕,倆人商量著去醫院婦科查查。都沒毛病,醫生是個耐心的大姐,問了他倆很多生活上的細節,問到那個環節,醫生笑了:原來這兩年林根本沒進對地方!就這樣,林每次還要吹噓自己是東方不敗……露越想越可笑。這只是個喜劇,喜劇之外的冒失就嚇人了。一次露過生日,林買來一束玫瑰,露去接花,卻見林的手背在往外冒血,哇一聲叫起來。林這才發現自己受傷了,卻高低想不起什么時候又是怎樣把手弄破了。這個冒失鬼!
想林確實是個大孩子,如此倒也無妨,只是多一份牽掛罷了。誰知他們有了孩子,隨著孩子的長高,林的脾氣卻還是原地不動,做事照樣冒冒失失。讓露更為不安的是,林在感情上也冒失起來。
林半路迷上了文學,作品沒怎么著卻先患上了文人的酸病:多情。露在林的換洗衣裳里時不時搜出一些女人寫給林或林寫給女人待發的信,不愧搞起了文字,比當年寫給露的情書來勁多了,長功夫多了。有一回,居然搜出一只安全套,露哇哇大哭。林又是下跪又是打自己嘴巴,寫了保證書,又生著法哄露。露的情緒剛剛穩定下來,林又茶余飯后羨慕起河南那個寫小說的某某,說人家一口氣換了四個老婆,最厲害的一次就是去天津領獎,把某大刊的編輯都勾走了啊……露氣得把手中的茶杯摔了。
越來越嚴重——露發現林的思緒開始迷亂起來,總在拾掇自己的行裝。拾掇好卻不需要去哪里,林便將這些行裝擱下。露悄悄替他打開行李,一樣一樣放回原處。可是過幾天,林照樣會再捆扎到一塊。卻還是無處可去,只好又將行裝放下。如此反反復復,讓露一顆心揪起又放下,放下又揪起。露猛然想起了托爾斯泰,這個大文豪一生都在隨時準備出逃,難道自己也要像托爾斯泰的妻子一樣防備林一輩子嗎?
真的遇到了外出,林便歡天喜地成了一個孩子。露細心給他準備行囊,他很不耐煩。露查看他的機票,問為啥不上保險?他更不耐煩,說買啥保險?你巴我出事呀?一句話噎得露淚花在眼眶里轉。
露不知怎樣才能拴住林的一顆心,只好抹著眼淚期待。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
不知是哪一天,林、露和小女兒晚飯后去散步。林噙著煙卷,和小女兒逗玩時不小心掉了下來。掉在地上的煙卷已快燃完了,只剩下一個長煙蒂,林竟彎腰撿了起來,吹吹海綿嘴上的灰土,又撲撲吸起來。露看呆了!以前林可不是這樣,就是整根煙卷掉在地上,林也不屑去撿。露內心狂喜起來,她隱約感到,自己期待的東西來了。露像個孩子一樣歡快起來,她拉起女兒,伴著廣場上的音樂,跳起了街舞。
林看著她們,身子也在一搖一晃,煙還沒燃完,火光一閃一閃的。露就覺得,音樂是從那煙蒂上發起的。她恍然若悟,仿佛在煙蒂上跳舞一樣。
煙蒂上的舞蹈告訴露,愛情也有熬出頭的時候。果然,第二天出門,林破天荒地把保險鎖轉了幾個圈,確信上足了才罷休。以前嘛,讓他出門把鎖轉幾個圈,不但不做,還沖露吹胡子瞪眼:轉個啥?家里有啥值錢東西?
一個男人,說對家負責就對家負責了。露在心里說。
責任編輯 婧 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