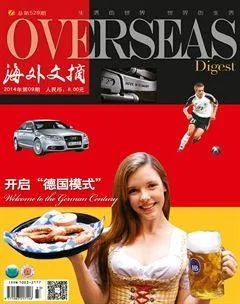讓的方舟




1940年6月22日下午,巴黎以北60公里,希特勒走進貢比涅森林中的一處空地。大大的納粹標志迎風展開,他檢閱了列隊的納粹士兵,然后登上曾經屬于費迪南·福煦(一戰中著名的法國元帥)的私人車廂。1918年11月11日,德軍曾在這節車廂內簽署了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所以,對于希特勒,這里真是一個恰當的地點。他坐在福煦的椅子上,兩邊是戈林、里賓特洛甫、赫斯,他們正目睹法國的投降。如今,在那節車廂的復制品中,你可以觀看這段歷史的新聞影片。這是希特勒建立他千年帝國夢想的重要一步。當然,4年后,帝國轟然倒塌,希特勒一命嗚呼。
還是在這片森林里,埋藏著一段截然不同的歷史。50年前的8月,35歲的前海軍軍官讓·瓦尼埃在位于森林邊緣的特羅斯利村購置了一座破敗的小屋。屋里沒有盥洗室,只有一個水龍頭和燒木柴的灶,他給小屋取名“方舟”(L’Arche)。然后,瓦尼埃邀請兩位智障人士拉斐爾·斯密和菲利普·蘇克斯搬進小屋,和他共同生活。拉裴爾和菲利普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擁擠不堪的精神病院里度過的。回首過去,讓·瓦尼埃說:“當時我絲毫沒有想到這將是一個改變世界的宏偉計劃。”
他認為自己、拉斐爾和菲利普可以像一家人一樣,后兩位可以擠進他老舊的汽車一起出去兜風。但就像圣經中的芥末種子,“方舟”的擴張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讓·瓦尼埃堅持認為,那些有智障的人擁有許多正常人所缺乏的天賦,朋友們受其感召,紛至沓來。更多的房產被購置,更多的人從精神病院被拯救出來。現如今,全世界每個大洲都有“方舟”的社區,共146個,它們分布在35個國家,從孟加拉到布基納法索,從愛爾蘭到象牙海岸,從巴勒斯坦到菲律賓。
希特勒造訪貢比涅森林,和讓·瓦尼埃到達特羅斯利村,二者并非全無關聯。二戰爆發時,讓·瓦尼埃才10歲。他的父親喬治·瓦尼埃少將是加拿大駐巴黎公使,功勛卓著的老瓦尼埃曾在作戰時失去一條腿。1940年5月,德軍大舉進攻巴黎,瓦尼埃一家被迫乘船撤到英國,再從那里返回加拿大。那次從法國波爾多到英國米爾福德港的海上之旅點燃了小瓦尼埃的想象,13歲那年,他便要求回到英國,進入位于達特茅斯的皇家海軍學院。
大多數家長一定不會同意孩子這么做。要知道那是1942年,穿越大西洋是相當危險的。數百艘德國潛艇潛伏在水下,伺機擊沉聯軍的船只。但老瓦尼埃顯然不是一般人(回國后他曾出任加拿大總督),他告訴兒子:“如果你確定這是你想要的,那就勇往直前。”這讓小瓦尼埃迅速成長,“既然父親信任我,我就可以相信自己;如果直覺告訴我這么做是對的,我就會義無反顧。”
我們在讓·瓦尼埃位于特羅斯利的客廳里交談,他今年85歲了,白發蒼蒼,有些駝背,但身材依然高大,散發著活力與平和。無論是會見無家可歸的人,還是國家元首,瓦尼埃總是身穿那件普通的藍色夾克,他說話有力,長長的手指總在比劃。困擾許多老年人的窘迫、遺憾、害怕、憤怒在他身上毫無蹤跡。相反,他充滿了生氣,有一顆開放之心,渴望繼續成長、學習,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快樂。
我們談話時,電話鈴響了,瓦尼埃邊接聽電話邊在記事本上用鉛筆做著細致的記錄。他家里沒有電腦或iPad,筆和紙對他來說就足夠了。數十年里,靠著筆和紙,他從未忘過一次會面,或者遲到過一次。瓦尼埃的紀律性極強,這源于他在海軍的良好訓練。
隨著二戰接近尾聲,瓦尼埃發覺海軍不是他夢想的職業。退役后,瓦尼埃選擇了學術生涯,在多倫多大學教授哲學。他喜愛教書,卻始終覺得這也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事。1963年,瓦尼埃前往法國拜訪他的靈性導師托馬斯神父,并尋求有關未來方向的指引。托馬斯神父那時是一家精神病院的院牧,在神父的建議下,瓦尼埃訪問了當地幾家精神療養機構,看到的景象使他異常震驚卻也深受感動。“這種感動在我參觀許多黑暗的地方(如監獄、貧民窟、麻風病人隔離區)時都感受到了。那些地方是可怕的,但正因如此,在那里發現的一丁點美好都特別可貴,讓人驚嘆。那些地方的人是與你我一樣的人,他們的臉上有憤怒和痛苦,卻也有著極度的溫和。每次參觀離開時,都會有人問我‘你會回來嗎?’在這句話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是一聲聲吶喊:‘我為什么被遺棄?我為什么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他們太渴望愛了。”
有好幾個月,讓·瓦尼埃都在對智障人士的待遇進行調查。“我探訪精神病院和相關機構,詢問病人的家屬,然后,我發現了一個‘悲慘世界’:這些人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受壓迫和最被羞辱的一群人。他們甚至并未被視為人,而是被叫做傻瓜、瘋子、蠢貨、白癡……人們只要給他們提供食物和住所,就仿佛是在行善。”巴黎以東有一座叫圣讓德瑞莫的精神病院,80個智障病人被鎖在一棟水泥建筑里。他們整天無事可做,大部分時間就圍成一圈走路。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智障人士也不一定能獲得更多同情。在一處農場,瓦尼埃遇到一個十幾歲的智障男孩,竟然被家人鎖在一間車庫里。
這些發現讓許多人憤慨,有些人選擇了奔走呼吁,催生變革。瓦尼埃則說:“發起變革沒什么不好,但我只會按我的方式去做。我能做的就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看看會發生什么。”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瓦尼埃遇到了拉裴爾和菲利普。兩人完全沒有謀生的能力,瓦尼埃決定邀請他們一起生活時,深知這將是一個終身無法變更的承諾,但他沒有絲毫猶豫,他只想給菲利普和拉裴爾一個家,一個以他們為中心的地方。
瓦尼埃發現,拉斐爾和菲利普讓自己重新煥發了活力,這是他在海軍和學術生涯里都沒有獲得過的。拉斐爾兒時患上腦膜炎,理解力嚴重受損,只能說20個單詞;菲利普得過腦炎,整天念叨著同樣的事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這兩個人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有殘疾,但和他們住在一起,瓦尼埃開始理解人性的真諦。“我們一起買東西、做飯、種花種草,三個人都過得很開心,常在一起哈哈大笑。在遇到他們之前,我的生活受我的頭腦和理智支配,而他們喚醒了我心中的童真,我開始隨心而活。”
雖然一開始瓦尼埃并沒有宏大的計劃,但他的所作所為卻符合了時代精神。在法國和意大利,智障兒童的家長開始共同抵制大型精神病院。在美國,著名精神病教授沃爾芬斯伯格大力倡導智障人士“正常化”。社會服務部門為瓦尼埃提供了經濟支持,希望他的“方舟”能接收更多的人。更讓人鼓舞的是,很多年輕人想要加入瓦尼埃的行列,試圖效仿他。瓦尼埃回憶說:“20世紀60、70年代是公社的時代,那時的年輕人都向往自由,想要擺脫政府的管制,嬉皮士大行其道。”有些年輕人只憑一時的熱情參與到幫助智障人士的行動,但還有一些人卻堅持了下來。就這樣,“方舟”不斷壯大,在法國其他地方、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開辟了更多的“方舟”之家。
世界各地的“方舟”社區不盡相同。在孟加拉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病人和穆斯林病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印度的“方舟”社區,大部分人則信仰印度教。智障人士是推動普世教會主義的最好榜樣:這些可愛的人憑著本能分享生活,不會因教義或信仰不同而爭執。所有這些社區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不是精神病院,而是真正的家,在那里,智障人士與正常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交流溝通。
“方舟”進入我的視線也是機緣巧合。早在大學里,我就有一位同學在畢業時放棄了大學助教的職位,說要去法國和智障人士一起生活。面對我的不解,她向我提到了讓·瓦尼埃。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瓦尼埃的事跡,雖然印象深刻,但也覺得這種做法有點兒極端。幾年后,我住在東京的哥哥嫂嫂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瑪麗,但瑪麗卻先天患有唐氏綜合癥,心臟和肺也出現多種并發癥,預計不會活過一個晚上。幸運的是瑪麗出生在東京,那里的醫生為她實施了手術,這樣的手術在英國是不會嘗試的。日本人把唐氏綜合癥患者視為特殊的人,稱他們為“天使”。
瑪麗還在重癥監護期間,讓·瓦尼埃正好訪問日本。我哥哥去聽了他的演講,他在家信中寫道:“如果你遇到聆聽他講話的機會,我勸你一定要抓住,他的圣德幾乎是可以觸摸到的。”我哥哥是位外交官,說話一向謹慎,所以,這樣的文字著實令我意外。又過了幾年,我在愛丁堡當牧師的表兄說起他認識讓·瓦尼埃。“我想見他。”我說。就這樣,我帶著表兄的介紹信去了法國。
在那個貢比涅森林邊的村莊里,我終于見到了“方舟”里的人們。他們都在“方舟”生活了多年,其中有的人像我侄女瑪麗一樣患有唐氏綜合癥,有的人像拉斐爾和菲利普一樣,大腦在子宮里或者在嬰兒時受過傷。晚飯后,我們圍坐在篝火旁一起聊天,有人拿出一個破舊的喇叭,大家便輪流吹奏,笑聲此起彼伏。
瓦尼埃的一名助手告訴我:“我無法具體證明,但我能強烈地感覺到,這些人比正常人更了解我、懂我。”在那里生活了幾日后,我也有了同感。在拜訪的最后一晚,我被自己所體驗到的一切折服,心潮澎湃,決定去小教堂里靜一靜。在教堂里,我遇到了走路、說話都困難的迪迪埃,他靜靜地陪我坐著,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仿佛能讀懂我心中的一切。人們常說,進入中年的好處之一就是,你不再對別人怎么看你感到焦慮。但多年前在“方舟”的那幾日里,二十幾歲的我就已經嘗到了這種滋味。對于我的學識和我取得的成就,這里的人們毫不感興趣,他們就想讓我做我自己。
20世紀90年代中期,BBC制片人邁克爾·西蒙斯·羅伯茲造訪了瓦尼埃的“方舟”。在制作一檔和基因有關的節目期間,羅伯茲采訪了多位科學家,他們認為給胎兒做B超可以提前預知他們是否患有某種遺傳疾病和生理缺陷,這樣父母們可以選擇到底要不要繼續孕程。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擔心這種“優生選擇”會為人類的未來帶去不好的影響。羅伯茲想為這種觀點找到例證,他說:“我聽說了‘方舟’的存在,了解到了讓·瓦尼埃的觀點——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就像弱者需要強者一樣,強者也需要弱者。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觸動。”
羅伯茲帶著攝制組來到了特羅斯利村,花了一周時間進行拍攝。從第一天早上,他就對這里“不平凡的平凡”驚詫不已。“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聚集到此,照顧這些智障人士,他們有的不能走路、不能說話,甚至不能自己吃飯。這里沒有白大褂,沒有被制度化、被醫院化,也沒有為它的神圣做廣告。他們就是一群想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愛的感覺幾乎觸手可及。我本人來自一個充滿愛的家庭,我愛過也被愛過,但我從未遇到過一處環境,愛意能像這般彌漫。”
羅伯茲說,電影、電視制作人大多都比較玩世不恭,“我們的工作使我們必須保持客觀,甚至是冷漠,你很難打動我們。但‘方舟’是個例外。當我們采訪讓·瓦尼埃時,他用了一個詞來形容智障人士——傳授溫和的老師,這也是我們體會到的。這里的人對外在的偽裝、教育、個人成就都不感興趣,他們迫使我們摘掉層層面具,直到我們回歸人性本真。”在那一周里,拍攝紀錄片的初衷變得“幾乎不重要了”,拍攝結束后,攝制組的一名成員甚至從BBC辭職,住進了“方舟”。
自首次拜訪后,我便定期回到特羅斯利村。我和讓·瓦尼埃漸漸熟識起來,經常開車送他去各地演講。他給各種各樣的人做演講,有犯人,有商人,也有主教,他們不光是被“方舟”的故事,還被瓦尼埃富有理智和情感的溝通能力所打動。盡管瓦尼埃的禮貌和從容無懈可擊,但我總感覺每次離開“方舟”,他都有點兒無所適從。
“沒錯,我的確有點兒不自在。”瓦尼埃說,部分原因是別人介紹他出場時的溢美之詞。“我不想聽到人們對我說‘您做的事兒太高尚了’,我總覺得他們的潛臺詞是,‘真慶幸承擔這事兒的是別人,而不是我’。但正是和有些瘋癲的人在一起時,我更快樂,更是我自己。我們那里的人都不受規則的困擾——著裝的規則、做事的規則。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千篇一律的社會里,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一樣——都想贏,我不想把自己禁錮在這樣的價值觀中。”
還有一些人,他們欽佩瓦尼埃的所作所為,但同時也認為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家要養、有工作要做、有孩子要照看,至于改變世界,他們就無能為力了。瓦尼埃說:“這是因為人們不夠自信。也許他們在生活中經歷過種種挫折,這給他們留下潛在的抑郁想法——‘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方舟’的核心理念是——每個人都是珍貴的,如果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珍貴的,那我自己便也是珍貴的。大家都可以從我做起,去改變世界,即使只是改變自己看人的方式。比如你走在大街上,路過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你與其考慮‘要給他錢嗎?’不如想想,你真的把他當人看待嗎?”
面對未來,瓦尼埃是充滿希望還是擔憂呢?“方舟”成立50年來,經歷過各種挑戰:資金短缺,人手不夠,越來越嚴格的衛生安全規定,某些國家正經歷政治動蕩,甚至是戰爭。瓦尼埃通過“方舟”組織,直接參與了過去半個世紀中一些較大的沖突,比如在愛爾蘭、以色列、巴爾干半島、盧旺達。我們這次見面時,他對在烏克蘭和敘利亞的“方舟”組織尤為關切。我回倫敦后不久,“方舟”在敘利亞的創始人就被謀殺了。瓦尼埃一生曾面對過無數困難,這賦予他一種務實的平和心態。“我們的世界是變化的世界。所以,我們要問的不該是‘未來是好還是壞?’,而是‘今天我該如何做才能實現自我、接納與我不同的他人,并幫助其中的一兩個實現他們的夢想?’”
今年春天我在特羅斯利的時候,一群年輕人正在“方舟”體驗生活。往常安靜的農場被嘻哈音樂和足球比賽擾亂。我坐在樓上謄寫采訪稿,一些年輕人圍坐在樓下和瓦尼埃交流。我能聽見他有力的聲音和偶爾的沉默,但更多的是笑聲。最終,瓦尼埃獨自穿過庭院,向自己的小房間走去。看著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我想起16世紀神秘學家、西班牙詩壇巨擘十字若望的一句話:“在生命的盡頭,你將被愛檢驗。”
[譯自英國《智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