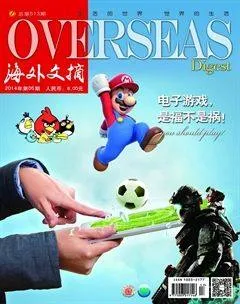正念革命



正念減壓療法
攥在手心的葡萄干變得越來越黏。它們看上去并不誘人,但在老師的指示下,我還是拿起了一顆,開始打量它。我發現它的表面在發光,再湊近些,還能看見從藤上摘下時留下的小印痕。接著,我把這皺皺的小東西放進了嘴里,用舌頭來回感覺它的紋理。過了一會兒,我咬開了它,開始慢慢地咀嚼。
這是我第一次如此專注地吃一顆葡萄干。整個過程也許看上去很傻,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專注是幸福和健康的秘訣。我參加的課程叫做“正念減壓療法(MBSR)”,這一療法是科學家喬·卡巴金1979年提出的。目前,在全世界30多個國家,已經有近千名治療師教授正念修習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冥想。
吃葡萄干這件事讓我們開始意識到,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專注于一件事已經變得這么難。現代科技讓我們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地分散:邊看孩子踢球邊接同事電話,看電視的時候把賬單付了,堵在路上也不忘打電話給商店訂貨。在這樣一個人人看上去都忙忙碌碌、分身乏術的時代,智能設備能讓我們不用東奔西跑就可以處理許多事情,可代價是我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里。
正念療法告訴我們,這種局面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念療法旨在幫助忙碌的上班族放松身心,專注于當下,不要為過往與未來煩憂。許多認知行為治療師將這種療法推薦給病人,幫助他們治療焦慮和抑郁。更廣義地說,正念療法被視為一種減壓的方法。
但如果簡單地將它視為一種時尚的減壓方式又不足以顯示它巨大的潛力,如今正有越來越多的公眾人物認可這一方法,其中包括硅谷科技精英、世界500強企業巨頭、西方眾多政治家等等。正念療法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適性。冥想不僅僅是我們獲得內心平靜的重要方法,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能專注于眼前的事情:專心地工作,專心地教育孩子,專心地學習,專心地健身,甚至是專心地吃東西。銀行業巨頭摩根大通還建議它的客戶專心地消費。
重塑大腦
嘴里的葡萄干快吃完了,我抬頭看了看班里的其他同學。我們每周一晚上上課,連續上八周。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我們花350美元來這里學習怎樣冥想,怎樣集中意念。一位20多歲的金發姑娘覺得每天一個接著一個的工作和會議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找不到任何時間來休整自己,醫生給她開了抗焦慮的藥物。一位正在休產假的新媽媽說,她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應該是和她的寶寶在一起,可是她就是靜不下心來。還有一位社區義工,他的工作是幫助別人的生活回到正軌,可是他自己卻對此倍感壓力。
而我也有自己的煩惱。我的孩子剛剛學步,我覺得我的家庭生活越來越忙亂。和許多人一樣,我每天要處理一大堆信息和工作。我有一部私人用的iPhone和一部工作用的黑莓,辦公室里有一臺筆記本電腦,家里還有一臺iPad,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得盯著屏幕。
逼自己不去與外界聯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的老師名叫博萊特·格拉芙,是一個瘦小的女人。每次開始上課時,她都會敲一下銅鈸,示意我們開始冥想。在這令人沮喪的40分鐘里,我努力按照老師說的那樣注意調整呼吸的速率,可我還是會不停地想到家里的事,聽到屋子里時不時的聲響,我甚至還得想怎樣把上課的內容寫進這篇文章里。
有一天晚上,老師讓我們行禪。我們在小小的教室里,排成一個圈,繞著圈走。“腳跟先著地,然后腳掌著地”,博萊特在一旁提醒著,“先抬一只腳,然后再抬另一只。”盡管我已經關了手機并把它扔在了一邊,可腦子里還是不停地想著下個禮拜的工作和郵箱里那些等著我回復的郵件。老師說這種不由自主的分心是正常的,沒有必要苛責自己。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能意識到注意力的分散,這才是集中意念的關鍵。
正念(Mindfulness)的概念其實來自于東方哲學,尤其是在佛教中。但以下的兩點原因使它從中分離了出來,推動它成為主流的實用哲學。
第一點是巧妙的推廣策略。卡巴金和其他理論支持者在傳播正念的時候,將注意力比作一塊肌肉,和其他的肌肉一樣,可以通過練習得到鍛煉。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當代科學研究表明,大腦具有適應和重組感覺的能力。這一現象被稱為神經可塑性。研究指出,大腦的鍛煉是切實有益的。
正是由于科學研究的支持,正念療法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產業。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2007年,美國人在正念療法相關的課程及藥物中投入了40億美元,其中就包括我參加的這一課程。關于正念的雜志、書籍和手機應用程序已經相繼推出。
通用磨坊食品公司的前總裁賈尼斯·馬爾圖阿諾是一個“正念達人”。06年她便將正念的概念引進公司,并在每棟辦公大樓中都設有冥想室。2011年,她離開了通用磨坊,開始經營一家名叫正念領導力的公司。2013年,她在達沃斯開設了一門正念療法訓練課程,參加的人數眾多。同年,她還寫了一本關于正念領導的書。她在書中提到,她所遇到的領導者們總是長時間的工作,一刻都不得閑。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時間細分主次或是對未來有所規劃。
研究發現,多任務處理會降低整體的效率。不停地在多任務間轉換會使人們降低對無關信息的處理篩選能力,提高錯誤率。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美國成年人在周末還要查收工作郵件,而10個人中有4個人甚至在休假期間都得這樣。只要你帶著手機,你的老板或者是雇員就不會放過你。正如馬爾圖阿諾所說:“科技的發展使得事情超出了我們能控制的范圍。”
硅谷已經成為了正念課程和會議的大本營。“智慧2.0”是科技領導者一年一度的正念交流會,2009年開辦時共有325名參與者,組織者預計今年將有超過2000名參與者。在這里你不僅能聽到卡巴金的發言,還能聽到來自推特、圖片共享應用和臉譜網等流行網站管理者的演講。
這其實并不難理解。寫程序的工程師們常常強調“進入狀態”,這就是正念治療師們所說的感知當下和集中注意力。不過,絕大多數的頂尖工程師們在冥想過后還是要繼續研發分散人們注意力的軟件和小玩意。
最近,iTunes上出現了上千個關于冥想與正念的應用程序,“頂部空間”(Headspace)就是其中一個。該應用程序為用戶提供一系列的網絡視頻,介紹正念練習和冥想的方法。它的開發者安迪·普迪科姆說:“只要我們正確地使用智能手機,它就不會為我們帶來任何傷害。”
正念革命發展史
我見到卡巴金是在一個正念交流會上,他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他身穿燈芯絨的褲子、休閑襯衫和一件鮮艷的運動上衣,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藝術家而不是靈性導師。
1979年,卡巴金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偶然參加了一次冥想講座。“我被深深地打動了,從那天起我開始冥想。我冥想的次數越多,就越覺得我的生活里除了科學應該還有些什么,比如說,怎樣生活。”
1979年,在一次冥想中,他突然萌發了一個想法:是不是能用佛教中的冥想來幫助病人緩解一些疼痛呢?就算癥狀得不到緩解,卡巴金認為正念的練習或許能幫助他們改變對疼痛的認識,從而減輕病痛帶來的生理與心理上的折磨。
于是,卡巴金與三位醫生一起在麻省大學開了一家以冥想、正念療法為主的減壓診所。治療效果幾乎算得上是立竿見影。一些病人說他們的疼痛消失了。而另一些病人說,盡管還是疼,可是正念練習幫助他們更好地面對生病所帶來的生活壓力。“這正是人們所期待的”,卡巴金說,“或許不奢求病能痊愈,但希望能找到一種方式讓生活品質不受影響。”
卡巴金的這一項目最終被麻省大學醫學院接收,發展成為正念減壓療法課程(如今全美已有上千名治療師在教授這一課程)。在隨后的幾年里,科學家們發現冥想和正念練習能降低皮質醇水平和血壓,增強免疫力,甚至能影響大腦的結構。科學研究無疑為正念減壓療法及其他冥想相關課程的快速發展打了一針強心劑。
聆聽生活
我參加的正念課程共有21個課時,除此之外還有家庭作業。有一個禮拜我們的作業是專心吃一樣零食,另一項作業是在地鐵上數同車廂的乘客數量。班上一個同學說,當他不再聽音樂和玩手機的時候,他的正念得到了突破。他開始觀察周圍的人,這讓他在到達辦公室之后能更快地專心投入工作。
八周的課程結束后,我們在一個周六進行了最后一次練習。在冥想和瑜伽后,我們安靜地吃了自備午餐。午餐后,博萊特帶著我們來到公園,讓我們開始四處走走,這在冥想練習中被稱為“漫游”。沒有手機也不許交談,只是享受當下。
朝遠處的草坪望去,我很容易就能認出我那些正在冥想的同學們,他們像僵尸般從扎堆在草地上野餐、燒烤、閑聊的人群中穿過。我看見一群20多歲的小伙子在玩飛盤,小孩們在騎自行車,女人們在曬太陽。
我就住在這公園附近,三年中我來過這兒無數次,可是這一次我聽見了不同的聲音。草地上有人在打排球,我聽見了球掉在草地上的聲音,我聽見了傳球時球與手臂碰撞的聲音,我還聽見了球員在交流時的咕噥聲。接著,身后傳來輕輕的叮當聲,原來是一只脖子上掛了金屬狗牌的小狗,叮鈴,叮鈴。
我們就這樣四處晃悠了半小時。回到教室后,我們討論了如何在課程結束后繼續正念練習,隨后我們把椅子折疊起來收進柜子里,輕輕地離開教室,各自回家。
在課程結束后的幾個月里,我并沒有經常冥想,但正念療法對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開始佩戴手表,這使我每天看手機、上網、查收郵件的時間減少了一半。吃飯時,如果我的同伴去了洗手間或是接電話,我不再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看新聞、刷微博,而是靜靜地坐著,觀察著身邊的人。出門在外時,我發現我開始不由自主地聞一聞空氣中的味道,聆聽這個城市忙碌的聲音。它們其實一直都在,只是當我開始學會感覺它們時,它們顯得愈發重要、精彩。
[譯自美國《時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