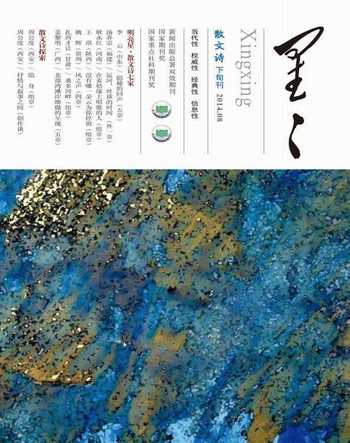抒情與敘事之間(創(chuàng)作談)
周公度
我把散文詩在中國的歷史上溯到漢賦時期。看世界各國文學史,再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學分類像中國,在那么久遠的年代,遙遠的西周時期,就對文學的各個門類做了細分。那是康德所盛譽的東方哲學中的理性主義的魅力所致。相對于古典文化,我們今日的所有體裁毫無新意。包括現(xiàn)代詩。五言、七言、宋詞的發(fā)展,在《詩經(jīng)》面前,都是現(xiàn)代詩,先鋒詩,它們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不停地解除束縛的過程。只是他們的努力,尤其是五代以及兩宋的詩人,令人遺憾地將詩意愈加表面化了。
漢賦的出現(xiàn)與影響也是如此。它的出現(xiàn)之初,冀圖達到規(guī)范的短詩所不能形成的磅礴氣息、綿密結(jié)構(gòu)、審慎的邏輯等等美學目的。它們在形成與流行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批經(jīng)典,但同時也進入了一種程式化的弊端。再也沒有一種文體比有了固定框架更令人傷心的了。最后,它成為了一個詩人表達能力微弱、解決問題遲緩的一種側(cè)證。因為優(yōu)秀的詩人總是能在最短的篇幅之內(nèi)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的復雜內(nèi)心。而漢賦徒具形式的博雜。隋末以后,這種文體逐漸淪為心慕古典的三流文人扮演詩人的重要工具。
散文詩在近代以來的歐美文學中,遠比在中國更為成熟。像梅特林克的散文與劇作、葉芝的隨筆、尤金·奧尼爾的戲劇,都是具有廣泛詩意的敘事文本。更不要說清新蘊藉的泰戈爾與廣博敏銳的紀德的杰出抒情作品。他們都是詩歌這一題材的偉大拓展者,努力在敘事與抒情之間找到最佳的契入點。他們延伸了心的外在領(lǐng)域,迫使原初之時像種子一樣集中的詩,現(xiàn)在成為清泉、湖泊、汪洋、炸藥、夢魘、碧空、草原、戈壁,與繁星萬點的宇宙。
而且,他們的努力歷歷在目。每一個詩人都比前一代詩人更為自由、博雜。如紀德之于米斯特拉爾,如圣·瓊·佩斯之于希梅內(nèi)斯,帕斯之于索爾仁尼琴。但他們之間并沒有高貴內(nèi)心的高下之分,相反他們擁有的一個一致的目標,在細微的愛與天賦的自由之間找到分野,消弭隔閡。散文詩最大的魅力即在此間。它對詩意場景的重視,對心的誠懇再現(xiàn),對文本整體的充沛需求,都在對文體界限的逐一打破中得以體現(xiàn)。它打破的愈多,愈有表現(xiàn)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