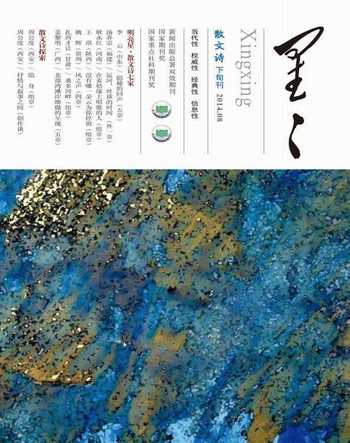桑多河畔(組章)
扎西才讓,藏族,1992年開始詩歌寫作。已在《十月》《民族文學》《詩刊》《星星》《詩選刊》《芳草》《飛天》等國內報刊雜志上發表文學作品近五十萬字。曾獲“詩神杯”全國詩歌獎、甘肅省第四屆敦煌文藝獎、《飛天》十年文學獎、《西藏文學》年度作品獎。作品入選多部詩歌年選和總結性詩集。已出版詩集兩部。
桑多鎮
先人說:“停下來吧,就在這桑多河邊,建起桑多鎮。
“讓遠道而來的回族商人,帶來粗茶、布料和鹽巴。
“讓那在草地械斗中喪身的扎西的靈魂,也住進被詛咒者達娃的家里。
“不走了,你們要與你們的卓瑪,生下美姑娘雷梅苔絲,養牛養羊,在混亂中繁殖,在計劃中生育。”
直到皮業公司出現,直到草原被風沙蠶食。
羊皮紙上的一百年,只待被史官重新書寫,在那情欲彌漫的書桌上,在那熱血沸騰的黑夜里。
桑多河:四季
桑多鎮的南邊,是桑多河……
在春天,桑多河安靜地舔食著河岸,我們安靜地舔舐著自己的嘴唇,是群試圖求偶的豹子。
在秋天,桑多河摧枯拉朽,暴怒地卷走一切,我們在憤怒中捶打自己的老婆和兒女,像極了歷代的暴君。
冬天到了,桑多河冷冰冰的,停止了思考,我們也冷冰冰的,面對身邊的世界,充滿敵意。
只有在夏天,我們跟桑多河一樣喧嘩,熱情,渾身充滿力量。
也只有在夏天,我們才不愿離開熱氣騰騰的桑多鎮,在這里逗留,喟嘆,男歡女愛,埋葬易逝的青春。
嘆息也如落葉歸根
牛車木桶,馭者在晨光中一聲不吭。
只河水嘩嘩,離開大霧彌漫的小鎮。
桑多河這邊有人嘆息,這嘆息也如落葉歸根。
秋已經很深了,但還是無法稀釋掉兩岸的風聲。
桑多河畔:想象
頭發,是灌木叢,是密林,是一地青稞正待成熟。
人,是沙漠,是海洋,是黃色土地使萬物生長。
好多年后我才認識到這些事實。
好多年后,我才把這種事實寫出來。
我在桑多河畔生活了多年,現在還住在這里,看到鶯飛草長,金菊怒放,聽說雪蓋牧場,牛羊病去。
我觸摸著大地上紫色的草穗,沉睡在自己的故鄉,有時想象自己就是一只鷹,漂浮在云朵做成的鄉村。
有時想象自己就是一條魚,游曳在河底的牧場。
但想象無法改變我的現實,我只好左手托住腮幫,右手按住心臟,坐成一尊無言的雕像。
高原月
高原之月從山上下來,跟著插箭的男子和沐浴的女人,來到小鎮北邊寺院的金頂。
高原之月映照著黃錦內的經書,撫摸著繪有吉祥八寶的鍍金的門楣,在深夜的街頭,迎來了晚歸的沮喪的書記官。
就這樣過去了多少年。多少年來,春花燦然綻放,秋果熟了自枝頭落下。
就這樣過去了多少年。多少年來,塵埃悄然落定,混沌寂然有序,那個晚課后得道的長發高僧,在天幕下頓悟了人世間的生死。
鄉親們
桑多河畔,神靈和鄉親們住在一起,享受著人間煙火。
他們的祖先也在餐桌旁,聽他們談論國家大事。
太子山上的花開了又敗了,它們體內的力量越來越弱。
他們體內的力量,也被什么給抽走了。
不過,他們還在努力活著,出門打傘,上路坐車,在佛堂里,把桑煙煨起,把長明燈點燃。
更多的時候,他們頭頂驕陽匯入人流,讓心境平靜下來。或者登高望遠,看瓦藍天空下的雪山,在遠處冷處,沉默著。
或許只有雪山知道,在人世上活著,是件多么寂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