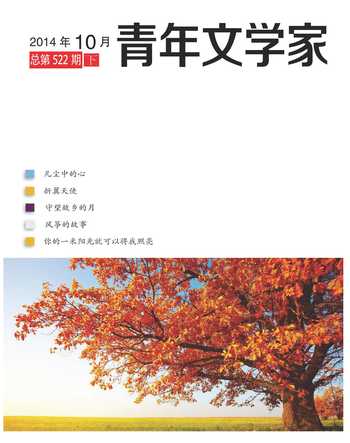蘇軾詠物詞之修辭技巧論析
摘 要:修辭技巧是我們?cè)谘芯吭?shī)詞作品的時(shí)候不可略過(guò)的一步,這對(duì)深層次的理解詩(shī)詞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幫助。因此,筆者通過(guò)對(duì)蘇軾各類作品的分析,總結(jié)出其詠物詞的修辭技巧特點(diǎn),希望能對(duì)探究蘇軾詞作有所幫助。
關(guān)鍵詞:蘇軾;詠物詞;修辭技巧
作者簡(jiǎn)介:嵇傲萍(1989.11-),女 ,漢,江蘇常熟人,12級(jí)碩士研究生,揚(yáng)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12級(jí)語(yǔ)文課程與教學(xué)論。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4)-30-0-02
宋代詠物詞的創(chuàng)作蔚然成風(fēng)。《全宋詞》收錄詠物詞2000余首,約占其十分之一,宋代有詠物詞傳世者達(dá)400余人,詞家或物感興懷;或逞才唱和;或依物言情。而在眾多詞家中,蘇軾之成就、地位上也鮮有能比者,據(jù)孔凡禮《三蘇年譜》在薛瑞生等人著作的基礎(chǔ)上,考察《全宋詞》、《全宋詞補(bǔ)輯》,蘇軾現(xiàn)存詞320多首,其中詠物詞50余首,北宋詞人中為最多。
修辭技巧是我們?cè)谘芯吭?shī)詞作品的時(shí)候不可略過(guò)的一步,這對(duì)深層次的理解詩(shī)詞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幫助。因此,筆者通過(guò)對(duì)蘇軾各類作品的分析,總結(jié)出其詠物詞的修辭技巧特點(diǎn),希望能對(duì)探究蘇軾詞作有所幫助。
(一)“比興”之深情物語(yǔ)
比興手法自屈原《橘頌》以來(lái),魏晉以后有進(jìn)一步完善。“原夫興之為用,觸物以起情,節(jié)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異者,亦有事異而情同者,循省六詩(shī),可榷舉也。”這里雖然是在解釋“興”,其意義實(shí)際包含著“比”。因?yàn)椤芭d”中不妨有“比”,觀其屢用“喻”、“譬”可知。詞中的比興,聯(lián)類無(wú)窮,涵義愈廣,便愈耐玩索。“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fā)之。而發(fā)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fù)纏綿,終不許一語(yǔ)道破,匪獨(dú)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宋代詠物詞,大都是“意在筆先”,卻又貌似無(wú)寄托,其原因正在于“神余言外”。在詠物詞中,傳統(tǒng)借物抒情的方法來(lái)源于詠物詩(shī),將詩(shī)人自己的感情、胸懷抱投入其中,寄托更深的人生感悟,是從蘇軾開始。
將詩(shī)人自己的感情以及胸懷寄托在事物之上,讓事物具有詩(shī)人的情感,以至于事物與詩(shī)人合二為一。司馬遷曾如此評(píng)價(jià)屈原的作品:“《離騷》者,猶離憂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yuǎn)。”北宋以前,詞少有寄托,直至晏幾道,其詞始合寄托。黃山谷《小山詞序》云:“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dú)嬉弄于樂(lè)府之余,而寓以詩(shī)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dòng)搖人心。”烏臺(tái)詩(shī)案后,蘇軾大半生窮困潦倒、顛沛流離,自身的感悟也愈發(fā)深刻,從他的詠物詞中可見一斑。
正如東坡在《荷花媚·荷花》以作中,寫荷的“天然地,別是風(fēng)流標(biāo)格”。于是作者有所“悵望”,希冀能夠“清香深處住”,人與荷精神相通,契合無(wú)間。這就不是一般的寫情狀物詞可以等同的了。
(二)“象征”之心聲暗表
象征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shù)手法方式,在我國(guó)古典詩(shī)歌中早已存在并被廣泛運(yùn)用,從《詩(shī)經(jīng)》中的《碩鼠》到《離騷》中香草、美人,構(gòu)成了一個(gè)龐大復(fù)雜的比喻系統(tǒng),這讓詩(shī)歌的形象更加鮮活。而到了東坡的詠物詞中,更是大放異彩。
蘇軾的詠雁詞通過(guò)象征手法,將他自己無(wú)所依托、飄零身世的痛苦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調(diào)笑令·歸雁》、《水龍吟·詠雁》,都是他流放江淮時(shí)期所作的篇目,這些作品的基調(diào)大多相似。前者“將飛卻下盤桓”,后者“徘徊欲下,依前被﹑風(fēng)驚起”。所表達(dá)的孤苦無(wú)依、漂泊孤苦的凄涼讓人印象深刻。張炎的《解連環(huán)·孤雁》也寫到“自顧影、欲下寒塘”,采用的是蘇軾的意。但有所差別的是,張炎是南宋遺民,抒發(fā)的是國(guó)家滅亡的痛苦,但蘇軾的詞作感慨的是自身個(gè)人際遇、身世飄零。
在東陂采用象征手法的這一類詠物詞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算是《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此詞作于東坡寓居黃州時(shí)期。開頭兩句寫夜景,月掛疏桐,夜闌人靜,空闊冷清。第三句寫“幽人”,下闋單寫孤鴻。孤鴻被勁回首,徘徊不止,揀盡寒枝都看不見可以停留休息之處,孤獨(dú)寂寞的場(chǎng)面可想而知。雖然詞面上單寫孤鴻,看似與“幽人”沒(méi)有關(guān)系,但實(shí)際上鴻即是人,人即是鴻,兩種形象互相融合,讓人自然而然想到“不知蝴蝶之為莊周,莊周之為蝴蝶”的藝術(shù)境界。孤鴻的孤寂, 寫出了蘇軾被貶后無(wú)處依靠又無(wú)處訴說(shuō)的落寞、悲苦之情。謝章鋌:“詠物詞雖不作可也。別有寄托,如東坡之詠雁。……斯最善也。”此處的“寄托”又為何物呢?蘇軾于神宗元豐二年(1079)七月因詩(shī)文得罪入獄。事發(fā)突然,心情慘淡但又無(wú)處訴說(shuō)。是年底遇赦,謫貶黃州,在黃州度過(guò)長(zhǎng)達(dá)五年的幽居般的生活,甚至產(chǎn)生投江自殺的念頭。東坡在黃州時(shí)那些郁結(jié)于心,又不得不吐之情,遂只能婉曲地寓于詞中。
(三)“擬人”之物我置換
擬人手法由來(lái)已久,旨在將物人化。這種手法為眾多大家靈活運(yùn)用。而在蘇軾詞作中,擬人手法的運(yùn)用更是隨處可見,且蘇軾的擬人不是部分?jǐn)M人,而是通篇擬人。
王國(guó)維曾評(píng)價(jià)說(shuō):“東坡《水龍吟》詠楊花,和韻而似原唱。章質(zhì)夫詞,原唱而似和韻。”詞人抓住所詠之物的特征,巧妙的人格化。將楊花比擬成一位春日思婦,寫離別的閨怨,生動(dòng)形象。歷來(lái)推崇備至。詞的上闋把楊花飄零漫天飄舞的情形,想像成思婦滿腔的離別愁苦,她在將要昏昏欲睡之時(shí),嬌媚的雙眼流露出 “欲開還閉”的倦容。因?yàn)樗龑?duì)情郎的思念之情太過(guò)于濃烈,竟然在夢(mèng)里隨風(fēng)萬(wàn)里去追隨情郎,但沒(méi)想到好夢(mèng)被鶯的啼叫聲驚醒。“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wú)情有思。”賦予柳絮以人的性情。明明是葬春楊花離枝,卻說(shuō)成“拋家傍路”。楊花飄忽無(wú)著,“拋家”而去,不是很無(wú)情嗎?可是柳絮“傍路”飄零,卻又依依難舍,戀“家”之情躍然紙上。真是“道是無(wú)情卻有情”!“有思”言其不忍離別的愁思和痛苦。“思量”是“惜”的進(jìn)一步的深入,使楊花飄忽不定的形態(tài)具有了人的情感。“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以極其細(xì)膩獨(dú)到的筆致,盡寫柳絮飄忽迷離的神態(tài),讓人柔腸百轉(zhuǎn),思緒萬(wàn)千,嘆為觀止。縱觀上闋是以人狀物,雖然是在詠柳絮,卻叫人難分詩(shī)人是在寫柳絮還是寫思婦。柳絮與思婦達(dá)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貌似神合的境界。
再如蘇軾的詞作《賀新郎·詠石榴》中用“美女出浴圖”,寄托了東坡不與不與群小浮沉的高尚情操。《洞仙歌》借柳喻人,寫垂柳的清高、英雋、雅潔、秀麗進(jìn)而刻畫了佳人的品格美。
蘇軾的詠物詞除了《浣溪沙·詠橘》以及《菩薩蠻·詠?zhàn)恪穯渭儾捎觅x體不用寄托比興的手法之外,其他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先言他物,再言所詠之物”,用“比興”來(lái)抒發(fā)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感悟。同時(shí),在創(chuàng)作詠物詞的時(shí)候,蘇軾常常不自覺(jué)地將自身的情感體驗(yàn)投射到所詠的事物身上,所以在蘇軾一部分的詠物詞中,“物”具有非常濃烈的象征意味。至于擬人手法的運(yùn)用在蘇詞中更是隨處可見。這使得蘇軾的詞作在宋詞中,既是獨(dú)創(chuàng)又成為范式,引起后來(lái)詞人的學(xué)習(xí)與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