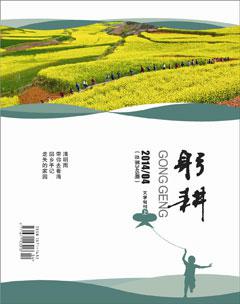走失的家園
劉文波
有人說(shuō),故鄉(xiāng)是屬于游子,屬于遠(yuǎn)行人的。身在家鄉(xiāng)的人沒(méi)有故鄉(xiāng)。對(duì)于遠(yuǎn)走他鄉(xiāng)的人來(lái)說(shuō),故鄉(xiāng)如同與生俱來(lái)的胎記洗刷不掉,痛徹肺腑。一個(gè)沒(méi)有故鄉(xiāng)的人是孤獨(dú)的,身老家鄉(xiāng)的人是幸福的。而今,這些已都與我無(wú)關(guān)。故鄉(xiāng)只是曾經(jīng)的記憶,是履歷表上的一個(gè)漸行漸遠(yuǎn)的符號(hào),一個(gè)曾經(jīng)的標(biāo)記,一個(gè)只能懷想,不能到達(dá)的傷心之所。
這種感覺(jué)從賣(mài)掉老家的老屋以后愈發(fā)濃重。小時(shí)候,讀魯迅的《故鄉(xiāng)》,很難體會(huì)魯迅先生的悲涼壓抑的感受。文章開(kāi)篇寫(xiě)道:“在蒼黃的天底下,遠(yuǎn)近橫著幾個(gè)蕭索的荒村,在漸近故鄉(xiāng)時(shí),天氣又蕭瑟了。”那時(shí)是無(wú)從體會(huì)先生悲從中來(lái)的寒涼。只覺(jué)得,遠(yuǎn)方有一個(gè)更加溫馨的家,一樣是美妙的。而體會(huì)不出那種將自己從生長(zhǎng)養(yǎng)育的土地上如莊稼一般生生拔離而去的刻骨的荒涼痛疼。
老屋簡(jiǎn)陋,那也是養(yǎng)育了自己的幼年、童年少年的襁褓。這種初物戀是每個(gè)生命都有的心靈感應(yīng)。小時(shí)候,農(nóng)田里種煙草、西瓜,要先在暖炕上育秧苗。移栽時(shí),再旺盛的苗子,如果不帶一點(diǎn)原來(lái)畦子里的土壤,也是不肯栽活的。因此,挪栽時(shí)都要帶一些原來(lái)的土壤,方肯成活。其實(shí),這何嘗不與人跟家園故土的關(guān)系一樣呢?動(dòng)物中的大象、狐貍、駱駝等,也都是重情之物。對(duì)其出生地有著難以割舍的感情。大象駱駝死亡時(shí)要拼卻生命回到它的出生地;狡猾的狐貍,也有“狐死首丘”的動(dòng)人之處。而人又何嘗不一樣呢?異國(guó)他鄉(xiāng)的水土雖是養(yǎng)人的,誕生要經(jīng)歷了水土不服的斷乳期。因此,把異鄉(xiāng)當(dāng)家鄉(xiāng)的人,大多是和著淚水入夢(mèng)的。
在一個(gè)地方呆久了,和周?chē)娘L(fēng)物熟悉了,如同物化為其中的一部分。一棵樹(shù)長(zhǎng)在田間地頭,吸風(fēng)飲露,長(zhǎng)成一棵巨樹(shù),而有朝一日,訇然伐倒,一下子消失了,人的目光在瀏覽此處時(shí),仿佛被閃了一下,有一種失落的空曠,不習(xí)慣不適應(yīng),總覺(jué)得少了些什么。而一處老屋,十幾年,幾十年的時(shí)光浸染,耳鬢廝磨,每一塊磚,每一片瓦,每一棵樹(shù)一棵草,墻壁上的水漬,屋角的裂痕,都已成為記憶的一部分。每一片瓦都安放著自己的一片目光,每一枝草葉都掛著一串生動(dòng)的笑語(yǔ),每一絲墻壁屋角都寄居著一個(gè)安謐的靈魂。怎么能不思念,怎么能不動(dòng)情?當(dāng)你離開(kāi)之后,雖沒(méi)有肢體分離的切膚之痛,但靈魂無(wú)處安放,身體是要飽食流離顛沛之苦的,身心因此不安分。
一個(gè)曾經(jīng)生長(zhǎng)自己過(guò)往生活的地方荒草叢生,或是被另一種生活,另一些人所代替,他的心會(huì)失血,枯槁的。老屋賣(mài)后,我的心就蔓草叢生,心無(wú)所依。
記憶中留駐了兩處老屋的影像:一處盛放了自己的童年,一處盛放了自己的少年。新一些的老屋建在舊一些的老屋之上,如同童年之后是少年。老屋的地基堅(jiān)實(shí),如同自己的身體健壯。如果說(shuō),我看到了老屋的誕生,長(zhǎng)大,不如說(shuō)是老屋看著我的誕生長(zhǎng)大。在我還不能獨(dú)沐風(fēng)雨,獨(dú)自闖蕩江湖的時(shí)候,老屋如襁褓般對(duì)我呵護(hù)有加,守護(hù)著我的每一個(gè)鳥(niǎo)聲如洗的清晨和艾草清涼的夜晚。而當(dāng)我能掙脫她的懷抱,經(jīng)不起遠(yuǎn)方的誘惑,我把她的看護(hù)看作束縛禁錮。逃離的愿望一天比一天膨脹。他鄉(xiāng)山奇水秀,他鄉(xiāng)人美物異。不安的心早已遠(yuǎn)離了故鄉(xiāng)。然而,他鄉(xiāng)的燈火溫暖不了疲憊的身心,他鄉(xiāng)的屋檐容不下抖索的身子。游子都想家了。
在我遠(yuǎn)離家鄉(xiāng),謀生異地的日子里,老屋成了我惟一的牽掛,因?yàn)槟鞘歉改赣米约旱难箟酒龅臏嘏募摇8赣H離我而去,母親也遠(yuǎn)嫁他鄉(xiāng),守著飄零的后半生。家成了孤獨(dú)的空巢。憑風(fēng)雨侵襲,荒草占領(lǐng)。日漸枯朽的門(mén)楣窗框,苦苦支撐著,讓我每一次來(lái)臨都淚雨滂沱。我不知道,它會(huì)不會(huì)先我在一個(gè)雨夜倒下去。沒(méi)人守望的,家也會(huì)老的,而在我遠(yuǎn)離它的歲月里,它已老態(tài)龍鐘,讓我觸目驚心。我一直堅(jiān)守著一個(gè)觀念,老屋在,自己的根就沒(méi)有斷,老屋是自己的影子,哪怕成了一對(duì)瓦礫。而想到它真的廢墟一般呈現(xiàn)在我的眼前,我不知能不能承擔(dān)得動(dòng)一塊磚瓦的重量。于是,在一個(gè)春意尚未萌動(dòng)的早春,老屋被賣(mài)給了本村的一個(gè)遠(yuǎn)方叔。
老屋終于賣(mài)了,老屋你可要挺住啊,我的心里放下了一塊石頭,卻放上了一座山。自從將房屋有關(guān)的房契易手之后,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踏進(jìn)這個(gè)院落一步。即使再次進(jìn)入,也只能作為一個(gè)外來(lái)人,一個(gè)匆匆過(guò)客。至此,老屋里承載的我的那些年華歲月,一起流失,消散。我已與它無(wú)關(guān)。
老家的人事如秋風(fēng)中的落葉,日漸凋零,熟悉的面孔愈來(lái)愈少,陌生的面容愈來(lái)愈多。原先,在村里,每一條小巷,每一棵老樹(shù),都是一段記憶。而今,走進(jìn)村子,一道走不通的死胡同,讓我如同外來(lái)者一般尷尬無(wú)比。我已成為一個(gè)外鄉(xiāng)人。我們形同陌路,兩不相干。新一茬長(zhǎng)起的孩子都會(huì)帶著異樣的眼光看我。老家沒(méi)有我容身的一榻、一枕、一碗、一席。沒(méi)有屬于我的一磚、一瓦、一草、一葉。沒(méi)有了老屋,我越來(lái)越缺少一個(gè)冠冕堂皇、光明正大的回鄉(xiāng)的理由。我的來(lái)臨會(huì)被曾經(jīng)的鄰舍好奇,遠(yuǎn)近的族親叔伯會(huì)將我如同遠(yuǎn)客一般邀到客廳,端茶上飯。這只能讓我感到隔離。
姐出嫁的村子反而成了我惟一能安心落腳的地方。我去姐家的次數(shù)越來(lái)越比回老家的次數(shù)多。雖然兩個(gè)村子相距很近,就在目力所及之內(nèi),土地毗鄰,隔河相望,但那個(gè)越來(lái)越只能成為遙望的地方距離我越來(lái)越遠(yuǎn),多情的炊煙不再為我飄起,肥沃的土地再也長(zhǎng)不出屬于我的莊稼。我向著家鄉(xiāng)抬起腳的力量漸漸枯竭。
有時(shí),我想從姐家趁著夜色掩護(hù),潛入那片曾經(jīng)熟悉的熱土,到在自己的老屋邊望一下,哪怕只是短暫的停駐,哪怕只是用手輕撫一下熟悉的院墻,籬笆,看一眼那棵依舊能喊出我乳名的父親親手栽下的白楊樹(shù)。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停留在我的想象中,無(wú)法付諸行動(dòng),我感到它的距離比任何一個(g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都要遙遠(yuǎn),只能遙望,不能抵達(dá)。我怕自己的失態(tài)會(huì)讓人窺出端倪,自己的多情會(huì)被人視為做作。我怕那棵老樹(shù)會(huì)喧嘩得天地痛哭,引得屋宇悲戚,讓我潰不成軍。
古希臘哲學(xué)家埃斯庫(kù)拉斯說(shuō)過(guò),人不能兩次踏進(jìn)同一條河。我也不能兩次擁有同一個(gè)故鄉(xiāng)。我是一個(gè)先遺棄了故鄉(xiāng),又被故鄉(xiāng)遺棄的人。
失去故鄉(xiāng)的我已一無(wú)所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