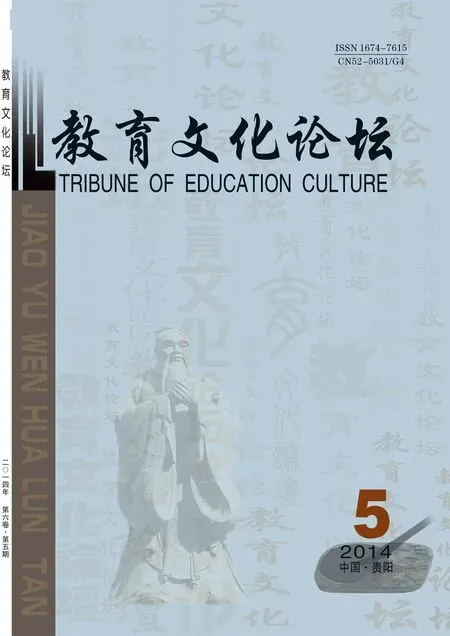沙灘黎氏與地域文化
黎 洌
(1.遵義師范學院 學科辦,貴州 遵義 563002;2.遵義師范學院 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貴州 遵義 563002)
“沙灘文化主體是黎氏家族,……黎氏家族沾溉及于鄭氏、莫氏兩家以及鄰里戚友。鄭珍和莫友芝接受黎氏家學且有所拓展,鄭莫二氏之學也是沙灘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1]黃萬機《沙灘文化志》對黎氏與沙灘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作了高度評價。任何一個文化現象都是在時間和空間交錯中呈現出它的特征,沙灘文化同樣,作為一種具有很強地域特色的家族文化,它與特定的時空密不可分。
一、沙灘文化形成前的地域文化時空特征
在漢文化圈,貴州可謂開發較晚,至明代始成為十三行省之一,朝廷控制范圍,多集中在由衛、所構成的交通沿線,甚至連布政使司也與土司宣慰府同城而設。少數民族環伺的社會環境和崇山峻嶺的自然環境,使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傳播較為遲緩,正如莫友芝在《黔詩紀略》卷一按語所言:“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至漢唐郡縣,幾不可尋。莫流鮮聞,安問風雅。”[2]
沙灘文化的發源地,今屬黔北,清雍正前屬四川,亦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但開發較早,秦定黔中郡,改鄨國為鄨縣。漢武帝開發西南夷,設犍為郡和牂柯郡,犍為郡的郡治即在鄨,但實施 “郡國并存”政策,即流官與土官并治。同時開辟五尺道,徙豪民屯田,漢文化進入,今天,在務川、仁懷等地發現的漢墓中,就有大量的漢文化元素的遺物出土。但兩晉時期,中原紛亂,黔中淪入大姓之手,漢民夷化,據《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記載,漢文化已廖如晨星。雖今黔北地區多為經制州,但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所見皆為“開山峒、招豪長”所置。這一時期的播州文化,受地理環境、民族習俗、歷史傳統等因素影響,決定了夷僚混雜、尚鬼信巫等特點。楊氏統領播州后,沙灘由于地勢平坦、土壤肥沃而被楊氏土司看中,“沙灘者,宣慰使楊應龍官莊也。”
南宋時,播州楊氏開始仰慕漢文化,從楊軫到楊文數代,大力招賢納士,設置官學,建孔子廟,以取播士請于朝,而每歲貢三人,在短短數十年間,“土俗為之一變”。出現“破荒冉家”,產生了八位進士,涌現了冉琎、冉璞等軍事人才,并產生了楊漢英這一學養深厚、精通漢文化的代表人物,不僅創作了詩文集《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還撰寫了哲學著作《明哲要覽》九十卷。但此時漢文化的流播主要局限于上層,是以“官學”身份出現,土官“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而下層民眾參與學習的機會則非常之少。為此,漢文化對播州文化整體結構影響不大。
明代,貴州的改土歸流引起楊代土司的警惕,兼之長期的內部紛爭,封閉保守成為播州的主流。直至萬歷二十八年平播之役的結束,將播州分置遵義和平越二府,結束了長達725年的土官統治。隨著府、縣等行政建制的設立,大批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流官進入黔北地區,開始了他們以漢化夷的文化管理,開設學館,充任塾師,執教授徒,興辦書院,將楊氏土司點燃的漢學星星之火,推向燎原之勢。天啟元年,黃平、湄潭的生員要求開科入試,表現出當地生員在漢文化教養下的濡化進程。同時,大量漢移民的進入,對播州文化及民風民俗的改變有極大的促動。隨著漢文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確立,“椎結之服,勁悍之性,靡然變易矣”,少數民族強勁野性的文化被溫文爾雅的柔性的漢文化所取代,而過去的“土司之民”也轉而為“朝廷之民”,人們社會文化的認知隨之改變。到雍正五年,將遵義劃入貴州,成為黔之北。
明末的戰亂,遵義相對安穩的環境,使大批文士趨之若騖,南明永歷王朝移駐貴州,更使部分上層官僚和知識分子進入貴州。明亡后,由于“滇黔猶保冠帶之俗,”大批明遺民滯留或遷移貴州,一時間,黔北鄉間文人雅士云集,或隱居明志,或遁入空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最具代表的是錢邦芑和陳啟相。錢邦芑,號大錯,明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南明永歷中,以御史巡按四川。永歷六年(1652),受任撫黔。翌年,張獻忠起義軍余部孫可望率眾進入貴州,他隱退于余慶蒲村。以后便削發為僧,潛心詩文,以授徒為業,從學者甚眾。陳啟相,四川富順縣人,官河南道御史,明末因甲申之變棄官來遵義,隱于平水里掌臺山寺為僧,號大友,設書院講學著書,談亮、羅兆甡等名士皆出其門下。“遵義人才之開,掌山功最鉅。”黎氏家族的黎懷智,明未任黃岡知縣。明亡后薙發為僧,號策眉,“與明遺老大友、大錯輩講味禪悅,藉以韜光。”[2]遵義明末清初由流亡文人形成的人文匯萃的歷史語境,為漢文化在沙灘的傳播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態,也為沙灘文化的形成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二、黎氏家族與沙灘
據《遵義沙灘黎氏家譜》,黎氏原 “家廣安軍渠江之金山里。”后因兄弟爭田水,黎朝幫“令懷仁祖擇鄰,初徙貴州之龍里,”“厥后二十九年而播州楊氏平,地入遵義、平越兩府,分屬川貴。更徙卜遵義治東八十里樂安水上之沙灘居焉。”“始吾祖自蜀遷黔之龍里,己著籍為黔人,居十九年而徙遵義,還入于蜀。”“越百有二十六載,而當我朝雍正五年,世宗皇帝丁未之歲割遵義隸貴州,故又復為黔人也。”[3]
家譜記述了黎氏家族遷入貴州的歷程,還附記了唐、宋時黎氏先祖的宦游情況,說明其家族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如果說家譜中關于先祖的記載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那么,對入黔始祖的記載則是清晰無疑的。始祖“朝邦,明廩膳生,兼力農。”與明初大規模移民不同,黎氏不是作為軍屯或民屯進入貴州,而是主動離開熟悉而又令人傷心的兄弟相爭的環境,選擇陌生的他鄉重起爐灶,入籍貴州。龍里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置龍里衛于龍里長官司”,康熙十一年(1672)始改縣,黎氏入遷時,周邊是平伐、把平長官司等少數民族政權[4]。作為一個讀書人,黎氏入黔始祖朝邦進入貴州前,已有功名在身,漢文化的教養使他渴望回歸于主流文化之中。因此,十多年后播州平定,改土歸流,黎氏家族選擇遷回蜀地,固然有戰爭使少數民族人口十去其九,留下大量無主土地,更有從“夷蠻之地”回歸故里,從少數民族與衛所雜錯的環境中回歸熟悉的巴蜀文化和漢文化環境的念想。雖然雍正五年,黔北并入貴州,黎氏家族再次入籍貴州。但此時的貴州,與當日不同,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區域行政屬性的改變,并未改變文化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家族的文化血脈里,一直就流淌著漢文化的血液。由蜀而黔,由黔而蜀,再由蜀到黔,改變的是地域身份,沒有改變的是對漢文化的依附與堅守。正是由此,一個家族的文化行為,才能帶動一方,最終形成享譽一方的文化景觀。
黎氏定居沙灘后,“其所卜居之業,治家之法,饒有古儒風焉。”[3]將儒家文化用于家庭管理,使文化傳承貫穿于日常生活之中,這就使家族繁衍與漢文化緊密相連,不絕如縷。“黎氏自遷遵義以來,累代耕讀為業。”耕讀傳家,是農耕時代漢文化圈理想的生活模式,在經濟收入較為穩定的環境下,將謀求生存與讀書做人合二為一。同時在科考中獲取功名,“讀書成才”,最終成為書香門第。黎氏家族從始遷沙灘起,就自覺以儒家思想規范自身的行為,即使在“三代不應清朝科舉”的束縛下,仕途無望,仍堅持讀書明理的原則,以儒家思想作為行動的準繩,通過讀書以陶冶情操。其意義在于,在滿清入主中原的歷史背景下,堅持儒家的倫理道德,就是堅守漢文化的傳承,守住漢文化之根,也即是顧炎武所說的“亡天下”與“存天下”。因此,四世黎耀才能以一介農夫做到“躬領家政,事親有道,溫凊定省,率家人以禮法,每遇元旦、慶節、生辰,雞鳴時子婦孫曾即起,拜跪稱觴,無敢惰慢,若遲至曙則有罰。”[3]五世黎天明,“生平忠直自處,仁厚待人。上事先白祖,下友諸弟,庭無閑言。”[3]雖讀書天資不高,仍追求“以詩書垂后”。六世黎國士舉止言談自覺以宋儒為典范。“葬祭必依于禮”。“治家有道,內外必肅。以耕讀、勤儉、孝友垂訓后人”。生活儉樸、不崇奢華,“飲食衣服、一縷一粟、必愛惜。遇喜筵,壽節,歲時,伏臘,毋糜費,毋奢華、閨門之內、秩秩如也”。“率族人以禮法”。子侄輩時群聚笑語,見其至,“輒拱立以俟。既尊長,行亦循循規矩。毋敢箕距喧嘩。”[3]同時刻苦攻讀,“家計艱難,教讀以資衣食,晝則訓誨生徒,夜則然膏課誦。亦時而經營交易,家以織布為業。每負往鄭場出售,挾所抄文藝冊及筆硯以隨,甫出門,即口占一四書題,途次構思,寂無一語,及至場入店,腹稿己成,輒伸紙錄之。或時在店,未及買賣,即取抄冊熟誦,其苦志如此。”[3]弟黎國柄幼讀書悉通章句,尤熟古文辭及三國志。又便弓馬,初欲應武試以圖進取,及兄黎國士考中舉人,“見門戶有庇,乃棄儒業,躬耕自給。產不甚豐,終歲勤動食指而外,家無長物,處之泊如。稼穡之余,親操紡織以供裳服,布素蕭然。”耕是為了生存,使家族能夠繁衍生息;讀是為了傳承文化,陶冶情操。正是不離不棄地對儒家禮儀的自覺遵守和對詩書的不斷追求,使黎氏家族在沉寂數十年后,重新成為簪纓之家,并成就一方文化。
對漢文化的恪守,具體化就是對“忠”、“孝”、“仁”、“義”等儒家道德文化觀念的恪守,二世祖黎懷仁曾這樣教育子孫:“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禮法帥子弟,在朝不可一日不以忠貞告同僚,在鄉黨不可一日不以正直化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為,敬恕而己。”[3]“忠”、“孝”、“慎”、“勤”等儒家文化觀,始終貫穿于黎氏家族的行為和著述之中,體現出一個移民家族對文化之根的記憶和堅守,這種堅守,對平播后漢人移民聚居的黔北,既是良好的示范,也是有益的帶動。
三、沙灘文化的地域特色
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受制于自然環境和風俗民情,文學創作更是如此。改土歸流有效地改變了西南邊陲土司割據稱雄的局面,推動了民族間的交流和發展,但萬山之中的自然條件并沒有改變。位于我國地勢第二級階梯邊緣的黔北,是云貴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湘西丘陵的過渡地帶,山巒起伏,地勢陡峻,交通梗阻,信息蔽塞。在清乾隆年間,貴州人口也才五百余萬。雄奇詭偉的群山,蠶叢鳥道的交通,地廣人稀的環境,對沙灘文人的生活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程千帆先生在論及文學與環境關系時說:“文學中方輿色彩,細析之,猶有先天后天之異。所謂先天者,即班氏所謂風,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謂后天者,即班氏所謂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為其根本,后者有多翻遍,蓋雖山川風氣為其大齊,而政教習俗時有熏染,山川自古若是,而政教與日俱新也。”[5]先天的自然地理,對生活于茲的沙灘作家群心理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如鄭珍《巢經巢詩鈔》,“有三百多首出現過‘山’這一意象近四百次,如果計入詞序中出現的‘山’,以及其他一些代稱山的字眼,如峰、巒、嶺、巖、石、厓等,則遠遠超過四百次。”[6]黎兆銓“蠶叢通一線,鳥道入重巖,山半成云海,輿前只石巉。難于經蜀道,險倍越崤函。間有人生出,依稀類黑猿。”[7]極力地描摹出黔北的峭山險道,成為作家外在的、易于指認的地域性界標;黎庶昌《丁亥入都記程》所記婁山同樣:“婁山即漢志之不狼山,山極高大,群峯崱屴,連延不斷。橫亙數十百里,皆婁山也,實不能指屬何峰。自黑神廟上至關門,非甚陡峻。惟立關門下瞰,則深壑中線路如蛇,陰森可畏。”[8]不管是沙灘文人吟詠的詩還是文,在取材和內容上,都打上了鮮明的黔北山地烙印。生于斯長于斯的沙灘文人,在這特有的自然景觀中,不自知地受到客觀環境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的規范,將地域文化作為邏輯思考與審美表達的起點,其中不乏柔軟的愛的溫情。在鄭珍的詩文中,哪怕是用奇字辟語,渲染了黔北山水的險峻雄奇,也很少使人感到兇險恐怖,相反,恰好有一種“歷盡萬山不覺險”的見慣不驚和隨意自然,傳達的就是這種愛和特定地域豐富多姿的生命豐采。正是這種愛,鄭珍輯《播雅》,莫友芝、黎兆勛等編輯《黔詩紀略》,黎庶昌編《全黔國故頌》、《牂柯故事》、《黔文萃》,刻《黎氏家集》,莫庭芝、黎汝謙編《黔詩紀略后編》,希望通過收集黔中散佚文獻,存留地域文化,建立“地方性知識”。
山川的風骨造就了沙灘文人不甘沉淪,勇于進取的精神。他們輯叢書,編方志,是為了彰顯貴州的特色,強調貴州并不落后,“亦有儒風”。正是這種文化自信,使他們有極強的文化自覺,敢于與中原人士一爭短長。如《遵義府志》,明確的以地域標準采錄地方事像,對遵義歷史沿革、山川河流、物產木政、職官宦績、古跡名勝,風土人情等地域空間及歷史文化作了大量的考證研究,將之記錄在案,成為人們認識黔北地域文化的教科書;而且,為了突顯地域特色,在體例上敢于創新,成就了“天下第一府志”的美譽。從某種意義上說,《遵義府志》實際上就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正如楊芝光言:“文辭典雅,堪追遺范于方姚,考據淹通,足紹絕學于顧、李,不特山川輝耀,亦閭里增其聲價焉”。[9]讓人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沙灘文化的產生,是移民文化與地域文化的完美交融。一方面,他們是移民遷居沙灘,骨子深處有一種移民前文化的優越感和對漢文化的自覺認同;另一方面,黔北艱難的生存環境,狹窄的文化空間,使他們踏實地選擇耕讀方式。荷鋤耕作、吸水破柴是生存所需,讀書著述、教化鄉土是精神所系,這就使他們的耕讀與其他地方的耕讀多了一份沉重和使命感。因此,盡管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鄭珍、莫友芝、黎庶昌功名都不高,但他們仍然潛心著述,就如耕作一樣,特別關注腳下給與他們安身立命的土地。體現在文化心理上,就使他們一只眼睛盯住眼前,關注當下;另一只眼睛卻始終關注外界,以博大的胸懷吸納外來文化,如鄭珍拜程恩澤為師,學習文字學,入程恩澤幕府;黎庶昌在西歐任參贊期間,廣泛參觀學習,對歐洲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認真觀察,并詳加記錄,撰成《西洋雜志》,被譽為“西洋十九世紀的風俗畫卷”[10];黎汝謙任日本神戶領事,與蔡國昭一起,翻譯了中國第一部《華盛頓傳》,在《時務報》發表,向國人介紹美國開國元首華盛頓的事跡。這種文化心理,不僅是沙灘文人的文化心理,也是所有貴州移民共有的文化心理。正是在這種心理下,他們踏實做人,執著堅定,同時又敢作敢為,以自身對文化的追求,參與構建了地域文化。
四、沙灘文化對地域文化的意義和價值
如前所述,從漢到明,黔北就一直沒有停下與漢文化交融的步伐。但總體來說,沙灘文化形成之前,黔北對漢文化是一種學習,相對于少數民族文化來說,是一種轉軌和融合;這種學習,雖然在土官上層是一種積極主動,但范圍有限,這從思州田氏后裔從田佑恭后就寂然無聞可見。遵義雖然在南宋時就儒學勃興,但在明代,楊氏土司出于個人利益對漢文化持疏離和抵制態度,漢文化興盛的大潮便瞬息消退,在明代近二百年的時間,播州考中進士的僅一人,而且還是從朱元璋始明廷在各地區大力興學的歷史背景之下。因而,漢文化在黔北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沒能形成民間思潮,下層群眾未能形成一種自覺的文化追求,故而影響不大,持續時間不長。整體來看,仍然是巫風盛行,“不學子弟泰然安行,無或至稍覺其非者”。
黎氏遷至沙灘后,不僅倡導耕讀傳家,更將漢文化視為生活、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具有秀才功名的黎氏兩代入黔初祖,其文化身份意識應該非常清晰,他們是“朝廷之民”而非“土司之民”,執著于漢文化就是執著于移民的文化身份,而這種身份又必須和生存環境適應。這就使黎氏家族所倡導的漢文化打上了濃郁的地域印記。始遷祖的秀才身份,使他具備了知識分子的資格,有別一般群眾;而僅具秀才的身份,離上層社會畢竟還非常遙遠,甚至連躋身官僚階層的資格都沒有。即使是黎懷智,雖任過黃岡知縣,也不過是一個七品芝麻官。因此,介于簪纓世族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文化地位,其漢文化的意識和追求,實際上是所有中下層移民能尋找到的精神支撐,也易于贏得廣大移民的響應。黎氏家族將這種意識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人格感召來提升民間精神生活,表達了偏遠地區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意識,正是在這樣的意識下,在滿清入主中原的歷史背景下,他們能以“救天下”為己任,規定“三世不應清朝科舉”,自覺斷掉了讀書人的進身之階,卻始終不懈的以讀書務本為業,在謀求生存的同時,追求崇高的品性,為周邊的漢民族儒生家庭樹立了道德典范,也從精神上產生了巨大沖擊,為今后沙灘文化的崛起奠定了良好和廣泛的群眾基礎。
康熙年間,清廷對儒家文化的大力吸納,消解了漢族知識分子的疑慮心態。到乾隆時,陳玉引入山蠶,使黔北經濟日臻富裕,成為貴州首富之區。但在嘉慶、道光年間,隨著清王朝的日漸腐朽,士子大都缺乏理想,只知埋頭時文,科考封爵,以鮮衣美食為宗,以高官厚祿、光宗耀祖為旨;或者科考無望,憑借所學訐訟鄉里,以飽其私欲,沒有仁愛廉恥之心;或者良心未泯,以課塾弟子為生,以求溫飽,無學術進取之意,無立德立功立言之志。儒學的價值觀、人生觀并未真正確立。在這樣的背景下,黎氏家族一方面積極參加科舉,以求融入主流社會;另一方面,積極倡導宋學,強調道德義理,強調個體的修身養性與道德完善,并以此教學授徒,對提升黔北儒生的思想境界有著積極意義。由于宋學缺乏干預現實的路徑,也缺乏展示立功立言的國家平臺,因此,沙灘學人又自覺地選擇漢學。一因漢學是實學,從乾嘉始,在全國即為顯學,要進入國家層面的學術話語體系,躋身全國大師之列,漢學是必由之路;二因洪亮吉、程恩澤等漢學大師先后視學黔中,奠定了漢學發展的基礎,莫與儔、鄭珍即先后出于門下;三是作為漢學先師的舍人、尹珍本為黔產,與黔中學術有深厚的歷史、地域淵源。莫與儔“教人崇篤學,去浮靡,從學者言考據,言義理,言詩古文辭,悉各就其性之所近,不拘拘焉以門戶相強。”鄭珍“其治經宗漢,析理尊宋,專精三禮,經術所不能盡者,發為詩古文辭以昌大之。” 正是這種融漢宋為一爐的學術思路,既承接了文化主流,趕上了時代演變的步伐;又打開了黔北文士的視野,為逐鹿中原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黎氏家族重視文化,重視讀書,當他們走出封閉的大山,外界優厚的讀書環境使他們倍加珍惜,如饑似渴地吸收知識,黎雪樓曾說:“人以進士為讀書之終,吾以進士為讀書之始。”在浙江桐鄉任知縣,所有的積蓄不是買田買地,而是用于購置書籍。鋤經堂近三萬卷的圖書,既是沙灘子弟讀書治學的基本工具,也打開了他們的視界,為沙灘文化崛起奠定的物質基礎。沙灘藏書作為黔北乃至貴州最大的“圖書館”,不僅哺育了鄭、莫、黎家族的沙灘文人,對蹇、宦、趙家族及桐梓趙旭、黎平胡長新等人的成長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正是沙灘文人身處下層、在艱難的環境中發自內心的向學,將讀書治學成為生存、生命中一種自覺自為的生活方式,才能使“沙灘不特為播東名勝,有清中葉曾為一全國知名之文化區。” 改變了漢文化“傳入”邊遠地區的文化流動方式,以一種新質的地域文化整體形象沖出大山,展示出輝煌的成績。
[1] 黃萬機.沙灘文化志[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2] (清)黎兆勛采詩,莫友芝傳證.黔詩紀略[M].關賢柱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3] (清)黎庶昌.遵義沙灘黎氏家譜[Z] 光緒十五年南京刊本。
[4] (清)周作輯.貴陽府志[M].貴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校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
[5] 程千帆.文論十箋[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6] 羅筱娟.鄭珍筆下的山意象[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09(6).
[7] 劉作會.黎氏家集續編[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
[8] 黎庶昌.丁亥入都紀程[Z]//《黎氏家集》,日本使署活字版本,1888.
[9] 楊芝光.民國桐梓縣志序[Z].1930年民國刊本.
[10] 黎庶昌.西洋雜志[M].鐘叔河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82.
[11] (清)鄭珍,莫友芝.遵義府志[Z].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1986重印本.
[12] 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遵義新志[Z].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1986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