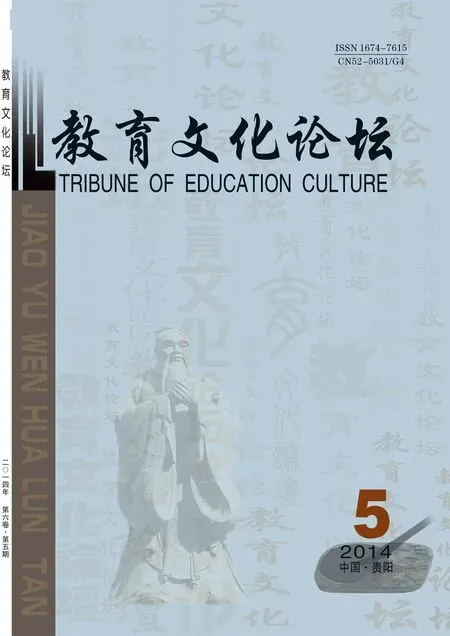款詞文化變遷:兼論傳統力量與侗族地區治理問題
梁宏信 張琪亞
(1.貴州民族大學 研究生院,貴州 貴陽 550025;2.貴州民族大學 科研處,貴州 貴陽 550025)
款規約的制定、宣傳與實踐依賴作為其語言載體的款詞來完成,因此款詞的傳承與演變過程既反映著款規約的變遷史,同時也具體地反映著侗族社會款的變遷。在傳統的侗族社會里,受漢文化和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款詞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可根據款詞表達與保存形式,將其分為口頭規約和文字規約兩個階段,由此來描述款詞的傳承與演變過程,以展示款詞文化的各時代特征及其對侗族社會傳統治理的直接影響。
一、款詞文化的生成與實踐
(一)款的形成與實踐
聚居湘、黔、桂交界地帶的侗人,由古代百越的駱越、西甌支系發展而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沒有發展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是處于一種氏族到國家的過渡階段。正因侗民族的這種過渡性,在自然秩序與國家政治之間孕育了具有原始民主性質的地方性組織“款”,通過它邀集各村寨頭人及族眾共同議定“社區秩序”以推進和維系侗族社會的良性運行及協調發展。
款以村寨為基本單位,結構上分為大、中、小三個層次,是侗族社會特有社會組織形式。朱輔《溪蠻叢笑》中載:“當地蠻夷,彼此相結,歃血為盟,援急相救,名曰門款。”[1]和周去非《嶺外代答》記:“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為款,御事以情實為款。蠻夷效順。以其中心實情,發其誓詞,故曰款也。”[2]二者即是對侗族“門款”或“款”的詳實介紹與解釋,可以看出侗族的款是一種“歃血為盟”的地方聯合性組織。
款濫觴于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或稱軍事聯盟)時期[3],存在于侗族社會除其民族自身的“過渡性”因素外,還受惠于侗族地區長期地處在傳統力量和國家政治的雙重統治之下的這一外部條件:“一部分侗族地區已經納入封建社會的統治軌道,而另外一部分侗族地區則仍然處在前階級社會階段,這是侗族款組織存在的基礎,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才有所改變。”[4]在這一段歷史時期內,侗族社會受封建政治影響極少,因此在管理上更多依賴民間組織的“款”來完成。
清代末期、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這段時期,國家政治在侗族地區逐步被強化,款這種傳統力量在社會管理中日漸“失意”。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配合、補充國家政治對侗族地區的管理,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民間規約形式——村規民約或鄉規民約,其承繼了款制度的精髓,繼續發揮傳統力量對侗族社會的治理作用。
(二)款詞:款規約的語言載體
在侗族社會里,款是建立在款規約基礎之上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具有自治、自衛性質的民間組織”[5],款規約對款組織活動及款眾行為具有直接的約束和規范作用;而具體的款規約又是款活動的產物:款眾根據侗族社會生產及生活需要,共同協商、議定出相應的規范性條款且當眾立石盟誓實施。所有參與盟誓的款眾需嚴格按照款規約行事,任何人觸犯都要被依款懲處。[6]其公布實施后,由款首在款坪或鼓樓內講誦這類款規款約,為便于講誦、記憶和產生互動效應,在其講誦過程中添加了一些富有寓意且雅俗相間的詞語,使之逐漸變成了一種口頭文學樣式,即稱之為“款詞”(Leix Kuant)。
因受早期社會生產力及侗族無文字等客觀條件限制,原始款詞是一種栽巖為誓的口頭式盟約,無文字記錄。參與立誓各方積極遵照盟約條款行事,款眾彼此監督,促進社會秩序的有序性。而地方精英的款首們為了方便款眾記憶以及款師講誦和宣傳,“借用人們喜聞樂見的詩歌形式來表達和保存款約內容”[7]形成侗族社會中寓意深遠、生動形象、富有節奏感的款詞。款詞的傳承和保存一直以極為傳統的口耳相傳形式進行,因此聚眾講款成為侗族社會傳統的款規約宣傳方式。隨漢文化進入后(明清時期),在制立款規款約時,侗人中的“知識分子”們通過漢字記音、漢字記意、土字記音的方法將這些具有約法性的款詞分條逐款地刻在石碑上,使其以文字的形式呈現出來。
然而,在上世紀80、90年代前后,款詞及款引領了侗學研究的一股“熱潮”。這股熱潮中,學者們對于款詞源流的各種探究及論證眾說紛紜,直接導致了款詞內涵與外延的模糊性,直至現今,這一論題仍為“各家之言”,難以統一。而正是由于這些探源及論證的“繁亂性”與不確定性,使款詞在進一步論述上遭遇難題。因此,本文首先要厘清這樣一個問題:款詞與款活動緊密相關,最初的形態即是語言粗糙的款規約;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款詞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豐富,不僅從內容單一(款約)的形式向內容更為豐富(款史款、約法款、遷徙款、英雄款等)的形式發展,而且更具韻律感及節奏感;在表達方式上,它也從一種單一口頭傳誦形式向文本記錄、口頭傳誦等形式發展。
二、款詞文化的傳承及演變
(一)款石:一種口頭規約的見證
侗款制度的產生源于侗族社會的失序。“當初村無款規,寨無約法的時候,好事得不到贊揚,壞事沒有受到懲處;內憂無法解除,外患無力抵御。有人手腳不干凈,園內偷菜偷瓜,籠里偷雞摸鴨。有的心中起歹意、白天執刀行兇,黑夜偷牛盜馬。還有肇事爭鬧、逞蠻相打。殺死好人、造成禍事、鬧得村寨不安寧,打得地方不太平。村村期待制止亂事,寨寨要求懲辦壞人。”[8]在這種失序的情況下,侗族各村寨頭人彼此相邀、召集族眾及地方長老進行集體議事,共同商定維持社區秩序的“款規”和“約法”,“大眾合意同心;就這樣約定、這樣講成”[9]。而于此時,經由大家“講成”后的款規約僅能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來表達、傳達與保存。因此,“口耳相傳”可以說是早期款詞的突出特征,其表現為一種無文字的口頭規約形式。
盡管早期款詞沒有文字記錄,但這種口頭規約仍具有其自身獨特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通過其自身的合法性及神圣性實現:侗族社會極力追求“平權”,他們更認同“協商”是處理問題的最有效方式,[10]款規約的合法性無疑得益于這種集體性“協商”——款規約在民眾議事中使其得以達成,并獲得民眾的集體性通過,這就意味著由此形成的款詞在侗族社會里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再加之款約的發布需以“栽巖為誓”的方式來實現最終的確定,那么使其固有的合法性在傳統民間儀式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一經實施它不但受款眾之間彼此的監督,還受規約本身“神圣性”的束縛,這雙重壓力使它更具穩定性的同時,也更有約束力、規范力和說服力。可見,集體性協商與“栽巖為誓”在款規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栽巖為誓”是侗族社會一種傳統的、嚴肅的“決議”或“決定”形式。栽巖儀式莊重且具宗教性,多在一些正式的場合與必要事件上進行,可涉及侗族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在侗族社會里影響深遠,“據調查,這種情況在明清時期的大部分侗族地區都仍流行,有的地方甚至比較盛行。”[11]甚至現今貴州苗侗地區處理一些事務時仍會使用。《侗款》中載“我們一齊好商量,商量好了,在九嶺十洞立塊石碑、開個款場。”[12]其中“立塊石碑”即是這種形式的具體體現,稱“勒石定規”或“勒石盟約”,是通過一項新規約的必經環節。“栽巖為誓”、“勒石定規”、“勒石盟約”又簡稱“栽巖”或“埋巖”,“‘栽巖’時,要舉行‘栽巖’大會,然后在集會地點將一塊長形的條石豎立栽入土中,半截露出地面,作為會議決議和決定的見證。”[13]
侗族款規約的制定一般稱作“栽大巖”或“做大巖”,是一種范圍較大的活動,所立之“巖”通稱“款石”。款石上無文字,多為質地堅硬的石塊,豎立于款坪的“款壇”之上,款詞獲得通過時“立石為證,以示威嚴。”[14]即一是表明參加誓盟者的決心有如石堅;二是表明款規約有如石頭一樣堅硬;三是表明條規一經議定有如石頭一樣永世長存。[15]而羅馬尼亞宗教史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關于“顯圣物”(hierophany)的討論中,給出這樣的解釋:早期人類注視一塊石頭時,他們看到的并非是一塊毫無生氣的石頭,他們在石頭上看到了堅固、永恒和力,是另一種絕對的生命式樣象征。由于石頭成為“顯圣物”,所顯現出某種隱形力量(一種超自然的存在)的存在而受到敬拜。[16]相似地,立款時的“栽巖”同樣具有這樣的寓意存在,侗人通過此儀式賦予“款石”一種超自然的力量,突出石頭的象征意義——“它總是通過擁有的恒久性和絕對性來提醒人們,并在這種提醒的過程中,通過類比的方法向人們展示了自己恒久性和絕對性”[17]。因此自然地,作為顯圣物的“款石”在此即會具有一種屬于神圣、屬于完全另類的某種精神存在。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款石’上沒有文字,是一種‘象征法’,但參加聚會的款眾心里對此次‘勒石’的目的和要調整的內容很清楚,如果村寨中以后出現了款石中所指向的行為,就會把違反者拉到款坪上,在款石前進行處理,這就是‘聚款’,所以在侗族原始的話語中都把‘犯罪’叫做‘犯巖’。”[18]以此類推,研究者稱侗款為“石頭法”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見,“款石”不僅見證款詞形成的整個過程,更是早期款規約的物質載體,對栽巖范圍內的款眾都產生相應的作用力。
(二)草結:款詞的另一種符號存在
款是侗族社會聯系的紐帶,它對內自治、對外防御,不起款時人們無法看見它,只有在其活動時才能清楚地知道它的存在,是侗族社會極為特殊的社會運行機制。款的活動通稱“起款”,圍繞著款詞進行,因此可將“起款”的原因歸納為款詞的制定、宣傳或執行三種,其中“制定”和“執行”視具體情況來定,而“宣傳”則是侗款最為頻繁的活動。款詞的宣傳活動通常在春秋兩季舉行,有“三月約青、九月約黃”的說法,主要原因是春秋兩季為下種和秋收的重要時節,作為南方的稻作民族,侗族對此自然特別重視,他們在春三月時起款宣誦款詞以祈求和保護禾苗不受破壞、健康成長;而“九月約黃”則是為了祈禱糧食飽滿和維護秋收的順利進行,確保稻谷完整歸倉,即反映了款詞文化在侗族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實際意義所在,也是該民族的生存智慧體現。
款詞的宣傳被稱作“說款”或“講款”,講款儀式十分莊重、嚴肅,說款者通常先在款石前三拜三叩,祭祀先祖后才能開始宣誦款詞。這項“活動一般以村寨或鼓樓為單位進行,全寨或全族人都參加,由有威望的寨老、款首或款師當眾背誦《約法款》或其它方面的款詞,并使講款活動一直處于一種莊重而神秘的氣氛中。講款者一般都站在高高的石臺上或板凳上,手中拿一大把用禾桿草或芭茅草挽成的草結。每講完一條,聽眾就齊聲高呼‘是呀’、‘對呀’,然后講款者就將一根草結放在神臺上,以示此條已經講完。接著再講一條,直至將各條講完,由此而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19]講完后,數數草結即可知道講過多少個條款。
打草結是侗族地區一種普遍的民間習俗,又稱“打草標”,以用禾桿草或芭茅草挽成草結多見。在侗族社會里,人們常常用打草結的方式來宣示自己對于某一事物的占有權,而社區成員也都會默認這種占有權的合法性,約定俗成、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打草結成為一種侗族民間普遍承認的不成文契約,草結則是這種契約被默認的標識性符號,在日常勞作中一旦遇見這種“標識符號”,大家都會彼此遵守俗規,敬而遠之,即便再喜歡也不能強行占有。否則,即會遭致世俗人言與神圣力量的共同“譴責”。在講款過程中,講款者以打草結的方式將每一條經宣示、并獲得聽款者承認的款詞做草結的標識,正是讓款眾牢記彼此達成契約的具體條款,并以這種方式使規約分條逐款地物化為具體的草結,進一步增加其合法性和神圣性“籌碼”。
(三)立碑:文字契約的建立
隨著時代的變遷,漢文化的進入使款詞文化體系日漸成熟。不僅各種規約在制定上更規范,從其表現形式上看,變化更加明顯:出現了文字形式的款詞,即款碑。款碑以漢文書寫,明顯表現為漢文化進入侗族地區后的產物;從時間上看,現存可考的款碑主要集中在清朝中后期,民國時期存有少量。[20]。究其原因,明朝以前漢文化對侗族地區的影響極為有限,而進入明清后,隨著政府加強對侗族地區的管理及大量漢學書院的設立,漢文化隨之全面深入這一地區,對侗族人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直接性的影響,也包括款的活動。漢文字進入后,侗族人民在制立或修改款規約時通過漢字記音、漢字記意、土字記音的方法將這些具有約法性的款詞分條逐款地刻抄在石碑上,以簡潔明了的文字形式以呈現出來。
文字的出現使得款規約的新時代特征表現更為明顯。在制定程序上,盡管延續了傳統款首、長老、民眾參與議事的民主原則,但發布時“栽巖”儀式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所栽之巖是一種細致地記錄了議事達成的具體內容的“款碑”。它的出現使得款規約有了更具體的保障: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記錄下來。這樣對參與立約款眾的約束除了依靠口頭承諾、集體監督、習俗維護外,還以“明文”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規約的運作更加有理有據。不僅如此,在款碑的行文格式中還清晰地記錄了立款的原因、具體內容、參與者(村寨)和時間:“第一部分是立碑的意義和原因,第二部分是立碑所要訂立的具體條款,也就是碑刻中的具體內容。第三部分是立碑的人員。第四部分是立碑的時間等。”[21]由此,盟約各方在處理款碑所指事件時即能“有法可依”,依據碑文進行論事的處理方式更顯理性和公正,也更有說服力(據明文條款懲處)。
現存款碑主要以地名、規約內容、立碑時間或立碑目的來命名,如“三龍大款款碑”、“鄉例碑”、“禁款碑”等。這些款碑除其碑文以文字記錄外,還表現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在句式結構特征上的明顯變化,從口頭盟約時期相對工整的、講究節奏感和韻律感的行文轉為平鋪直敘的敘事型句式結構,念誦起來相對平穩、直白,且簡單易懂易記;二是款詞內容上發生了變化,因受漢文化和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它既繼承了傳統的族規、寨規和地方規約,同時也融入了與國家法典相關的內容,彰顯國家政治的存在。與此同時,新時代的款詞也更加偏重于對違約者的嚴重懲處姿態,顯現了“法”的理性存在。總之,這些變化凸顯出在漢文化進入后新時代的款詞特征。
款詞在侗族社會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文字的出現使得款詞走進了“文字時代”,文字規約形式使款規約有了更明確的保障,也更加理性、更具說服力,亦是款詞在新時代的新表達和保存形式。
(四)紙、音、像:款詞的新載體
新時代的新表達和保存形式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漢文字傳入后,侗族地區一些“文化人”以手抄的形式將款詞集成文本形式,世代相傳;到了20世紀50年代,文化工作者陸續進入侗族地區進行研究,在侗文化歷史調查的過程中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的款詞,并著手刊印;80年代,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啟動與實施,侗族款詞以民族民間文化的姿態進入民間文學領域,獲得了較為全面的搜集、整理、編冊、刊印等,如當時搜集編成的《侗族款詞·耶歌·酒歌》。
而隨著黨及國家對民族文化的重視及民族文化旅游的開發與發展,侗族各村寨慶典活動時刊印相關的民族文化宣傳冊,刊印和宣傳村規民約條例,或族譜、家譜規約等將款詞記錄下來。[22]特別近幾年,一些地區還以錄像影音的形式將款詞及誦款者唱誦的現場拍錄下來制成影音文件,以DVD、VCD碟片或電腦文件的形式進行播放與傳播;部分在場者甚至用智能手機進行拍錄,進行數字化處理后再以藍牙或網絡方式分享與他人等。這些都是新時代文化語境中款詞的新的表達與保存方式,各類文本即呈現了一種新的款詞存在方式。
三、結 語
款詞是款規約的語言載體。在漢文化和國家政治大量進入侗族地區之前,它主要依靠口頭傳誦的方式來進行表達和保存,并在周而復始的“講款”活動中警示、約束、規范和教化款眾,推進和維系侗族社會的良性運行、有序發展;進入明清時期后,國家政治在這一地區的用強和漢學書院的大量設立,款詞也以漢文字形式呈現出來。但無論是口頭規約時代還是文字規約時期,款詞都需要通過集體性“協商”(集體議事)與當眾發布的方式使其本身合法化,并在傳統“栽巖”、打草結、立碑活動中使這種合法性得以增強且神圣化,成為侗族社會治理無可代替的傳統力量。這種力量的獲得既是傳統民族民主制度的賦予,也是民俗自身力量的自我推力。無論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民俗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的展示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民俗努力將人們的言行和思想觀念納入規范的維度之中;另一方面,是以傳統的力量捍衛傳統。”[23]侗人款詞的歷史變遷即展示著這種力量的存在。
[1][14] 冼光位.侗族通覽[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2]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 粟定先.論侗款流源[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4).
[4] 石開忠.侗族款組織的文化人類學闡釋[D].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4.
[5] 劉琳,張中華.廣西三江侗族侗款的傳承及其現實影響[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2(4).
[6] 丁桂芳.儀式、契約與秩序——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群體盟誓制度探析[J].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6).
[7] 張美圣.略論侗族款詞及其文學價值[J].貴州民族研究,1985(4).
[8][9][12] 楊錫光,楊錫,吳治忠.侗款[M].長沙:長沙:岳麓書社,1988:84,13,229.
[10] 林淑蓉.“平權”社會的階序與權力:以中國侗族的人群關系為例[J].臺灣人類學刊,2006(1).
[11][20][21] 石開忠.侗族款組織及其變遷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3,118-120,141.
[13] 龍耀宏.“栽巖”及《栽巖規例》研究[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
[15] 楊玉琪.款制文化探析[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6).
[16][17] (羅)米爾恰·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M].王建光 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88,89.
[18] 陳迪,徐曉光.款詞與講款—兼論黔湘桂邊區侗族社會的口頭“普法”形式[J].貴州社會科學,2010(3).
[19] 徐曉光.“石頭法”的嬗變—黔湘桂侗族地區從“款石”、“法巖”到“石碑法”的立法活動[J].貴州社會科學,2009.
[22] 吳鵬毅.自然法則與生態生產觀:款詞款約法的文化調查模式研究[D].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23] 萬建中.民俗的力量與政府權力[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