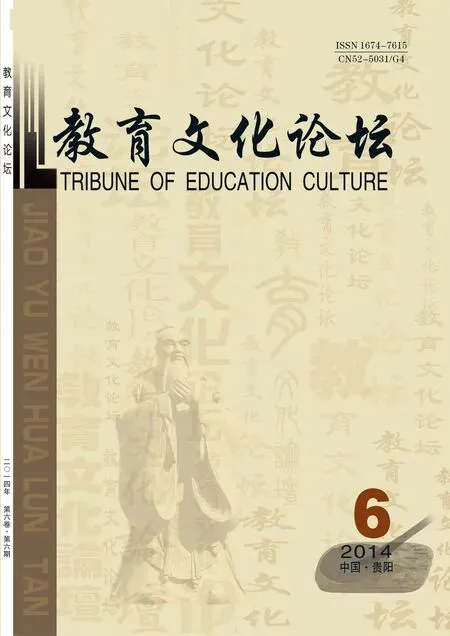教育能不能超拔人與社會
周 杰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7)
當代,興許捉來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雙城記》中的一段話可形容: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明智的年代,這是愚昧的年代;這是信任的紀元,這是懷疑的紀元;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的春日,這是失望的冬日;我們面前應有盡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將直上天堂,我們都將直下地獄……
人的精神是社會文明的表征,社會文明是人的精神的燦爛。不可否認,當下人的精神與社會文明仍然存在差距,在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時期到來的時候,教育的成敗必然體現(xiàn)著強國的意志和力量,惠及著大眾的利益和權力,展示著民族的希望和未來。為此,通過教育有效地解決發(fā)展過程中的矛盾和對抗的機制構建等問題,自然受到世人極大的關注。
一、三種人性的扭結
從人類社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歷程來看,社會大概有三種性質:神圣性,世俗性和獸性。相應的,人也具備此三性。社會與人的神圣性在《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中上帝造人的敘述中可以窺出端倪:
上帝造人的故事——永恒主上帝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了人(或譯:亞當),將生氣吹進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一個有生命的活人……永恒主上帝在東方栽種了一個園子在伊甸,把所塑造的人放在那里……永恒主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里,去耕種,去看守……永恒主上帝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能使人分別善惡(或譯:好壞)知識樹的果子,你卻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圣經(jīng)·舊約全書·創(chuàng)世記(第1章)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人,賦予了人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和價值。上帝造人,要使人成為世界的主人,人和神的形象是相同的,將人和各種自然明確區(qū)分開來,在世界上只有人和神最接近,最相似。[1]人是在神的庇護下開始生活的,人無疑具有神圣性。在基督教文化中,人和神的區(qū)別在于壽命和智慧,由于人偷吃了智慧之樹的果子,知道了是非善惡,人就具有了更多的神性。
這里面還有另外一層意義:人的肉體來自于塵土,因而是污濁罪惡的;靈魂來自上帝,因而是純潔神圣的。土地,是人之所從來之地,也是人的歸宿。因此上帝對亞當說:“你本是塵土,仍要歸于塵土。”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流傳的女媧造人的故事,也和塵土有關,據(jù)《太平御覽》所引《風俗通》云:“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1]塵土意味著世俗性,是人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人從一開始就帶著神性和世俗性走來。人的神性和世俗性,顯現(xiàn)于吃穿住行、生老病死之中,人既可以高談闊論于精神,道德,思想的玄虛之中,又斤斤計較于柴米油鹽醬醋茶道場,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人所依托的文化,是世俗中的神圣味道,神圣中的世俗味道。在猶太教和天主教看來,人的獸性的源頭,是人不聽上帝的勸告,聽毒蛇的話,偷吃禁果,形成人類的原罪。人的世界坍塌了,人的尊嚴也坍塌了,人在世上要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贖罪——“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于塵土。”[2]所以,人的社會,一開始就是一個異化的社會。本來,在創(chuàng)世記里,人和動物可以直接對話,那諭示著人性與獸性的通達。但在人的社會中,人把自己身上的獸性,投射到對他人的作踐上,個人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背信棄義,政權集團為一己之私,置人民于不顧,“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3]
當代心理學揭示獸性是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一個源泉,也是人發(fā)展的動力。教育存在的一個道理就是把人的獸性通達到人的神性,也就是使人成為人,進一步成為神。然而,人性凝滯在獸性的時候多,凝滯在神性的時候少,社會和社會的組織形式——政府,變成了人的上帝。涂爾干(Emile Durkheim)就說,社會取代了上帝……社會與人的關系,演繹為上帝與人的關系。社會教育人怎么說話,怎么做事,與社會背道而馳會使人們在生活中處處碰壁。[4]然而,“神”一般的社會,它的意志不是凡夫俗子所可窺得的,那么,社會學家是不是能夠在人和社會之間充當使者,就像先知和神之間的信使赫爾墨斯那樣?社會學家的作用,告訴人們社會要求他們?nèi)绾稳プ觥=處熢诮逃惺遣皇且材軌虬缪莺諣柲梗蔀槊癖娕c社會之間的信使?教育本身就是社會,不是社會的一部分。涂爾干認為,“教育變革總是社會變革的結果和征兆,前者要從后者得到解釋。換言之,當社會變革時,教育也隨之發(fā)生變革”。[5]變革伴隨著危機產(chǎn)生,教育也在危機中有了自己的尊嚴。
二、教育家的社會
教育家和其他思想家一樣,向來是社會禮崩樂壞的人格代表。承平歲月,是普羅大眾的天下,他們可以享受幾天醉生夢死的顛倒生活。苦難與罪惡時代,從窮鄉(xiāng)僻壤和廟堂中,會竄出幾個大匠,來榮耀他們的人生,也順便榮耀人類——也許,大匠也是從借糧的生活尷尬中爬出來的。所以,社會出現(xiàn)教育家和思想家,是人類的幸福。因為,普羅大眾總是各種各樣大匠腳底下的支撐。教育家與其他思想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教育家是來引導人類走向善與正義,使民眾走出愚昧。
蘇格拉底領悟到整個人類都是那樣的不堪,人就像在糞便土壤中綻開出來的花,人的尊嚴只在一剎那。蘇格拉底時代,社會動蕩、戰(zhàn)爭頻繁、欲壑難填、政權不斷僭越更替,舊的倫理道德秩序和信仰土崩瓦解,社會和人一般地處于獸性的癲狂與狹隘之中。他決心做一只牛虻,去蟄醒雅典這匹昏睡的純種馬,他要做社會的導師,用教育引導出人心靈中固有的智慧和道德,實現(xiàn)人的靈魂的轉向,達成至善的世界。而城邦是至善世界的人間摹本,人與社會的和諧就是人與城邦的和諧。蘇格拉底的思想不能為狹隘的希臘人接受,他遭人陷害誣告,罪名是教唆青年,褻瀆神靈,“合法地”被判死刑。蘇格拉底之死是整個人類的悲劇與恥辱,但他本人泰然處之,他認為自己是要到至善世界去,他說道:“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式考察,那就會看到很多理由希望死是一件好事。……死也可能像人們說的那樣,是靈魂從這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一個人到了那個世界,擺脫了這一班所謂法官,遇上了那一批據(jù)說在那里秉公審案的真正法官,……以及其他生時為人正直的神人們,這一移局豈不是非同小可嗎……如果這些事情是真的,我情愿死好多次。”[6]“現(xiàn)在我們各走各路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nèi)セ睢_@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清楚,只有神靈知道。”[6]這才真的是生得偉大,死得光榮。教育在于做人,蘇格拉底以身說法,做他那樣的人,那才是人的尊嚴與偉安。蘇格拉底的死,成就了人的尊嚴和哲學的尊嚴,以后兩千年的社會,都是蘇格拉底的社會。
孔子同樣從一時一地,領略到整個人類的把戲,不過如此。那時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眾暴寡,禮崩樂壞。孔子用教化與人格熏陶人心。《禮記·禮運篇》云:“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7]古希臘的至善社會是理型世界,城邦是人世間的理型社會。中國的至善社會是大同,大同是圣人理想與人民世俗生活合一的社會,所以,大同具有神圣和世俗二重性。中外圣賢對社會與人性的體認是一樣的,人性能顯現(xiàn)為善,也能顯現(xiàn)為惡,我們情愿把人性先驗地體認為善,那么社會的善惡正是人性善惡的顯現(xiàn)。教育的最終目的——善,是高于具體社會形態(tài)的形而上,不是對具體社會現(xiàn)象的稱贊或者抱怨。所以,教育和教育家的職責最終是教人跳出社會,而不是沉溺于社會。
三、人的社會: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人既要艱難地生存,也要有尊嚴地生存,實際上,人能夠屈辱地生活,也能光榮地生活,教育在于教人怎么光榮地生活。只是,蕓蕓眾生活著不易,多不去思考身后,雖然活著的時候為自己、為子孫后代打算,那多是為人的責任,卻也明白“死去原知萬事空”,可以認為那是休息去了。這大概是跟女媧學的,女媧造完人以后就去休息了,她最終沒有成為萬民靈魂的信仰與寄托,只是逢年過節(jié)在紙錢與鞭炮的煙霧里飄蕩,恰如我們死去的先人。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8]莊子也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9]死,也是人生和生命的一端,教育中沒有死的意義,人生和生命就不是完整,人最后只能是一個糊涂鬼。生的尊嚴在于死的尊嚴,死的尊嚴在于生的尊嚴,所以,古人以“養(yǎng)生送死”為人之責任。人活著的時候,生命的意義集中于信仰,中國的教育似乎從來就沒有達成信仰的境界。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一書的末尾也說:“轉眼之間,我們的社會結構竟然發(fā)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超出了環(huán)節(jié)類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與這種社會類型相適應的道德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影響力,而新的道德還沒有迅速成長起來,我們的意識最終留下了一片空白,我們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亂狀態(tài)。傳統(tǒng)失勢了。個人判斷從集體判斷的羈絆中逃脫出來了。在狂飄突起的時代里,亂作一團的各種功能也不再會有時間去互相磨合了。新的生活剎那之間出現(xiàn)了,還沒有能力把自己組織起來,還無法滿足我們內(nèi)心涌起的公平需要。”如果不加遏制,社會和人將墮入無家可歸的深淵。“中國社會當下正實踐著歷史上最大的文明轉型——從農(nóng)耕文明(內(nèi)河文明)向工業(yè)文明(海洋文明)過渡,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是兩個文明冰河系統(tǒng)之間的關系,不是社會某一個因素的變化。傳統(tǒng)社會早已定型,現(xiàn)代化社會尚未最終形成。”這或許是當今中國社會及人面臨的最大的矛盾與危險。但我們不會失去希望,這個希望,來自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教育的意義。
毋庸置疑教育,就是在生死的體驗過程中,把個人意義和社會意義,把人的神圣性、世俗性和獸性,把人的光榮與苦難、把道德與淪喪,智慧與愚昧,在人的身上通達起來。而不是祛除彼保持此——祛除獸性保持神性,驅除愚昧保持智慧,驅除苦難保持光榮。因為人的社會本來就是有善有惡的二重社會,人本身就立于二元世界。教育的最高智慧也不是驅除彼保持此,而是將彼轉化為此——將獸性轉化為神性,將愚昧轉化為智慧,將苦難轉化為光榮。
四、教育的價值和意義
教育的意義應該是叫人知道自己,知道社會——教育人民,你個人和你的時代雖然只是一個短暫,那卻是永恒。孔子、蘇格拉底也都在世界上只活了70來年罷了,但他們的精神是永恒的。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和我們的不同,在于他們知道自己,因為他們已經(jīng)超越了生死,救贖了自己,然后才有救贖天下的情懷。在社會與人的身上,獸性的膨脹,使道德、文明與精神瀕于陷落,它們雖是人的神性的燦爛,卻容易毀于人的手中,社會與人的進步是踩著生民的血汗蹣跚前行的。如果說前人的努力是為著今天的文明作注,那么今人之獸性的膨脹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們是為未來的文明道德作努力。無怪乎歷史對于產(chǎn)業(yè)革命的態(tài)度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文明都有一部閱盡人間滄桑的“血淚史”。這恰是人咎由自取,是獸性的最佳借口,或者說,是人類的必然嗎?教育教化人們,最主要的是教化他們?nèi)绾紊睿绾卧谖kU中生活。將獸性歸化為世俗性,在世俗中尋求神圣的滋味,可為教育之根本。
時代越往前走,為什么有的人越不知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簡單的人道理解是,社會是人的社會,只有尊重個人,才能尊重社會,現(xiàn)代教育就是要形成這樣的觀念。雖然早期社會人類簡陋的社會組織中,蘊涵著整個人類文明形式,就像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研究印第安部落而成就的《古代社會》所揭示的那樣。實際上,摩爾根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極其深刻的認識社會和認識人的立場,那就是文明系統(tǒng)。游牧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與我國欲進入的工業(yè)文明,不在一個文明系統(tǒng)。游牧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是以人為核心的文明,工業(yè)文明,則是以人以外的東西為核心的文明,致命的是,那些東西,都是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就等于說,人創(chuàng)造了自己殺死自己的系統(tǒng)。這種文明系統(tǒng)下的教育,教育人相信的是人以外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要教育人思考新的文明體系下的東西,語言、價值準則、規(guī)范、思想、社會制度。譬如,中國當下的性觀念,走得遠得已經(jīng)超過了西方社會,而在30年前,國家明文規(guī)定大學生不允許講戀愛。所以,我的老師輩的老大學生們,大多數(shù)都沒有戀愛經(jīng)歷,只有婚姻經(jīng)歷。至于到底是他們幸福,還是所謂的80后幸福,不能刻意比較,因為,那是兩個文明冰河的敘事。
教育的根本社會意義在于扶起時代的人。“以前,我們把社會理解為根本,現(xiàn)在,應該正本清源,人才是根本,社會是基于人的社會,為了人的社會,屬于人的社會。人改造社會,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這個新的社會為人的自由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高的條件,最終造就新的人。”[10]
[1] 黃明云,李雙印.試論《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的倫理思想[J].道德與文明,2006(01).
[2] 夏劍欽,王巽齋.太平御覽(第一卷)[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672.
[3] [英]戴維·布萊克萊吉等,王波等譯.當代教育社會學流派——對教育的社會學解釋[M].南京:春秋出版社,1989:22.
[4] [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對話集·蘇格拉底的申辯篇[M].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53-55.
[5] 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65-266.
[6]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53-54,113.
[7] 曹礎基,莊子淺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93.
[8] [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366.
[9] 畢世響.師生關系:以教學為交往實踐的特指關系——親緣倫理關系、契約倫理關系和人的關系[J].上海教育科研,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