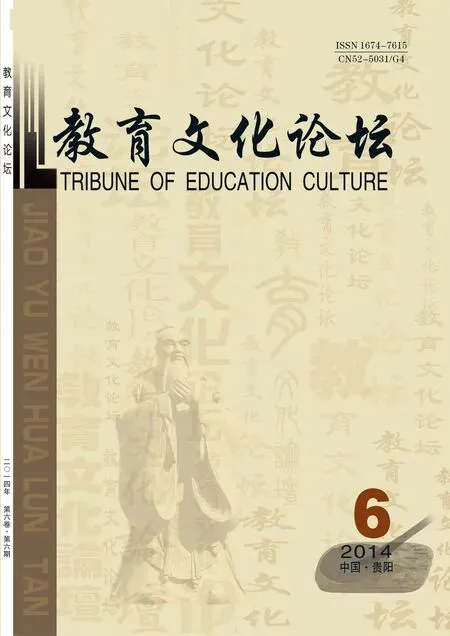香在無(wú)心處
——我的儒學(xué)情懷
吳 光
(浙江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25)
我的儒學(xué)情緣,或許可以追溯到童蒙時(shí)代。我并非出身于書香門第,而是普通的農(nóng)家子弟,模糊記憶中祖父還認(rèn)識(shí)幾個(gè)字,比父親有文化,但他什么也沒(méi)傳給我。我的父親只讀過(guò)一年半書,因?yàn)榧揖忱щy輟學(xué)了。但父親寫的毛筆字是正宗楷體,比我現(xiàn)在寫得還要好。他還能夠熟練背誦《三字經(jīng)》,并傳給我未曾謀面的哥哥,我哥哥是在我出生那年病死的。于是家里僅有的四本書——《三字經(jīng)》《百家姓》及另外兩本中醫(yī)手抄本便傳到我手里,成了我的啟蒙讀本。我母親出身于外村的破產(chǎn)地主家庭。原本家境不錯(cuò),但都給我舅舅賭博敗光了,所以正式成分是貧農(nóng)。母親雖然不識(shí)字,但對(duì)儒家的一套做人道理卻懂得很多,什么“做人要仁義”“要講信用”呀“要窮得有志氣”“唯有讀書高”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呀,簡(jiǎn)直比文化人還有文化。我想,這也許是外公、外婆教育的結(jié)果,也許是當(dāng)?shù)匚幕諊鶟撘颇灾痢鞍傩杖沼枚恢卑桑?母親在我出生那年因?yàn)閮蓚€(gè)哥哥相繼去世而悲傷過(guò)度,并染上了肺結(jié)核,終其一生也沒(méi)有治愈,但她那慈愛(ài)善良、堅(jiān)忍不拔的性格始終是我人生的榜樣、力量的源泉。
然而,在那個(gè)全面批判儒家“舊道德”的年代,我接受到的家庭儒學(xué)教育難以抵消社會(huì)上和正規(guī)學(xué)校里的反儒、批儒教育。所以青少年時(shí)代的我,對(duì)孔孟之道并無(wú)好感,尤其是當(dāng)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之類“反封建”作品以后,對(duì)所謂“封建禮教”十分反感,并且誤以為那“吃人”的禮教便是儒家的全部了。所以直到大學(xué)時(shí)期乃至文化大革命時(shí)期,我在思想上基本是反封建、反儒家的。
“文革”初期,我積極響應(yīng)偉大領(lǐng)袖“重點(diǎn)是整黨內(nèi)走資派”的號(hào)召,參加了造反派的隊(duì)伍,但我沒(méi)有打人罵人,而只是隨大流參加批斗會(huì)。然而,1967年到處發(fā)生的奪權(quán)、武斗、停產(chǎn)的形勢(shì)教育了我,使我開(kāi)始懷疑文革的正當(dāng)性,使我思想上變得“右傾”而走向反對(duì)“極左”的一面,于是我參加了調(diào)查文革紅人戚本禹的“大批判組”,并在1968年初戚本禹垮臺(tái)時(shí)公開(kāi)寫了一張批左大字報(bào),定名《戚本禹的垮臺(tái)說(shuō)明什么——論“極左機(jī)會(huì)主義”的破產(chǎn)》。從此以后,我自覺(jué)走上了反左的路線,并在林彪滅亡、四人幫倒臺(tái)時(shí)始終堅(jiān)持批判極左的立場(chǎng)。這也是我在文革以后的撥亂反正、真理討論中能夠自覺(jué)擁護(hù)改革開(kāi)放、實(shí)事求是路線的內(nèi)在思想原因。
1978年我以優(yōu)異成績(jī)考上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歷史系研究生以后,開(kāi)始系統(tǒng)閱讀諸子百家之書,雖然我的論文選題是《道家黃老之學(xué)》,但我還是寫下了批評(píng)老莊貶斥儒墨的“消極無(wú)為”主義、贊賞黃老“采儒墨之善”的“積極無(wú)為”主義的文章,并寫下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辯——論董仲舒“王道”觀的進(jìn)步性》《王充學(xué)說(shuō)的根本特點(diǎn)——實(shí)事疾妄》等肯定儒家思想的文章,這可能是我“崇儒兼道”思想的起點(diǎn)。另一方面,我在中學(xué)時(shí)代,開(kāi)始讀王充的《論衡》、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和魯迅的雜文集,頗受其批判精神與民本思想的影響,再加上自己出身農(nóng)民、又是新安江移民,我的家人和鄉(xiāng)人深受當(dāng)時(shí)“共產(chǎn)風(fēng)”之苦,幾乎處于餓死邊緣,因此能真切感受民眾疾苦,自然比較容易接受他們的社會(huì)批判精神以及民本、民主思想。這也是我能夠提出并堅(jiān)持“民主仁學(xué)”的原始根源。
1988年,我由于劉述先先生的推薦、杜維明先生的認(rèn)同而被聘任為新加坡東亞哲學(xué)研究所就任“專任研究員”,我認(rèn)真思考了新加坡經(jīng)濟(jì)騰飛的原因,認(rèn)為新加坡的成功奧秘在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法治社會(huì)、中華美德”三大法寶,并且真切感受到一個(gè)“多元社會(huì)”、“多元文化”的力量之偉大,所以在1988年9月1日的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bào)》上發(fā)表了《漫說(shuō)多元?jiǎng)僖辉返淖x史隨筆,回國(guó)后又發(fā)表了《東西方禮儀交互作用的新加坡》(載張敏杰編著《當(dāng)代國(guó)際禮儀指南》,長(zhǎng)春出版社1994年版8月版),這又是我“多元和諧文化觀”之濫觴。
當(dāng)然,我之所以能夠形成比較系統(tǒng)化的儒家思想,主要還是得益于我在研究生時(shí)期通讀了《十三經(jīng)注疏》《諸子集成》《國(guó)語(yǔ)》《戰(zhàn)國(guó)策》《史記》《漢書》《后漢書》《古史辨》等古書,得益于1988-89年在新加坡做研究時(shí)閱讀了大量宋明理學(xué)家和現(xiàn)代新儒家的著作,尤其得益于我們這個(gè)全球化、現(xiàn)代化、民主化世界和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和平崛起階段的時(shí)代思潮。這使我從不自覺(jué)到逐步自覺(jué)地走上了當(dāng)代新儒家的思路,從而建立了我的《從道德仁學(xué)到民主仁學(xué)》的理論論述。
誠(chéng)然,比起哪些現(xiàn)當(dāng)代儒學(xué)大師來(lái),我的儒學(xué)史與儒學(xué)理論的論述還是很不系統(tǒng)、很不完善的。從我主觀自覺(jué)而言,并沒(méi)有存想建立一個(gè)什么新儒學(xué)哲學(xué)體系,而且我也沒(méi)有這個(gè)能力和學(xué)養(yǎng)去建構(gòu)一個(gè)哲學(xué)體系,充其量只是提出若干經(jīng)我思考、自覺(jué)有些創(chuàng)見(jiàn)的新觀點(diǎn)、新命題罷了,只能算是一偏之論、一得之見(jiàn),絕不敢自稱是什么哲學(xué)家或思想家,也不敢奢望我的觀點(diǎn)會(huì)有多少擁躉(粉絲)。但我很喜歡山野中綻放的蘭花那種品格,很欣賞古人吟詠蘭花的詩(shī)句。20年前,我在寫于1995年4月21日而發(fā)表于10月20日《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的散文《尋蘭》一文中寫道:“世間繁花似錦,品類萬(wàn)千。而我最愛(ài)的卻是初春盛開(kāi)的山蘭,是山野間那吸納天地精華自然開(kāi)放的野蘭,那默默無(wú)言毫無(wú)矯飾的素蘭,那散發(fā)幽香激勵(lì)追求的幽蘭。屈原《九歌·禮魂》中的‘春蘭兮秋菊,長(zhǎng)無(wú)絕兮終古’,以蘭菊芳香長(zhǎng)繼的品格,比喻詩(shī)人始終不渝、千古不移的情操。宋代曹組的詠蘭詞有“著意聞時(shí)不肯香,香在無(wú)心處”的名句,則借蘭花的幽香表達(dá)詞人淡薄名利獨(dú)善其身的志趣。”我在文中還介紹了清初浙東抗清名將兵部侍郎馮京第仿照《周易》而編著的《蘭易》與《蘭史》,指出“著者雖然寫的是蘭,而所寄托的卻是性情志趣,隱含的是國(guó)家興亡、政治變革。”“我真希望那些治史而有閑情者,為政而有逸致者,也能讀讀馮侍郎的《蘭易》和《蘭史》,庶幾從中汲取一點(diǎn)修身養(yǎng)性、治國(guó)安民的教益,使人格如蘭之清,期德業(yè)似蘭之馨。所謂開(kāi)卷有益,豈虛言哉!豈虛言哉!”這是我當(dāng)初著文的感觸,也符合今天寫書的心情。也許,拙著中某些有新意的觀點(diǎn),就像山野默默開(kāi)放的蘭花,會(huì)被進(jìn)山觀景的人們?cè)跓o(wú)心中發(fā)現(xiàn)其可愛(ài)而予以欣賞的。
下附:
吳光先生新著《從道德仁學(xué)到民主仁學(xué):吳光說(shuō)儒》,于2014年7月由孔學(xué)堂書局出版,此書屬《大眾儒學(xué)書系·名家說(shuō)儒》叢書之一,題下共分五篇。
第一篇,題曰“以仁貫道的儒學(xué)發(fā)展史”,下設(shè)九小節(jié)。系著者對(duì)中國(guó)儒學(xué)史的回顧與展望,梳理了從孔子到當(dāng)代儒家仁學(xué)的發(fā)生、發(fā)展、演變簡(jiǎn)史。指出:儒學(xué)自問(wèn)世以來(lái)經(jīng)歷了先秦子學(xué)、漢唐經(jīng)學(xué)、宋明理學(xué)、清代實(shí)學(xué)、近現(xiàn)代儒學(xué)和當(dāng)代新儒學(xué)等六種形態(tài)變化,但不同時(shí)期的儒學(xué)在本質(zhì)上都是仁學(xué)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而已,它在先秦時(shí)期是“仁本禮用”的道德仁學(xué),在漢唐時(shí)代是“德主刑輔”的經(jīng)典仁學(xué),在宋明時(shí)代是“修己治人”的經(jīng)世仁學(xué),在清代中前期是“經(jīng)世致用”的力行仁學(xué),在清末近代是“中體西用”的維新仁學(xué),在現(xiàn)代是“開(kāi)新外王”的心性仁學(xué),在當(dāng)代則是“新體新用”的創(chuàng)新仁學(xué)。
第二篇,題曰 “儒學(xué)的智慧與現(xiàn)代價(jià)值”,下設(shè)十四小節(jié),系著者關(guān)于儒學(xué)的基本特質(zhì)、核心價(jià)值觀、發(fā)展方向、現(xiàn)實(shí)意義等理論問(wèn)題的探索與思考,提出了著者本人不同于前人論述的一些原創(chuàng)性觀點(diǎn)。如把儒學(xué)定位為東方型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xué),論說(shuō)了儒學(xué)的五大基本特征、儒學(xué)的政治觀、歷史觀、知行觀,儒家對(duì)德治與法治關(guān)系的表述等,還對(duì)儒家生態(tài)觀的思想模式、儒家廉政文化的內(nèi)涵與實(shí)踐方向,儒學(xué)核心價(jià)值觀的歷史演變與當(dāng)代論述及其現(xiàn)代性與普世性,“中國(guó)夢(mèng)”的思想解讀與及其核心價(jià)值觀等重要問(wèn)題進(jìn)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論說(shuō)。
第三篇,題曰“儒學(xué)的創(chuàng)新:新體新用的民主仁學(xué)”,下設(shè)六小節(jié),著者在簡(jiǎn)述當(dāng)代中國(guó)儒學(xué)復(fù)興十大標(biāo)志與新儒學(xué)主要形態(tài)的背景下,論說(shuō)了著者的新儒學(xué)理論即“民主仁學(xué)”論。民主仁學(xué)的基本思想架構(gòu),可以概括為“民主仁愛(ài)為體,禮法科技為用”的體用論,“一元主導(dǎo),多元和諧”的文化觀和以“仁”為根本之道、以“義禮信和敬”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核心價(jià)值觀。“民主仁學(xué)”為確立當(dāng)代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提供了充沛的思想資源,在政治實(shí)踐上堅(jiān)持不懈地推動(dòng)中國(gu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與多元化。它在建立民主仁政、提升公民道德人文素質(zhì)、輔助法治社會(huì)的公平正義、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中國(guó)夢(mèng)”的偉業(yè)中將起到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第四篇,題曰“治學(xué)方法經(jīng)驗(yàn)談”,下設(shè)六小節(jié),系著者30年來(lái)的治學(xué)心得。著者以為:治學(xué)方法不在于“求同存異”,而應(yīng)是“存同求異”;學(xué)問(wèn)之道,貴在“獨(dú)立思考”,反對(duì)空談與抄襲;提倡分析與綜合兼?zhèn)洌瑘?jiān)持經(jīng)世致用,并提倡“會(huì)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學(xué)術(shù)視野、“實(shí)事疾妄”的批判精神、“兼采眾長(zhǎng),但開(kāi)風(fēng)氣不為師”的學(xué)者情懷。
第五篇,題曰“弘道興儒,身體力行”,下設(shè)四小節(jié)。主要追記了著者30年來(lái)弘道興儒、身體力行的儒學(xué)實(shí)踐,諸如主編《黃宗羲全集》《王陽(yáng)明全集》《劉宗周全集》《馬一浮全集》,主持《清代浙東經(jīng)史學(xué)派資料選輯》等資料整理工作,為學(xué)界提供了寶貴可靠的原始資料,可謂嘉惠士林之善舉;又如籌辦三次黃宗羲國(guó)際研討會(huì),籌辦國(guó)際儒學(xué)、國(guó)學(xué)研討會(huì)、發(fā)起成立浙江省儒學(xué)學(xué)會(huì)和發(fā)起全國(guó)省級(jí)以上儒學(xué)團(tuán)體負(fù)責(zé)人聯(lián)席會(huì)議(中國(guó)儒學(xué)年會(huì)),以及奔波各地進(jìn)行講學(xué)弘道活動(dòng),為儒學(xué)的傳承、推廣貢獻(xiàn)了一份心力。
書末“附錄”,題曰“吳光儒學(xué)論著目錄(1979—2014)”,以便讀者檢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