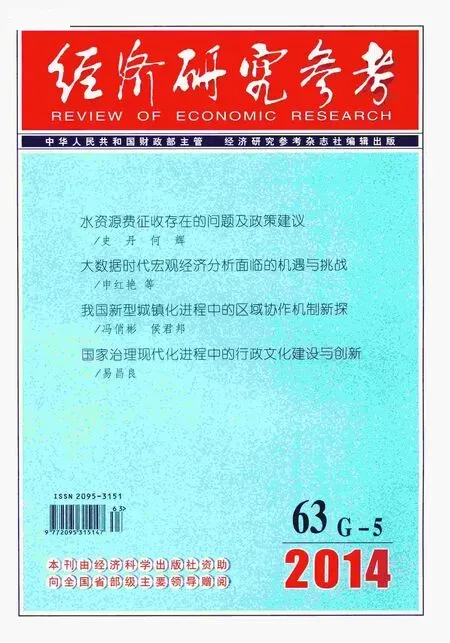基于一種新城市規模劃分的我國城市均衡發展分析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 浦 湛
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是我國城市發展的兩個顯著特征,其形成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城鎮化進程中城市規模體系逐漸失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通過差異化人口管理和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思路。目前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國以往城市規模劃分所用的方法并不能真實反映城市人口集聚程度,因此,本文采用真實反映城區人口規模的數據及城市規模的新劃分方法對我國城市體系的失衡性進行了研究,分析了造成我國城鎮發展不均衡的原因,提出應對措施。
一、我國城市和城市群發展存在失衡
(一)城市體系的結構不盡合理。
我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對城市規模等級的劃分標準進行了界定,具體為:50萬人口以上為大城市,50萬人口以下、20萬人口以上為中等城市,20萬人口以下的為小城市。1980年,《城市規劃定額指標暫行規定》將城市規模分為四個等級,在原標準基礎上補充定義人口100萬人以上城市為特大城市,但未對何為城市人口作出明確界定。1989年頒布的《城市規劃法》,沿用了大、中、小三個等級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將城市人口定義為市區和近郊區的非農業人口。該劃分方法的主要問題是依賴各城市總體規劃對城市的具體分區,而且基于戶籍的人口劃分不能真實反映城市人口集聚規模。2008年出臺的《城鄉規劃法》中未對城市規模進行規定。
本文將城市規模等級的劃分標準調整為:小城市人口規模認定從20萬人以下提升至50萬人以下,中等城市認定從原20萬~50萬人上升至50萬~100萬人,大城市從原50萬~100萬人上升至100萬~500萬人,將500萬~100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界定為特大城市,1000萬人以上人口規模的界定為超大城市。其中的城市人口采用該行政區域的城區(“城區”定義參考《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范圍的常住人口。其主要理由是,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不同等級城市人口規模標準應相應提高;另一方面,采用城區常住人口更能反映在城市空間范圍內生產生活的真實人口規模,而且可對全國城市按統一口徑的統計數據進行等級劃分。
采用以上標準對2013年我國658個城市的人口規模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目前城市體系的構成有如下特點:一是超大城市規模巨大,且還在高速擴張中。658個城市城區總人口達4.33億人,人口規模在1000萬人以上級別的城市5個,分別為上海、北京、重慶、深圳和廣州,其中達到2000萬人級別的城市為上海和北京;這五個城市人口總量達到7498.8萬人,占全部658個城市的17.3%,而且人口規模還在持續增長,解決城市病成為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二是特大城市數量及規模相對不足。500萬~100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數量僅有6個,為天津、武漢、東莞、南京、鄭州、沈陽,其人口總量僅相當于超大城市人口總量的1/2,平均城市人口僅為超大城市的2/5,帶動區域城市群發展的力量不足。三是大城市數量較多,但人口規模偏低,中西部的大城市數量偏少。大城市共有68個,其平均人口規模僅為200.5萬人,不到特大城市平均城市人口數的一半。基本上分布在東部,僅江蘇省就有8個城市達到大城市及以上規模,而人口相對較少的中西部省份如青海、甘肅、陜西、新疆、寧夏、廣西、云南、海南等僅省會城市達到大城市的規模。四是中小城市散、多、弱。中小城市數量極為龐大,占全部城市數量的88%,但城市人口規模卻僅占45%;平均人口規模僅為31.9萬人,甚至達不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一個市轄區的人口規模,相對大型城市來說沒有吸引力,無法達到經濟發展必要的規模經濟要求,部分小城市還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口凋敝。
(二)不同規模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
不同規模城市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的差異,由于沒有針對本文界定的城區范圍的有效GDP統計數據,因此,仍以全市范圍內常住人口和全市GDP作為指標,對2011年人均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進行分析,從結果來看,這些城市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人口規模超大、經濟實力強的一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這些城市城市化率高,規模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不但是人口大市,也是中國的經濟重心;第二類是以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為代表的高人口規模城市,這類城市常住人口規模在700萬~1300萬人之間,其平均人口規模小于第一類城市。此類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城市化程度也差異較大,很多農業為主的大市人口分散,集聚程度不高;第三類是低人口數量,高GDP的資源型城市,包括鄂爾多斯、東營、大慶、包頭,常住人口規模在200萬~300萬人之間,主要發展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型產業;第四類是數量眾多的大中城市,人口規模、經濟水平都相對較低。
以上述標準衡量,我國城市發展水平存在以下特征:一是700萬人常住人口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第一道門檻。常住人口700萬人以下的城市,除幾個資源型城市以外,僅有無錫、大連、珠海少數幾個城市人均GDP超過8萬元/年;超過7萬元/年的也不到10%。二是700萬~1100萬人口的城市經濟兩極分化。杭州、南京、寧波、佛山等城市雖然人口規模與第一類城市還有一定差距,但經濟水平已比較接近第一類城市的平均水平,其共性是城市化率高;而南陽、周口、菏澤、臨沂等人口大市,城市化率低,農村人口負擔重,經濟水平不高。三是1100萬人口成為城市發展實力的另一道門檻。北京、上海、廣州、天津、蘇州、深圳這些人口規模巨大、城市化率高的城市經濟實力明顯領先,而成都、重慶雖然處于中西部,經濟發展起步晚,但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
(三)各城市群發展水平不均衡。
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總結了全國初步形成的21個城市化地區,即城市群的發展范圍,此外各地還提出了其他一些城市群劃分,由于其各自地理分布、發展歷史、發展條件等因素影響,城市群的規模、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首先,就三大城市群來看,京津冀雙核心,中心強周邊弱;長三角單一核心,發展比較成熟;珠三角雙核心,發展較為均衡。其次,其他城市群的發展差異也較大。如武漢1+8城市圈,明顯的單中心化發展,位于城市圈核心的武漢,“五普”至“六普”間十年常住人口增長了17.72%,增長速度居中部城市第三,而其周邊黃石、荊門、襄陽、宜昌等城市常住人口增長率卻分別為-1.94%、-3.27%、-2.80%、-2.16%,城市圈核心城市和周邊各城市的發展不均衡。再如,部分城市群內各城市經濟各具特色、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區域綜合發展潛力較高。
二、歷史基礎疊加行政主導是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1.城鎮化發展的政策、歷史基礎造成起點不同。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戰略一直以來提及較多的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等,中小城市為重點是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戰略,但中小城市發展本身面臨的經濟規模劣勢和人才、基礎設施缺陷,導致發展戰略所引導的和實際情況是脫節的,一方面是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發展勢頭強勁,另一方面是中小城市發展乏力,沒有形成合理的大中小城市體系結構。
2.人口、經濟集聚的路徑依賴及交通成本狀況不同。保羅·克魯格曼在其新經濟地理學及空間經濟學模型中驗證了兩條重要事實:一是人口和經濟的集聚存在路徑依賴,二是交通成本的降低影響著城市人口的擴散—回流效應,并決定了城市的規模。前者要求城市發展具備一定歷史基礎和較大的原有城市規模,如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實際上只有少數具備特定歷史機遇的城市,如深圳才有后來者居上的機會。后者交通成本對城市規模的影響十分顯著。在交通成本逐步降低,城市規模逐步增大的過程中,擴散—回流效應具有不同的作用。首先隨著交通成本降低,給其他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的流入降低了成本,人口和經濟更加向中心城市集中;而當城市規模增大到一定程度,交通成本的降低卻使得在其他城市工作和居住更加便利,產業鏈條也更便于在相鄰城市布局擴散,促進城市群的協調發展。
3.行政主導、市場跟隨強化了“馬太效應”。第一,城市行政級別的差異導致在資源分配和政策傾斜上的差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資源配置和政策傾斜上往往占據優勢。一般來說,從資源占有的優勢來講,直轄市大于副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大于地級市,行政層級越高,發展優勢越大。在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基礎上,市場力量跟隨,強化了“馬太效應”,即發展條件好、實力強的城市吸引力大,發展越來越好,而發展條件不好、發展速度不快、實力弱的中小城市則吸引力差,發展機會少。第二,市場自發力量強的地方發展會較均衡。如長三角,珠三角是以市場自發力量主導的典型。長三角城市群中,僅江蘇省城市人口在100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8個,即便這些城市人口規模與上海仍有差距,但幾個主要城市的經濟普遍較發達。南京、杭州作為次中心城市,寧波、蘇州,無錫等作為再次一級的城市,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城市體系。珠三角城市群中,廣州、深圳作為一級城市,東莞、佛山成為次中心城市,惠州、中山、珠海等成為第三級城市,城市體系比較合理。可見,市場力量主導下的城市群發展相對較為均衡,形成比較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城市布局,實現城市群內城市的共同發展。
三、發展以超大和特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
1.依托城市群,整合城市體系發揮合力。城市的發展,并不能孤立地發展大城市或發展中小城市,而是要發展依托城市間網絡聯系便捷頻密的城市群體系,在城市群中形成大中小城市的合理空間分布和規模結構。發展城市群,有利于其中不同規模的城市,對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來說,可通過城市群的發展,將部分產業和城市功能向周邊中小城市轉移,緩解自身的城市病問題。對中小城市而言,承接大城市的帶動輻射、通過大城市的產業和功能轉移,為自身的發展提供機會。
2.著力發展幾個作為增長極的超大和特大城市,帶動城市群發展。城鎮化的驅動引擎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表現得非常明顯,應當適當再培育和發展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理由如下:
第一,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城市群發展的增長極。如何發展城市群,首先要培育超大和特大城市,當其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后,開始發揮其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進而實現整個城市群的發展。第二,超大城市集聚優勢突出,有規模效應。一是超大城市的集約優勢明顯,有巨大的“黑洞”效應,由于規模大,產業發達,在吸引人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明顯;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投入和運營是需要一定的人口規模支撐的,同時,超大城市的政府財力強,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第三,中國人口多、可開發用地少,因此,需要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數量多,實現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
我國目前有三大增長極,即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全部集中在東部,還應培育第四、第五個增長極帶動其他區域發展,關鍵是培育具有增長極作用的超大城市。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選擇發展條件較好、人口聚集較多、生態承受能力較強的城市,培育發展為超大或特大城市,縮小與目前三大增長極城市之間的差距。從目前的城市發展狀況來看,部分區域中心城市如沈陽、武漢、成都、西安等可著力培育,進一步吸納人口,發展為1000萬級人口規模的城市,帶動所在城市群的發展。
3.打通特大城市與其周邊地區之間的微循環,發揮回流效應。在三大城市群中,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內部城市發展比較均衡,而京津冀城市群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內部城市發展極不均衡,“環首都貧困帶”的提法就比較形象地說明了這一特征即,北京僅發揮了“極化”效應,對周邊城市資源進行吸納,而“回流”效應,即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沒有得到很好地發揮。要實現從“極化”效應向“回流”效應的過渡,實際上是實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自身發展和周邊城市發展的共贏。一方面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的繁榮,促進城市群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將居住、產業等功能分散到周邊城市,也能夠緩解自身的大城市病問題。
4.中小城市要依托城市群進行定位,以市場力量為主實現發展。對于處于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要從城市群發展的角度對自身進行定位,接受城市群核心城市輻射和為其提供服務,或走特色之路,為自身的產業發展和人口集聚提供動力。在中小城市實現發展定位后,要做好發展規劃和環境保護,能夠有條件承接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輻射和帶動,避免與核心城市落差過大,無法接受其產業和功能轉移的狀況。
與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中小城市應該主要通過市場的力量發展,同時并不是每一個中小城市都要得到發展,靠市場力量形成發展和淘汰機制,對于發展條件不利,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政府就不應一廂情愿地大搞城市建設。過去的經驗證明,如果中小城市政府一廂情愿地通過投資拉動城市建設,而實際上無法實現產業發展和人口集聚,對大量的政府投資來說是一種嚴重的浪費,同時也引發財政風險。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日益嚴重,這其中,中小城市政府的償債危機更加突出。因此,中小城市的發展不應以行政干預為主,而應以市場力量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