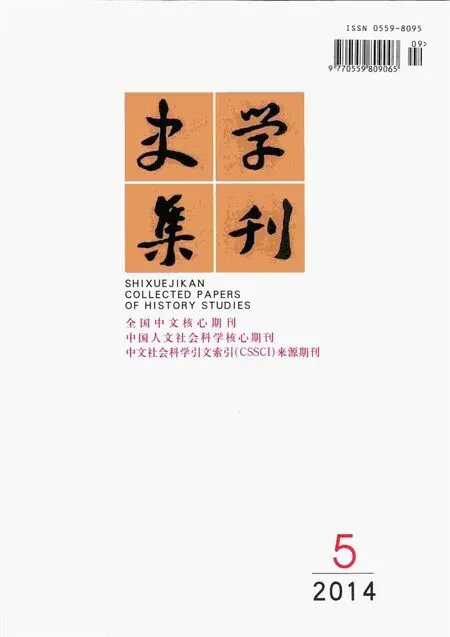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的多重悖論
王秋彬
(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在漫長的國際關系史長河中,冷戰結束以來的20多年只能算是滄海一粟。但這20年來國際關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卻遠遠超過國際關系史上的任何一個20年,這是一段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這一時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關系既延續了歷史的慣性,又體現了多元化與極化的特征,在全球、區域、行為體層面形成了國際關系的多重悖論。
悖論一:在全球層面,世界高度相互依存與全球性問題空前突出。
冷戰的終結,打破了東西方兩個平行市場的分野,原東方陣營國家逐漸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結束了世界的分裂狀態;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們的交流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人類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形成了所謂的“全球村”,全球化也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顯著的標志。全球化塑造了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這其中,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全球化正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它是由西方領導的,同時也帶有很強的美國政治經濟權力的烙印,而且它也產生了高度不均衡的后果。但是全球化并不只是西方對非西方的支配,它也像影響別的國家一樣影響了美國”。①Anthony Giddens,Runaway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03,p.4.全球化實現了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加便捷,智能手機、微信、微博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共享的信息資源不斷增長,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與創新。但同時,在全球化時代,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核擴散、貧困、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更加凸顯,這些問題有的因全球化而產生,有的早已有之,但其危害性卻被全球化進一步放大。換言之,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諸多便利與繁榮的同時,也造就了諸多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國界的限制,靠單個國家的力量已經無力解決,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治理亟待加強。
悖論二:在區域層面,區域一體化深入發展與區域沖突頻仍并存。
冷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它的示范作用下,東亞、北美、南美及非洲均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區域合作與一體化努力,建立了一系列國家間合作機制。它們旨在憑借地緣紐帶,通過集體協作,延展單個國家的實力和活動空間,增強各國抵御危機與挑戰的能力。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超國家觀念和區域治理一直是難以突破的瓶頸。以歐洲為例,從批準馬約到歐洲憲法條約,再到歐債危機,歐洲一體化披荊斬棘,并非一帆風順,特別是債務危機,使歐盟陷入自一體化啟動以來最嚴重的困境。作為一體化“模板”的歐洲尚且如此,其他地區開展一體化的難度可想而知,特別是那些曾經遭受過殖民統治,歷盡艱辛才獲得獨立的國家,對主權倍加珍惜,還有一些主權國家深受內部分裂勢力之擾。因此,冷戰后世界出現了一方面許多區域推進超國家組織構建,另一方面主權國家進一步分裂的場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增加了一些新成員,除了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之外,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道揚鑣,蘇丹、南聯盟一分為二,東帝汶也從印尼分離出來,科索沃、南奧塞梯等地區則擅自宣布獨立。
在區域整合的同時,地區沖突也十分頻繁。冷戰的結束給一些冷戰時期東西方斗爭色彩濃厚的地區沖突的解決創造了機會,部分久拖未決的地區熱點問題得以降溫甚至解決,但也導致原來被美蘇兩極所制約、按照美蘇戰略利益需要而被控制著的種種矛盾沖突迅速爆發,與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地區沖突合并在一起,出現了冷戰后地區沖突的新高潮。據統計,1945—1989年間,全球累計發生武裝沖突247起,年均5.5起,其中重大武裝沖突135起,占沖突總數的55%。而1990—2006年的17年間,全球發生武裝沖突214起 (冷戰時期延續下來有42起,冷戰后新增172起),年均12.6起,其中重大武裝沖突90起,占沖突總數的42%。①唐永勝、劉東哲、陳曉東:《冷戰后全球武裝沖突的特點及演變》,《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8期。這些沖突主要集中在巴爾干、中東、非洲以及原蘇聯地區。從波黑沖突到科索沃戰爭,從巴以沖突到阿拉伯之春,從索馬里內戰到非洲大湖地區之亂,從高加索到克里米亞,這些激烈的地區沖突反映了全球化時代世界血腥的一面。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2014年伊拉克反政府軍的大屠殺似乎把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人們帶回血雨腥風的歷史,世界仍沒有擺脫戰爭與屠殺的陰霾。
悖論三:在行為體層面,國際關系行為體多元化與主權國家中心地位難以撼動。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數量的急劇增加及其在國際舞臺上作用日益凸現,改變了民族國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一直處于國際事務中心角色的地位,不得不與諸多非國家行為體分享權力,國際關系行為體也更加多元化。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深陷危機的東南亞國家為了能獲得貸款援助渡過難關,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改革方案。由發達國家、新興國家以及主要中等強國組成的二十國集團,已經取代八國集團成為解決世界主要問題、推進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已故英國著名學者蘇珊·斯特蘭奇早在1996年便提出,國際關系權力從領土國家向世界市場和非國家行為體 (例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的實質性轉移正在加速。②[英]蘇珊·斯特蘭奇著,肖宏宇、耿協峰譯:《權力流散:世界經濟中的國家與非國家權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42頁。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改變了國際關系史上長期存在的國家中心主義現象。此外,在信息傳播如此迅捷的時代,人們獲取資訊變得需要更加便捷,曾經司空見慣的秘密外交在今天已經無所遁形。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的界限日趨模糊,主權國家在處理國內問題時需要更加慎重,以免國內問題外溢成國際問題,從而造成被動局面。這一方面體現了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與透明化,另一方面對主權國家則形成了無形約束。
盡管主權國家的權威在全球化時代受到一定的削弱與挑戰,但它在國際舞臺上的中心地位仍不可撼動。全球化發展的最重要推手是各國政府;主導歐債危機以及其他全球性問題解決的仍然是各國政府;大國博弈與國家間互動仍然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保護因揭露美國政府從事國際監聽活動的前特工斯諾登的是俄羅斯,而不是某個國際組織。但也應當看到,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進入了群雄并起的時代,國際關系權力出現了轉移與流散的趨勢,即由傳統強國向新興國家、由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轉移。1989年夏,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黃勝強、許銘原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頁。冷戰結束20多年來,美國在國際舞臺上一超獨霸,試圖構建以其為主導的單極世界,即使在遭受了“9·11”恐怖襲擊之后,小布什政府仍然沒有任何收斂,大力推行單邊主義路線。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美國和歐洲元氣大傷,也表明了歷史并未終結。奧巴馬上臺后放棄了單邊主義路線,轉而采取“巧實力”外交,加強與盟友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合作,以共同應對新挑戰。身陷債務危機的歐洲“列強”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向前殖民地國家請求支援。與發達國家日子普遍“不好過”相比,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迅速崛起,即使在危機時刻仍然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使國際關系權力對比呈“東升西降”的態勢,世界多極化進程加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表決權改革也隨之向新興國家傾斜,有史以來,西方第一次不得不向非西方國家讓渡自己的權力。隨著非西方世界的興起,“除了軍事層面之外,工業、金融、社會、文化等層面的權力分配正在發生轉移,即美國優勢正在喪失。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后美國世界’”。②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8.
總的說來,在全球化時代,世界進入了一個復雜多元、一體化與碎片化、國家權力 (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集中與分散并存的裂變階段。在這一時期,傳統的國際關系觀念正在解構,全球命運共同體意識已經形成,世界正在重組之中;大國之間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動,權力正在轉移,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進一步分化,部分發展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部分則陷入貧困與戰爭的惡性循環,淪為“失敗國家”;各地區紛紛開啟區域一體化進程,但還有許多歷史遺留下來的爭端與沖突影響著區域合作氛圍。這就是全球化時代世界的復雜圖景。鑒于當代國際關系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各行為體應當超越傳統的權力政治思維,探索新型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