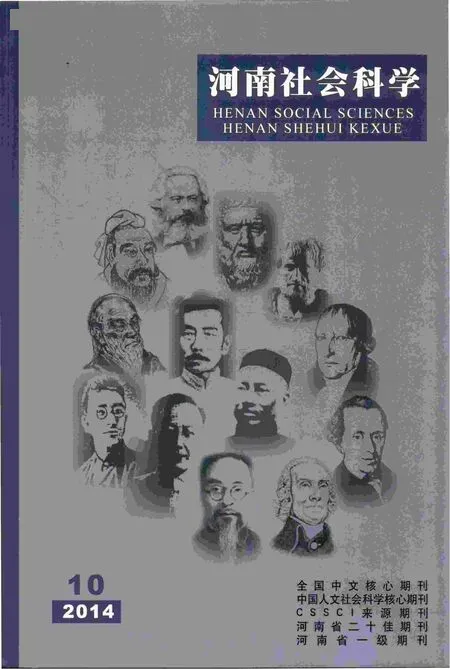從杜甫研究看現代唐詩研究的三種范式
杜學霞
(鄭州師范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在唐詩研究的現代歷史上,有三位學者必須提及,他們分別是陳寅恪、聞一多、錢鐘書。這三位學者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都是清華學人,都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又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師。其實,他們還有一個相同之處,就是都推崇杜甫,都把杜甫當成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并都留下了關于杜甫研究的重要成果。將三位學者關于杜甫的研究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杜甫的關注點、評價有很大的差別。這些差別實際上反映了他們研究方法的差別,反映了唐詩研究在現代學術中三種不同范式的差異。
下面,我們將分析他們對杜甫的研究和論述,以期考察唐詩研究的三種現代范式。
一、陳寅恪的杜甫研究
作為歷史學大師,陳寅恪是由歷史研究切入文學研究領域的。陳先生有三篇關于杜甫研究的論文,它們是《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此外,他的《柳如是別傳》中涉及杜詩43首,《元白詩箋證稿》中涉及杜詩5首。在《韋莊〈秦婦吟〉箋釋》《論再生緣》等文中,他對杜甫的詩也有論及。在這些著作中,陳先生對杜甫詩的引用和箋釋達到信手拈來、隨筆而出的程度,足見先生對杜詩的熟悉程度。
陳先生推崇杜甫,在《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稱“少陵為中國第一詩人”。他對杜甫的研究集中體現在他對杜詩的“詩史”的論述和他采用的詩史互證范式上。所謂杜甫的“詩史”說,是認為杜甫的一些詩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因而具有史料的價值。杜詩“詩史”的觀點,并非陳先生所獨創,早在晚唐,孟棨的《本事詩》就提出了杜詩的“詩史”說。在宋代千家注杜的背景下,從“詩史”角度闡發杜詩的大有人在。到了清代,錢謙益把杜詩的“詩史”說發揮到一個新的水平。雖然也有人批評錢謙益的《錢注杜詩》“事事征實,不免臆測”,但不可否認,他對杜詩的解釋是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文學與史實的關系之上的。陳寅恪研究杜甫,考察杜詩的“詩史”性質,明顯受到了錢氏的影響,并將詩史互證研究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所謂的詩史互證是指:或者從詩歌中考證一段史實,或者依據一段史實來對詩歌做出相應的解釋。例如在《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中,他依據《舊唐書》中關于安祿山、史思明傳中所謂的雜種胡以及《新唐書·回鶻傳》中所言的九姓胡,指出杜甫所謂的“雜種胡”就是“九姓胡”,其根據為杜甫與安、史為同時代人,杜甫以雜種胡看安、史,實際上中亞九姓胡被稱為雜種胡,證據可信。這是通過杜甫的詩歌考證出兩《唐書》中的差異。又如在《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中,他通過杜詩中的句子“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結合唐代史料考證出,朔方健兒并不是指郭子儀、李光弼統帥的朔方軍,而是指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同羅部落。該部落勇健善斗,為安祿山厚祿招降,在安祿山攻下長安后,該部落與安祿山為伍,助紂為虐。再如,他通過杜甫的詩歌,考證唐代典籍、制度、宮廷結構等。如杜甫《哀江頭》中有詩句“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他就根據唐代長安都城的建筑情況,指出“子美家居城南,而宮闕在城北也。自宋以來注杜詩者,多不得其解,乃改‘望’為‘忘’,或以‘北人謂向為望’為釋,殊失少陵雖欲歸家,而猶望宮闕為言,隱示其眷念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矣”[1]。陳寅恪以詩史互證的方法來研究杜甫的詩歌中“史”的價值,在他的眼里,杜甫的詩不僅是個人生命年譜與生活日記,而且是唐代詩體年譜與歷史實錄,從杜甫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安史之亂、藩鎮胡化,以及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可以了解到唐代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人事制度和財政情況等。
詩史互證也非陳寅恪的發明,而是繼承了孟子知人論世、比興說詩的優良傳統,繼承了“六經皆史”的傳統,還在此基礎上融入了西方的實證主義科學研究方法。陳先生的最大貢獻在于把這種研究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系統化、理論化,并成為一種學術范式。特別是陳先生對詩史互證的唐詩研究范式是有理論上的自覺意識的,因為他在《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明確提出“思別求一新解”,這一新解就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察唐詩,特別是考察杜甫詩歌對唐代歷史的反映。
詩史互證的研究范式對史學是有意義的。這種研究范式為學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其史學意義在于,在某些史料缺乏的情況下,經過嚴格考證的詩歌可以補充某個階段的歷史。詩史互證范式對文學研究而言同樣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我國歷來有文史不分的傳統,加之我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受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關注現實、借助詩歌表達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優良傳統。對于杜甫這樣有著強烈現實精神的詩人來說,通過詩歌創作反映重大的歷史事件,反映社會發展變化,反映自己在重大社會變化時的心理感受,是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所以,用詩史互證的方法研究杜甫的詩歌,可以有助于我們了解唐代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
二、聞一多的杜甫研究
聞一多從事唐詩研究的時間是1928~1940年。1933年,他給友人饒孟侃的信中曾提及他的古典文學研究計劃共八項,其中有六項是與唐詩有關的,這六項是《全唐詩校勘記》《全唐詩外編》《全唐詩小傳補訂》《全唐詩人生卒年考》《杜詩新注》《杜甫傳記》。由于先生的英年早逝,他的唐詩研究計劃沒能如愿完成,僅留下來《唐詩大系》《唐詩雜論》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他列入的唐詩研究計劃中,關于杜甫的就有兩項,足見杜甫在他唐詩研究中的位置。聞一多的早逝,給唐詩研究留下了很大遺憾,如果不是這樣,按照他原先的計劃,他肯定會為我們留下更多的唐詩研究成果。而他當時的研究,已經具有了范式的意義和價值。從他關于杜甫的研究成果《杜甫》《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少陵先生交游考略》等著作中,我們仍可以看出他的獨特的唐詩研究范式。
關于聞一多的唐詩研究范式,已經有不少學者研究,只是這些研究成果的觀點有很大出入。董乃斌把聞一多稱為唐詩研究中鑒賞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鑒賞學派研究唐詩,主要立足于自身讀詩的美感體驗,著眼于對唐詩的美學分析,發掘唐詩的美學意義,并努力從中抽出某種帶規律性的認識,同時也使盡可能多的讀者能夠領略唐詩之美”[2]。他總結出聞一多唐詩鑒賞的幾個重要特點,如深入詩人內心世界、具有強烈深沉的歷史感、突出美感分析、用詩化語言說詩、指向哲理的升華和規律的總結等。正如董乃斌所言,聞一多擅長文學鑒賞,我們從他未能完成的《杜甫》一文中仍可以看出他用詩意筆觸為我們刻畫出的一個活潑的文學天才的形象:詩人早年的經歷、早慧的性格、與李白的歷史性會面,都被寫得栩栩如生。可惜被收入《唐詩雜論》中的《杜甫》一文沒有完成,否則我們肯定能看到他關于杜甫詩風的精彩論述,正像我們看到他對孟浩然、賈島等的論述一樣。也有人認為聞一多的唐詩研究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他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就是這種研究方法的成果。對古籍的整理和辨正是文獻學的工作,也是整個研究工作的基礎。要想做好一項研究,必須先有可靠的資料作為依據。聞一多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注重資料的整理和挖掘,力爭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對材料的準確把握上。與清代樸學的研究不同之處在于,他并不像清代樸學研究那樣從事單個的證據研究,而是結合了西方的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并將自己的研究自覺系統化、理論化。如在《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中,他不僅對杜甫的生平進行考證,還將杜甫生活時代重大的歷史文化事件描述出來,讓我們看到了杜甫生活時代大的文化背景。但是,聞一多并不滿足于文獻學工作,他認為這種工作只是自己學術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他的著力點是在文獻學基礎上,對唐詩進一步研究。
從現有的聞一多的杜甫研究成果看,聞一多的研究方法遠不止上面說的兩種能夠概括。聞一多對杜甫的研究方法的突出特點就是體現為一種“多元意識”。所謂多元意識,就是“面對‘一個對象’或‘一個問題’,一多先生總是避免只從一個方面進行思考,久而久之,就取得了方法論意義的結論”[3]。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的“多元意識”體現為以訓詁考據為基礎、鑒賞與理性分析相結合、人格與詩格相結合等多個特點。如他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是考據和文化闡釋的結合,他的《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則顯示了他對杜甫與其他唐代士人、其他詩人之間的互相影響關系,他的《杜甫》則是對杜甫人格和詩格的論述。在他的這種多元意識中,運用了唐詩文獻學、唐詩鑒賞學、唐詩文化闡釋、唐詩心理闡釋等多種研究方法。
三、錢鐘書的杜甫研究
錢鐘書關于杜甫和杜詩的論述散見于其《談藝錄》和《管錐篇》等著述中,達二百余條,足見杜詩在其詩歌研究中的地位。考慮到我們論述的對象“現代”一詞的時間限制,我們把錢先生的研究限定在1948年首版的《談藝錄》中關于杜甫的論述上。
一般研究者均知道,錢鐘書在宋詩研究方面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一部《談藝錄》有大部分是討論宋詩問題的。錢先生對杜甫如此關注也與杜甫詩是宋詩的源頭有關,與宋代詩人大多接受了杜甫詩歌的影響有關。錢先生推崇杜甫,尤其與他個人對杜甫詩歌藝術價值的欣賞有直接關系。在其《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他明確將杜甫詩標舉為中國詩的正宗。在《談藝錄》中,他更是提出“詩尊子美”,肯定了杜甫在唐代詩歌中的地位[4]。在《詩分唐宋》一文中,他論述了杜詩與宋詩的關系,指出杜甫是開宋調者;他論杜詩的境界,肯定嚴羽對杜詩的評價:“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5]認為“詩至李杜,此滄浪所謂‘入神’之作。”[6]他稱杜甫的詩是唐詩的變體,肯定杜詩的創新精神。此外,他還研究杜詩的影響,稱為“少陵七律兼備眾妙,衍其一緒,緒足名家”,并列舉了宋代以后諸詩家學習杜甫的得失[4]。
從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看出,錢先生的杜詩研究,關注的是杜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杜詩在唐詩中的體裁變化、杜詩的藝術特征等諸多問題。總之,關注的是杜詩的藝術性和文學性等方面的內容。錢先生很少像陳寅恪和聞一多那樣關心杜詩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很少關心知人論世、社會政治等“詩史”方面的內容。《談藝錄》中涉及杜詩的思想方面的內容,甚至是可以作為對知人論世評論方式提出的反證來讀的。如針對歷史上一貫討論的杜甫詩歌中的愛國忠君思想,錢先生卻說:“少陵‘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詩人例作大言,辟之榖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闕,橡飯思君,則摯厚流露,非同矯飾。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濟之才,此不可不辯。”[6]
錢先生的《談藝錄》還采用了古代詩話的寫作方式,他有意忽略詩中的本事、具體時間、地點等,體現了他對中國古代以修辭、評點、談藝的傳統詩話的繼承。但他的《談藝錄》又明顯融合了西方詩學的新觀念,是一種唐詩研究的新范式。其中,用西方現代心理學方法闡釋唐詩,就是錢先生唐詩研究的最大特色。這種闡釋方法有一個基本的理論預設——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攸同”,亦即承認在不同的作者、不同時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共同的心理。如他在《談藝錄序》中開篇即宣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6]于是,揭示人類文化各層面的“同心之言”,便成為錢鐘書學術研究中的重要主題之一。我們從他上面對杜詩的解讀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如他舉出杜詩中《至后》一篇中“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說明文學情感捉弄人、“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悖論。又如在杜甫《哀江頭》中有詩句“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宋人對杜詩的解釋,以陸游為代表,側重于將“望”字解釋為“忘”,并認為是詩人情緒惶惑,不記南北。陳寅恪用詩史互證的方法,考證唐代的宮闕方位,認為“望”反映了杜甫在顛沛流離中仍然眷顧朝廷的愛國心情。而錢先生針對這一問題,肯定宋人將“望”理解為“忘”仍然是有道理的,并認為他反映了杜甫“喪精亡魂”之際“衷曲惶亂”的心理。正如有學者評論說:“陳的說法是回到歷史當下,回到杜甫其人,錢的說法則可以引申到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性。”[7]
從錢先生對杜甫的研究看,他是以文藝學、心理學的方式在闡釋杜甫的詩歌。因此,我們可以稱他堅持的學術范式,是一種站在文藝學立場上,配以語言學、心理學、哲學和藝術學說詩的學術范式。
四、三種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問題
把三位學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也許更能看出他們的不同。
陳寅恪的研究是歷史學,他的研究范式對歷史學肯定有價值。那么這種研究范式對文學研究的價值何在呢?關于這個問題,學界一直存在爭論。筆者寧愿相信胡曉明的觀點:“詩歌文學不應僅僅被看作藝術、美學、理論的文本,而更應是文化歷史的方方面面的輻集:社會風俗、倫理問題、宗教習尚、制度文物、婦女生活、政治軍事事件、民族關系等等的文本。”[7]他的《元白詩箋證稿》就集中體現了用“詩史互證”方法研究唐詩的成就。從這部著作中,我們看到了中唐社會生活的政治、制度、宗教、風俗、道德、婚姻狀況等方面的情況,也可以看出他后來在實踐中對專主考據的研究方法有所克服。但是,這種研究方法也存在明顯的弊端。文學創作是一種虛構,雖然詩歌中的寫實性作品能夠表達某種社會現實,但并不能完全掩蓋文學的虛構性質。過分坐實,把虛構的詩歌(文學)當成有信可征的歷史,對號入座,容易忽略文學的虛構性質。還有,按照陳先生的觀點,只要具有史學意義的詩就算好詩,那么,論詩就完全可以不管其是否具有美學價值,只要具有史料價值,即便是押韻的文件也等同好詩。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陳先生的研究方法容易造成所謂史實對“詩意”的傷害,容易模糊文學和史學的界限。對此,連陳先生自己似乎也有察覺:“若有以說詩專主考據,以致佳詩盡成死句見責者,所不敢辭罪也。”[8]另外,用“詩史互證”范式研究唐詩還應該提出這樣的前提條件:該研究方法只對寫實性較強的詩歌才有效,對與社會內容關系不大的詩歌如王維、孟浩然等的一些抒寫自然的詩歌未必適用。
其實,針對陳先生詩史互證的研究范式,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反對最為激烈的,就是錢鐘書。有學者研究,錢鐘書對陳寅恪的唐詩研究范式的反對,從20世紀40年代一直持續到80年代。
錢鐘書對陳寅恪的詩史互證范式的不滿之處主要表現在哪里呢?下面兩則引文集中體現了錢先生對詩史互證研究范式的觀點:
比見吾國一學人撰文,曰《詩的本質》,以訓詁學,參以進化論,斷言:古無所謂詩。詩即紀事之史。根據甲骨鐘鼎之文,疏證六書,穿穴六籍,用力頗劬。然……為學士拘見而已。史必征實,詩可鑿空。古代詩與史混,號曰實錄,事多虛構;想當然耳,莫須有也。與其曰“古詩即史”,毋寧說:“古史即詩。”[6]
1958年,在《宋詩選注·序》中,錢先生又一次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詩的骨干,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征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的穿鑿附會。考據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9]
從以上兩則引文,我們可以看出錢先生反對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忽視了詩歌(文學)與歷史的學科之間的差別,意在維護詩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性。我們知道,文學既有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規律,我們不妨稱之為“自律”,也有與其他學科如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等相互交融之處,我們不妨稱之為“他律”。這兩項研究合在一起,才是文學研究的全部。作為文學的一種文體——詩歌(唐詩)有其審美的一面(這是唐詩的文學性的體現)。同時,由于詩是唐代主要的文學形式,加之以杜甫為代表的詩歌的確反映了唐代的社會內容,所以,就出現了從藝術審美角度研究詩歌和從歷史文化角度研究詩歌的分野。
錢鐘書反對陳寅恪的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還存在著一個大的歷史背景。現代文學研究籠罩在濃厚的歷史學背景下,其中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學人們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詩經》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這樣的背景下,錢先生維護詩歌(文學)的學科性獨立性就顯得難能可貴。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錢鐘書的著作中關于“詩史”的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其《宋詩選注·序》和《管錐篇》中,他又談到詩與史的關系,已經不是一味反對,而是承認詩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反映歷史的真實,并提出了詩歌反映歷史真實的三種方式:寫實、寄意、懷古。這一方面是因為錢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自覺接受了唯物主義文藝學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錢先生在文學評論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詩歌和歷史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關系。錢先生的轉變還說明,陳先生與錢先生各自主張的研究范式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存在互補的可能性的。文學的學科獨立性是在與其他學科的比較中產生的,事實上,要維護文學學科的所謂的“純潔性”是很難做到的,比如,錢先生自己就有意識地借鑒了文化學、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相比而言,聞一多的研究是文獻學、鑒賞學、文化詩學等多種方法的結合,其理論視野是非常開闊的。但聞先生的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唐詩研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文獻學派、鑒賞學派、歷史學派等幾個研究方向,其各自的研究對學術研究都有獨立的存在價值。一個研究者在具體的研究中要想面面俱到,是一種不現實的想法。所以,多元意識如果沒有明確文學研究方法的“本體論”意識,很容易走向偏頗,從多元滑向一元。
三位先生的研究構成了現代唐詩研究中的三種不同的研究范式,他們站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場上,依據各自不同的文化修養,為唐詩研究的現代化轉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相對于古代的唐詩研究只重視考據或者只重視文獻整理或者只重視點評等零碎的、缺乏系統性的研究,他們都在有意識地創立一種唐詩研究的新范式,所以,他們的研究都是對唐詩研究的豐富和發展。
五、三種范式對當代唐詩研究的啟示
三位先生的唐詩研究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考驗。雖然有些具體觀點被當代研究者提出質疑,但他們創立的范式至今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為我們當代的唐詩研究提供了經驗。三位大師留給我們的啟示如下:
首先,唐詩研究必須堅持文學的民族性立場。在對中國詩歌民族特色的認識上,三位先生都認識到了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明顯不同。西方的詩歌在表現內容上長于形而上的思維和寫宗教性體驗,我們可以從西方的古典詩歌如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浪漫主義詩人拉馬丁的《沉思錄》以及現代的詩歌如艾略特的《荒原》等可以看出來。而中國的詩歌創作者大多是士階層,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擔當意識和責任感,這就使中國詩歌長于現實性體現,具有寫實性特點,這種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表現得最為鮮明。陳寅恪認為“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就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的以詩史互證的方式對杜詩的“詩史”性質進行的研究也是有效的[10]。聞一多本人就是詩人,對中國詩與外國詩的不同也有清醒的認識:“西洋人不大講詩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詩,對詩有大貢獻,反足以掩護作者的疵病,使他獲得社會的原諒。”[11]聞一多認為中國詩歌的最大特征是詩人人格與詩風的統一,所以他在研究唐詩時,注重描述詩人人格與詩格的統一。我們從他關于杜甫的研究可以感覺到他對中國詩歌民族性的認知。錢鐘書也認識到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差異。如他在詩歌中推杜甫為第一人,在繪畫方面,他認為王維的畫是中國第一。很顯然,他看到了同是中國藝術,中國詩與中國畫的評價標準不應該是一樣的,這就肯定了中國詩歌的獨特性。但錢先生更強調中西方詩歌的相通之處,以此尋找出中國詩與西方詩的“文眼詩心”相通。
當今時代,堅持唐詩研究的民族性依然有著重要意義。作為中國民族詩歌的高峰,堅持唐詩研究的民族性,實際上就是堅持中國文化的民族特點,就是不以西方的文學標準來評價中國的詩歌,不以西方的文化標志來評價中國文化。堅持唐詩研究的民族性,也是抵制某些學人將西方文學研究方法不加轉化地運用于我們帶有明顯民族特色的唐詩的研究行為。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思潮涌入中國,它們在給我們的唐詩研究帶來新的視角的同時,也令唐詩研究出現了一些弊端。如有些人在研究中置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于不顧,對外來的尤其是西方的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名之為研究,實則造成對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曲解和誤讀,結果是對我們唐詩研究也危害甚大。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警覺。
其次,堅持唐詩研究的科學性。所謂科學性,就是不同于感悟、聯想等方法,而是重視邏輯的嚴密、論據、推理等方法。三位大師都深受現代西方學術思維方式和現代西方科學主義的濡染,都自覺地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都力圖把自己的學科建立在現代科學之上,并將之具體運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中。
在陳寅恪的研究中,唐詩研究的科學性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表現為借鑒了西方的實證主義方法,又加上他對清代樸學的繼承,使他的整個學術建立在嚴格而縝密的基礎上。他的杜甫研究、他的《元白詩箋證稿》都可以看出他對研究材料的重視。聞一多的唐詩研究在科學性方面與陳寅恪有些相同,他把自己的唐詩研究建立在文獻學研究上,對清代考據學與西方實證主義哲學均有借鑒,他對心理分析、神話學等多種學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他的唐詩研究的科學性尤其體現在文學比較研究法上。如《宮體詩的自贖》,他采取縱向比較的方法,把宮體詩發展歷程、轉變過程清晰地勾勒出來。錢鐘書的唐詩研究也同樣是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正如他的好友鄭朝宗所說:“錢鐘書早在青年時代,就已立下志愿,要把文藝批評上升到科學的地位。”[12]根據錢先生的文藝批評實踐,我們說他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對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自覺意識上和將文化學和心理學引入文藝批評實踐中來。
科學性是中國文學研究從古代走向現代的一個標志。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有自己的規則和規范,遵守相應的學術規范,是文學批評的前提。而當今我們有些所謂的學術研究,不顧相應的學術規范,妄加評論。更有一些“酷評”理論,置研究的理論方法于不顧,使中國詩學脫離文本,望文生義,嚴重地違背了文學研究的科學性真義,更是對文學學科的傷害。對于這種研究方法,陳寅恪早就提出過批評,稱之為“呼盧成盧,喝雉成雉”[10],胡曉明則稱之為:“畫鬼術,人天牛鬼的比較法。”[7]
再次,堅持與西方文化的對話與融合。唐詩研究的現代學術范式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會的語境中誕生的,因此與西方文化的對話與融合也是三位先生學術研究中的共同特點,正是因為三位大師在學術研究上積極地吸收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研究方法,才體現了廣闊的學術視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的發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積極主動地借鑒和吸收其他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對我們的唐詩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將本民族的詩歌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認識和審視,也將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們民族詩歌的獨特之處。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現代詩學的發展已經走過了近一個世紀,回顧歷史發展的進程,我們發現,歷史的巨變、文化觀念的更新使唐詩的當代研究站在新的起點,也對我們的唐詩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學習和借鑒三位大師的學術范式,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將唐詩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是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的。
[1]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董乃斌.唐詩研究的鑒賞學派與聞一多的貢獻[J].中州學刊,2000,(2):93—94.
[3]吳艷.論聞一多詩學的“多元意識”[J].江漢論壇,2004,(6):93—95.
[4]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5]嚴羽.滄浪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6]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7]胡曉明.陳寅恪與錢鐘書:一個隱含的詩學范式之爭[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1):69—70.
[8]陳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9]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0]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11]鄭臨川.聞一多先生與唐詩研究[J].南充師范學院學報,1983,(1):71—79.
[12]田慧蘭.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C].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