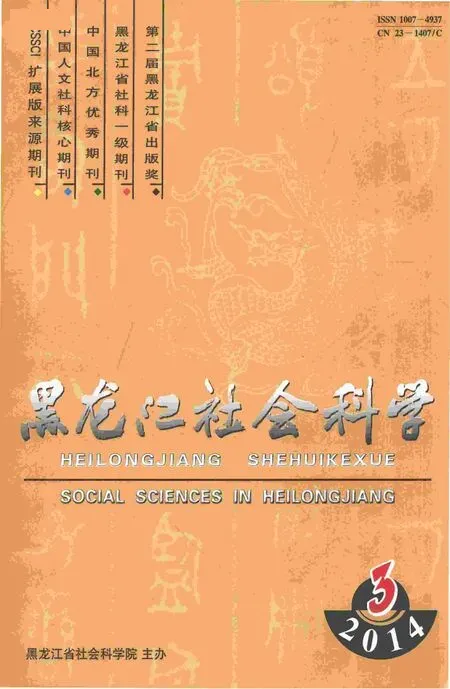清代齊齊哈爾流人社會及其文化述略
吳麗華,張守生
(1.齊齊哈爾大學文學與歷史文化學院,黑龍江齊齊哈爾161006;2.齊齊哈爾市政協文史學宣委員會,黑龍江 齊齊哈爾161006)
清代東北流人問題是東北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以往的研究宏觀較多,個案偏少。本文從齊齊哈爾流人社會成因、狀況和流人文化等方面進行探究,具體剖析流人生存生活狀態,以揭示清王朝的一個潛在社會層面。
清代齊齊哈爾流人,指因罪被清廷及其各地司法機關按大清律例強制發遣至齊齊哈爾服刑、服役的人犯。康熙三十年(1691)建城后,齊齊哈爾始具備人犯發遣條件。受清廷流人政策多次調整的影響,至乾嘉時期,齊齊哈爾流人達到一定規模,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了潛在的流人社會,其文化現象對齊齊哈爾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清代齊齊哈爾流人社會的形成
清代前期,流人發遣地集中在東北地區的盛京(今沈陽)、尚陽堡(今遼寧清河縣)、烏喇(今古林市烏拉街鎮)、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市)等地。清廷正式向黑龍江駐防將軍轄區發遣流人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分多系“為盜”之徒。至康熙二十八年,清廷已經向黑龍江發遣人犯1 612名[1],這些流人均發給黑龍江城、墨爾根城披甲為奴。因齊齊哈爾城系“最為緊要形勢之地,蒙古、錫伯、索倫、達斡爾等所居地界總匯于此,且距通達興安嶺北呼倫等地及尼布楚之道甚近”[2],康熙三十一年,經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呈請,清廷決定在齊齊哈爾駐兵。由齊齊哈爾屯等村屯選達斡爾丁1 000名,從科爾沁蒙古臺吉所獻錫伯壯丁中選1 000名披甲、2 000名附丁駐防齊齊哈爾,由200名滿洲八旗官兵進行訓練,使得齊齊哈爾城也具備了流人發遣條件。
由于史志資料匱乏,目前尚不能確定齊齊哈爾第一批流人發遣于何時。為使人犯發遣平衡,杜絕隱患,清廷對于流人發遣數量、類別等采取了調控。從康熙中葉至光緒時代,流人政策曾多次調整,對齊齊哈爾流人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四次。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康熙諭大學士等:“人命所關重大,朕數年以來將為盜者,止誅首惡,為從者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朕曾問及將軍薩布素,此等罪犯聚集,或致生事。據奏,新滿洲兵眾多,將兇徒分給為奴,勢孤力散,惡不能逞。由此觀之,不但全活甚眾,且新滿洲資益良多矣。”[3]213按照這一政策指向,清廷把大批“為盜”者發遣黑龍江。康熙三十八年,黑龍江將軍衙門移至齊齊哈爾后,流人遣戍中心開始由寧古塔向齊齊哈爾轉移。第二次是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稽查黑龍江御史章格對發遣至黑龍江的覺羅后裔生計狀況極為憂慮,認為“覺羅等又無以為生……歷年久遠,覺羅等之子孫,或致難以查考”。為此,清廷決定減少向外地發遣宗室和覺羅的數量[3]289。第三次是乾隆元年(1736)五月,清廷按照民族進行區分,對流人政策進行了一次系統調整,決定:此后滿洲有犯法應發遣者,仍發黑龍江等處;而漢人犯法者,應改發于云貴煙瘴地方。此次流放政策的調整,使得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發遣齊齊哈爾的流人數量趨于下降。至乾隆八年,清廷改令免死減等盜犯,無論有無妻室,照舊例仍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為奴。由此,因抗清失敗、文字獄獲罪者多被發遣齊齊哈爾,齊齊哈爾流人中文化人偏多概源于此。第四次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八月,鑒于“吉林、黑龍江為本朝根本之地,近年發遣人犯過多。應如何再行酌定,將擬遣人犯改發新疆及各煙瘴地方之處,著刑部詳查核議具奏。尋奏:發吉林、黑龍江人犯原例十六條請概行停止,以九條改發云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以七條改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得旨:照所議辦理。載入例冊,永遠遵行”[4]。這一新規,遂致東北流人減少。
清廷發遣政策的不斷調整,使得齊齊哈爾流人呈現出八種類別:抗清斗爭失敗案案犯、康雍乾時期文字獄案案犯、乾嘉時期東南沿海為盜案案犯、乾嘉時期教案案犯、乾嘉時期民間秘密會黨案案犯、瀆職案(包括科場案)案犯、貪贓枉法、營私舞弊案案犯、政治斗爭失勢案案犯。清廷發遣政策的調整還使得齊齊哈爾流人在數量上經歷了康熙時期漸次遣入,嘉慶以前數量較多,咸豐以后數量漸次減少的變化;遣犯的成分則呈現出由康熙前期以“盜”為多,逐步轉變為康雍之交政治流人較多,乾嘉時期文化流人較多,繼而在道光之后宗室、軍人、太監較多的變化。但從總體看,數量最多的仍然是形形色色參與反清斗爭的百姓。史志文獻記載了清末黑龍江流人的數量。據光緒九年(1883)黑龍江將軍呈送軍機處的文件顯示,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光緒八年,黑龍江將軍轄區各城共接收發遣人犯26 157名,其中:逃脫未獲遣犯518名,已故遣犯23 462名,調發遣犯1808名,現存遣犯369名內逃脫已獲遣犯273名[5]。
清廷對待發遣至黑龍江的流人,有多種處理方式。流人首先發遣到齊齊哈爾城,然后由主管刑獄的官員根據刑部判決向黑龍江將軍稟明情況,執行律例。對待宗室、覺羅,一般采取管束、圈禁,限制其自由。如嘉慶二十二年,宗室海康等因加入天理教被遣戍齊齊哈爾管束;咸豐七年(1857),宗室忠能因搶劫被圈禁三年,等等。對犯罪官員采取的懲處方式主要是安插、安置、效力行走。如原黑龍江將軍奕經等封疆大吏,原總兵陳國瑞等高級將官。不過,此類流刑往往可以納捐贖罪,三年即可釋歸,有的甚至可以復官。如原浙江學政劉鳳誥、河東河道總督李亨特等。普通百姓則往往充當苦差,主要是在驛站充當站丁,在水師營充當水手,在官莊充當勞力。對于重犯,則發給披甲人為奴,受主人奴役并累及子孫,起義者、“邪教”分子、刑事重犯往往受此懲處。
清代的齊齊哈爾城,社會結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層:第一階層是在黑龍江將軍、齊齊哈爾副都統掌控下的以滿、蒙、索倫、達呼爾、漢軍為主體的駐防八旗官兵。第二階層是隸屬八旗的水師營營丁、驛站站丁、官屯屯丁。他們非旗人,與綠營兵相似,為軍籍,屬于駐防體系的一部分。第三階層是隸于民籍的漢族、回族百姓,外來商賈,流民以及放入民籍的流人或其子孫。第四階層即為流人、賤戶。
二、清代齊齊哈爾流人的生存、生活狀態
清代齊齊哈爾流人社會的出現,是清廷長期、大量發遣流人的產物。由于流人身份、地位的不同以及所處社會環境不同,造成了流人不同的生存、生活狀態。
抵達齊齊哈爾的流人,“不盡留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6]965流人對此異常擔心,往往“夤緣求免”。據記載,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南山集》文字獄案流放齊齊哈爾的桐城方登嶧家族,原擬拆散分遣他城,是方登嶧之子方式濟靠賣衣物找人通融,家族才得以聚居齊齊哈爾。
流人生存,第一是住處。從目前的史志資料看,大部分流人都能安身立命:為奴者,有奴主提供住宿條件;被安插各處充當苦差者,由駐防各旗或部門管理,等等。但有一些流人的住宿是靠自己解決的,比如方登嶧一家。
齊齊哈爾流人中,除被圈禁的皇室成員外,都要自食其力,所從事的職業大概有以下幾種:一是幕僚。此類流人大多原是官員,如提督浙江學政劉鳳誥、天津知府張光藻等。這一類流人有文化,原有地位,故受優待,進入黑龍江將軍衙門或齊齊哈爾副都統府任文案,不僅衣食無憂,還有一定社會影響。二是教師。“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6]984有的還能進入官學教授漢文,如原衙署司務龔光瓚、知縣王性存等。三是醫生。“醫官流人,獄官土人,頂戴峨然也。”[6]929乾隆年間發遣齊齊哈爾的呂留良后人即有操此業者,如呂留良玄孫呂景儒。四是水手。“水師營……水手皆流人充役,卜魁,三百一十九;艾渾,四百二十七。流人漸多,或老懦者則輸費正役,日幫丁。水手食兵餉之半,故一正予一幫。”[7]925五是應打鷹之役者。黑龍江的鷹供是一項重要貢賦。“打鷹流人役也,人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為最。貢無定數,多不逾二十,常倍備之,以防道斃。艾渾、墨爾根各三十架,送卜魁將軍,匯選之。”[7]927這項職業極為辛苦,風險也很大。六是手工業者。“齊齊哈爾出堿,城東有堿廠,流人相聚煎曬,通行吉林。”[6]963七是菜農。“流人辟圃種菜,所產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蘿卜、王瓜、倭瓜、蔥、蒜、秦椒。”[6]987從目前所見史料可以斷定,流人為清代齊齊哈爾專業菜農之祖。八是副業。比如從事木耳采集者,“枯柞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采者春去秋還,山中為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輩,皆齊齊哈爾流人也。”[6]990九是傭工。在齊齊哈爾從事建筑行業的泥瓦匠不少,“拉核墻……掛泥壁。工匠皆流人,技拙而值貴。”[7]935作為雇農的流人更多,“齊齊哈爾等城不過負郭百里內,有田土者,世守其業,余皆樵牧自給,或傭于流人、賈客,以圖溫飽。”[6]950十是伶人。“齊齊哈爾諸廟各有會期,或三日或五日,誦經、演劇,商販醵金以辦。僧與伶皆流人也。”[6]936
關于流人的社會生活,我們可以從史志上看到一些記載。在社會習俗方面,比如:“上元賽神,比戶懸燈。歲前,立燈官。閹、屠、儈名于神前,拈之。鎖印后,一方之事,皆所主。……開印之前夕,乃自匿去。”[7]929當時為閹、屠、儈者,流人居多。又如:“流人死,茍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冢一事,亦時有之。”“客死者,柩還鄉時,請鬼票于城隍廟,遇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6]973
因身份以及發遣方式的不同,流人的境遇也存在較大差別。嘉慶年間,“一宗室遣戍將至,其本旗協領謀于同事曰:謁見問起居,我膝當幾屈耶?”[6]958又如,嘉慶年間發遣齊齊哈爾的參贊大臣愛星阿,“初謫齊齊哈爾,以百錢得雙鯉”,似可以隨意外出活動。此外,那些在將軍及副都統衙門擔任幕僚的如英和、劉鳳誥、張光藻等人,自然受到特殊的關照。又,嘉慶朝開始發遣太監之時,發給披甲為奴的太監往往態度猖狂,動輒就稱遵旨而來,使得其主人心生畏懼,“傾家奉之而不足”[8]1085。于是許多披甲人請求黑龍江將軍將其“請走”,別指一主。但轉到下一家,往往舊病復發,勒派如故。后來某宗室據實條陳于清廷,皇帝諭令嚴加管束,太監的氣焰始被打消。
而一些流人生活在社會底層,從事著低賤、陰暗的營生:“齊齊哈爾賭風最盛……流人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為博場,亦肆無忌憚之一端”[6]975;“倡妓之輩,其始流人賤戶,迫于凍餒為之”[6]976;“其無賴者乃聚賭、窩娼、竊馬牛為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6]967。
為奴流人的境遇最為悲慘。為奴的流人,按照律例,由將軍分給披甲人,即索倫、達呼爾為奴,就是從事苦役的奴隸。為了加強對為奴流人的管治,清廷在例律上做出了一系列的規定:奴主有權處死為奴之犯,不受追究;奴主要對其嚴行管束,斷不許勒索贖身及任聽其在外居住;為奴流人在受到責罰時不許自衛;等等。此外還規定:奴婢辱罵家長的,處以絞刑;毆打家長的,處斬;殺害家長的,凌遲處死。不僅如此,流犯家屬的遭遇也往往不幸,奴主圖占流人妻女的事件也時有發生。乾隆元年(1736)九月,清廷制定新規,“令黑龍江、寧古塔等處查明現在為奴人犯內,有曾為職官及舉貢、生、監出身者,一概免其為奴,即于戍所另編入該旗、該營,令其出戶當差。并出示曉諭披甲人等,俾其痛改舊習,倘仍有圖占犯人妻女,因而致斃其命者,查出,仍行照律治罪。”[8]1085
清前期,流人家屬連坐的,與流人一樣為奴,但跟隨到戍所的,并未規定為奴。然而,在戍所盤桓時間既久,盤纏用盡,其生活也就無法維持。為解決這一問題,乾隆七年三月,清廷規定,遣犯妻子須根據情況分別對待:凡是發遣黑龍江、寧古塔當差之犯,同僉妻子者,同本犯一同羈管;妻女子孫系情愿隨同者,于僉解文內注明,免監行羈管;賞旗為奴人犯的子孫前去探視,須到主管衙門報名,寫明回期,給票放行;如旗主刁難計陷,按存養良家男女為奴婢例治罪[3]335。然而,乾隆二十九年卻改訂為“為奴之妻子,一并給與原賞之人為奴”[3]486。這里雖不能排除清廷為解決流人妻子生計的考量,但實際上卻是變相的株連。為奴流犯的子孫往往世代為奴,不許出戶為民,更不許科考。
各類流人的最終命運各有不同,史載:“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系援,嘗不待三年,即占土缺。余并傭于店肆,茍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藉號呶于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6]965可見,當差流人三年流放期滿即可重返社會,而其他流人則沒有那么幸運,特別是因文字獄得禍者,往往殃及子孫,禁錮塞垣,四五代都難以翻身。
三、齊齊哈爾流人的社會貢獻及文化貢獻
約略言之,齊齊哈爾流人的社會貢獻有如下幾點:
駐防建設方面。清代在黑龍江設置有水師營,一方面擔當保衛邊疆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安插、管束效力罪官,安置發遣當差為奴之類流人的“基地”。為加強邊疆與中央的通訊、郵政聯系,保障運輸渠道和軍糧儲備,還設置有驛站、官屯:“營、站、屯三項……流人、戍卒子孫,而吳、尚、耿三藩舊戶,站丁居多。”[6]938這樣,流人以軍事化的形式,長期承擔了兵役、驛遞、官屯耕作等任務。
地方政務方面。流人擔當文案,參與黑龍江地方政務,各朝不乏其人。由于這些人大多是科舉出身且有長期的從政經驗,遂成為地方官的得力幫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龍江將軍衙門的政務水平。
開發邊疆,發展地方經濟方面。“卜魁四面數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數萬人,咸資食于蒙古糜田。蒙古耕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則終不破土,故饑歲恒多。雨后,相水坎處,攜婦子、牛羊以往,氈廬孤立,布種輒去,不復顧。逮秋復來,草莠雜獲。計一畝所得,不及民田之半。”[7]930流人的到來,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靠天吃飯的耕作模式。特別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四十四年傅玉任黑龍江將軍期間,揀放旗奴及其所帶子女進入新增設的齊齊哈爾官莊,擴大了耕地面積。不僅如此,流人還把內地休閑、翻茬、輪作等先進的耕作技術帶到了齊齊哈爾,提高了作物產量,糧食和蔬菜品種也得到極大增加,使得齊齊哈爾種植業的發展超過了黑龍江其他地方,由此奠定了近現代農業的基礎。流人的到來,也促進了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發展,從事手工業、商業、運輸業者遍布城鄉。
清代,齊齊哈爾的主流文化是駐防八旗文化。各族官兵統一于八旗整體意識與滿洲核心文化之下,說滿語、服滿俗、習滿藝(騎射)。然而,隨著流人的到來,以漢文化為表現形式的流人文化對齊齊哈爾乃至黑龍江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繁榮本地文化,流人可謂貢獻巨大。從康熙時代起,許多文化流人就以其文化自覺,或詩以詠志,或記述見聞,或結社集會,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方登嶧、訥爾樸、劉鳳誥、英和、張光藻等人閑暇之余的創作,鑄就了《述本堂詩集》《畫沙集》《五代史補注》《卜魁城賦》《龍江百五鈔》等詩集或作品,成為齊齊哈爾極為重要的文化遺產;方式濟的筆記體方志《龍沙紀略》、程煐的戲劇《龍沙劍傳奇》,也是流人潛心著述的精品。當然,齊齊哈爾流人文化的形成也有當地人的參與。嘉慶年間,齊齊哈爾出現了“惜字會”,發起人為齊齊哈爾漢軍佐領達興阿,參與者是以流人為主的“蒙師”,其主要活動是于重九日在文昌閣“焚化”,然后登高賦詩,成為當時齊齊哈爾著名的文人集會[6]935。光緒七年(1881)前后,在齊齊哈爾義學“經義書屋”興起的同時,流人王性存與當地塾師王舒毓倡導文人集會,創立了“梅花”“菊花”兩詩社。當地文化人蘇榮軒、迎善卿、色字明、陳全齋、常蘭亭、雙三樂,文化流人貴筑、廖景森、林煜南、孟振林、延憲、孫家穆等“以道義相尚,并結詩社,暇日詠歌,稱一時之盛”[9]。清代流人文化至此形成又一個高峰,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流人文化的絕響。
流人的大量到來,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改變了地方風俗。土著居民漸漸吸收、借鑒了流人從中原帶來的定居、建房室、食飯蔬、穿布帛、用瓷器等生活方式,逐步改變了穹廬為室、肉食、衣皮、用木器等生活方式。節日以及婚喪嫁娶,漢人與土著居民的風俗習慣逐漸融合,區別越來越小。流人中的從醫人員帶來的中醫知識,對當時崇尚薩滿、巫醫治病的土著居民來說影響很大,對薩滿信仰產生了沖擊。嘉慶年間,在幕府當差的齊齊哈爾達斡爾族人富林,由于長時間接觸漢文化,漸知書理,對族人大談:“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6]980當然,當地的一些習俗也影響了流人。流人到達齊齊哈爾后,也不斷學習土著居民居住飲食、騎馬射箭、打柴燒炭等適宜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另外,流人與當地居民的交往也溝通了彼此的情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清代齊齊哈爾流人社會最為明顯的變化出現在咸豐、同治之后。以實邊、足餉為目的的移民招墾興起,大批的關內流民進入黑龍江,與當地得到釋放的流人一起,成為黑龍江土地開發、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加速了八旗制的崩塌。而漢族與土著居民人口結構的轉換以及由此帶來的漢文化沖擊更為巨大,深刻地改變了齊齊哈爾的文化狀況,影響至今。
[1]樂志德,等.達斡爾資料集:第九集(檔案專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05.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錫伯族檔案史料:上冊[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9:29.
[3]李興盛,張杰.清實錄黑龍江史料摘抄:上編[M].哈爾濱:黑出管字第259號,1983.
[4]李興盛,張杰.清實錄黑龍江史料摘抄:中編[M].哈爾濱:黑出管字第259號,1983:165.
[5]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代黑龍江歷史檔案選編:光緒朝八年—十五年[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99.
[6]西清.黑龍江外記[M]//任國緒.黑水叢書:四.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
[7]方式濟.龍沙紀略[M]//李興盛,呂觀仁.黑水叢書:五.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
[8]徐宗亮.黑龍江述略[M]//任國緒.黑水叢書:四.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
[9]萬福麟,張伯英.黑龍江志稿:下[M]//崔重慶,等.黑水叢書:三.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