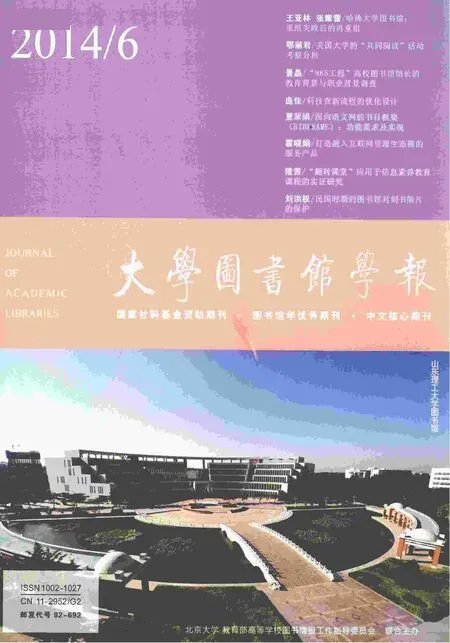明代的學術流變與江蘇私家刻書之關系*
□王桂平
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是影響藏書和刻書活動的重要原因。
學術之興,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書籍,要讀書必須得有書,要有書必須藏書。因而學術文化和私人藏書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學術文化的繁榮對私人藏書的建設起著重要的補充作用,反過來,私人藏書家輩出,利用豐富的藏書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對學術文化的發展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學術大興,社會上才能出現大量的學術成果,為刻書提供來源;學者要想得到更多的藏書,必須要有大量的刻書流傳;刻書,使得以前的大量古籍得到翻刻,重新得以流傳,時人的著作亦藉此而傳于后世。
明代重視儒臣,興學重教,招賢納士,就連武官也喜歡舞文弄墨,大大促進了藏書事業的發展。明代的私人藏書事業相當繁榮,據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統計,明代藏書家達427人(不含藩王藏書),藏書數量不斷增加,規模大大超越前代。此前私家藏書能過萬卷已屬不易,明代藏書量達10萬卷以上者為數不少。這就為刻書提供了大量的優良素材。明代私家藏書在地域分布上,北方少,南方多,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
明代自太祖洪武元年就下令免除書籍稅,經營刻書有利可圖;同時免去筆、墨等與圖書生產相關的材料和器具的稅,加之對手工業也實行了新政策,改變工匠的服役制度,使工匠有更多時間從事生產,刻書事業的生產力獲得了一個很大的解放;明中葉以后,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市民階層大大增加,對文化精神生活有一定需求;政治制度上對刻書又沒什么嚴格的管理,故刻家蜂起,刻書進入興盛期。明代江蘇私人刻印圖書十分繁盛,據冀叔英不完全統計,僅明中葉江蘇就有刻工651人、寫工23人[1]。據《江蘇刻書》統計,家刻有493家。據杜信孚的《全明分省各縣刻書考》統計,江蘇家刻有950家。
1 明初學術與私家藏書刻書
1.1 明初程朱理學為官方學術和皇朝統治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在起義過程中,即采納浙東儒生劉基、宋濂等人的主張。朱元璋在稱帝的前一年,于宮室兩廡書寫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前往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并”。宋濂等儒生,更是與朱元璋“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明朝建立初期,出于加強大一統封建皇朝統治和培養效忠于封建專制的知識分子的需要,理學,主要是程朱理學被統治者奉為安邦治國的圣典,成為官方的哲學。
宋濂等不遺余力強調程朱理學的重要性,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的“章句集注”為依據,經義以程頤、朱熹及其弟子等的注解為準繩。并規定,文章須據于宋代經義、仿元代八比法,謂之八股,又稱“制藝”、“制義”,不但強調“代圣賢立言”,不許自由發揮,而且嚴格規定體例和字數。程朱之學由是成為官方的統治學術。明洪武年間,解縉上書,建議“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作為“太平制作之一端”[2]。這是官修理學之書的開端。其用意亦在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解縉的建議,成為后來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學巨著的先聲。
永樂十二年(1414),朱棣以程朱思想為圭臬,命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人匯輯經傳、集注,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明成祖親自作序,詔頒天下,以統一全國思想。頒賜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三部理學大全的編纂完成,標志著程朱理學思想統治及其獨尊地位的確立。
明朝企圖建立一套以程朱理學為指導的、更為系統完整的哲學和政治思想體系,以統一全國的思想,從而達到加強封建思想統治的目的。它與科舉制度相結合,在封建社會后期的學術思想界以至全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于藏書刻書來說,由于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理學家同時又是大藏書家,如宋濂(1310-1380),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浙江浦江(今義烏)人,明初文學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宋濂家有青蘿山房,藏書萬余卷。這些藏書家崇尚理學,著書講學,門徒遍及南北,形成風氣,當時的藏書和刻書都以圣賢經書為主。
1.2 明初(1368—1464)的藏書刻書以程朱理學方面的著作為主
明初的統治者配合著封建制度,大力推行程朱理學。首先,廣開科舉。重新點燃了讀書人的熱情,為了應試,從朝廷國子監到地方書院,以至鄉村的社學,無不進行程朱理學教育,讀書人需要大量的儒家經典和文史圖書;其次,以八股取士取代經義取士。科舉的各級考試,都用四書五經的句子來作考試題目。在考試科目上,規定對四書五經的詮釋,都以程朱派理學家的傳注為準,程朱之學由是成為官方學術。讀書人為了金榜題名,一心攻讀與科考有關的時文,不再研究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經書大義,正所謂“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3],“家孔孟而戶程朱”[4]。李賢在《薛公瑄神道碑銘》中云:“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正。”[5]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因此收藏程朱理學和儒家的書籍占絕大多數。
在明初,三綱五常成了刻書的主要內容,朱元璋屢次下詔頒四書、五經、《通鑒綱目》、《說苑》等用于教化的書于學校。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見國子博士趙俶等云:“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為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因此“俶請頒正定十三經于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宮。”于是“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6]而且政府對四書、五經和一些重要的圖書,采用“欽頒官本”作為樣式,規定只能“依樣翻刻”。例如《御制大誥》是重要的政令書,當時規定每戶都要備一本,最初是經廠刊行的,各地大量翻印,朱元璋很不滿意,在《大誥續編》的后序中專列一條:
近監察御史丘野奏,所在翻刻印行者,字多訛舛,文不可讀,欲窮治而罪之。朕念民愚者多,況所頒二誥,字微畫細,傳刻之際,是致差訛。今特命中書大書重刻頒行,使所在有司就將此本,易于翻刻,免致傳寫之誤。敢有仍前故意差訛,定拿所司提調及刊寫者,人各致以重罪。
地域上,南方成了刻書的重要地區。《云谷臥余》中楊常彝云:“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蘇杭,而北方賈人市買以去,天下群奉為的矣。”[7]郎瑛在其筆記小說《七修類稿》中嘗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鈤抄》一冊,甚獲重利,后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明初,由于朝代更替,剛剛經過兵燹,社會經濟遭到破壞,文化事業的恢復需經時日,私家刻書不多,有文集、儒家經解等。
明天順六年(1462)華亭黃瑜刊唐之淳輯《文斷》,不分卷,十三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雙邊。明宣德九年(1434),吳訥刻(元)吳澄撰《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為十三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明正統十一年(1446),海虞魏祐刻明謝子方撰《易義主意》二卷。明景泰六年(1455),長洲韓雍刻(宋)文天祥撰《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別集》六卷,《附錄》三卷。版式為十一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明景泰元年(1450),常熟劉檄刻明高啟撰《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邊。天順七年(1463),昆山張和、歐陽溥刻(元)柳貫撰、(明)歐陽溥編《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標目》二卷,《附錄》一卷,為十二行二十字,大黑口,四周雙邊。明宣德年間,無錫馮善刊自輯《家禮集說》,不分卷,十二行二十四字,無直格,黑口,四周雙邊。
程朱理學本來就是一種脫離人們生活實踐、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的理論體系,導致明初刻書的版式變化不大,且持續了近百年之久。版式和元代的作風校為接近,字體都是趙體,字畫精整,結構嚴謹,讀之字朗悅目。版式都很闊大,大黑口,即每版中縫線的上下兩端,或者稱為版口的地方,為寬粗墨印黑條子。四周雙欄。元代刻書除遇元代諸帝的全名,一般不避諱。多用簡體字。除復刻宋本有刻工姓名外,一般無刻工姓名。
2 明中期陽明學派崛起與刻書
2.1 “心學”的崛起
程朱理學充滿著虛偽的道德說教,一旦成了士人追求利祿的敲門磚,其虛偽與無用的本質就更加暴露無遺。到了明代中期,社會矛盾已經暴露、封建倫理道德面臨危機,人們厭棄、反感程朱理學而要求變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年輕時因家遷至山陰(越城),他筑室陽明洞而自號陽明子,故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他是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他的心學,人稱王學或陽明心學,又稱“姚江之學”。他繼承并發展了南宋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提出與朱熹理學相對立的主觀唯心論的理論,王陽明心學體系主要包括“良知”是“心之本體”說、“知行合一”說和“致良知”說三個方面。特別是“致良知”的心學宗旨,以“心”代替了程朱的“天理”,將程朱理學所規定的客觀外界強加在人身上的“理”變成了人們主觀可以感知的“心”。把唯心主義學說推向了高潮,打破了程朱理學桎梏天下的局面,給困惑中的士子指明了修道的捷徑,激發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
浙中王艮代表的是市民階級的思想,他主張“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8]認為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9],沖破了當時“玄之又玄”的“良知說”,認為真理——道并不在天上,而在于現實生活中,用他的格物論根本否定了心性論。王學左派最著名的人物是李贄,他提出了更為大膽、鮮明的主張。他評述了用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儒學,指出“夫六經、語、孟,……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10],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理論基礎。
王學開展了如火如荼的講學運動,吸引了中下層士子及普通民眾,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同時李贄的私有論思想對當時的資本主義萌芽無疑在理論上作了初步探索,間接地促進了私人刻書業的發展。
2.2 文學上的復古運動
陽明學派活躍了明朝的思想界,解放了被程朱理學禁錮的思想意識,使人們把視野擴大到更廣闊的領域,為文化事業的繁榮打下了思想基礎。在文學方面,明代前期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的天下。三楊的詩文都是“頌圣德,歌太平”,毫無創新,毫無生氣,空洞無物,拘謹刻板。但由于他們先后都曾官至大學士,做過多年的太平宰相,而同時期大多數高級官僚的創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內,逐漸形成氣候,控制了整個文壇。
明代自成化、弘治時起,朝野便開始彌漫著復古的氣息。正德嘉靖年間,針對當時虛飾、萎弱的文風,以李夢陽、王世貞為首的前后七子在文壇上提倡復古運動,“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一時蔚然成風。他們鄙棄自西漢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詩歌,反對明前期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臺閣體”和“八股文”,反抗科舉八股文對思想、創作的束縛,在政治上敢于同殘暴貪婪的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進行堅決的斗爭。得到了文壇許多人的支持。
繼前后七子之后,又有歸有光、王慎中、唐順之、毛坤等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以及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先后起來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他們在文風上推崇宋代諸大家,繼續給刻書業的全面復宋創造了文化氛圍。
2.3 明中期(1465——1572)興起私家翻刻、仿刻宋本的風氣,刻書內容十分廣泛
受文學復古運動的影響,文人們不滿足于習見枯燥的經書和當代人的詩文集,而且士人的學術研究與典籍整理也需要古籍;文人嗜書好古的風尚更使他們寶愛古籍。然而當時古書流傳日稀。都穆在《南濠居士文跋》卷二《申鑒》還記述:“漢黃門侍郎荀悅所著有《漢紀》及《申鑒》二書。《漢紀》余嘗讀之,而《申鑒》恨未之見,蓋求之三十年而始得之。”
2.3.1 掀起私家翻刻、仿刻宋本的高潮
為滿足士人閱讀古文的需求,刻書業興起了翻刻宋本的風氣。復古思潮的興起,使得子書借翻刻宋本得以解放,收藏、刊刻宋版書一時風行,藏書家以藏古書多寡相爭勝。翻刻宋本的主持者多是學者、藏書家,且多為官員,他們對朝野政治、文化風氣的把握最為敏銳,反應也最快。明政府曾下令嚴禁竄改舊版文字、行格,因宋版日稀,且紙墨精美,訛誤稀少,頗得明人士大夫的喜愛,于是多由官員、學者、藏書家參與的家刻,蜂起于經濟發達、文化復古意味濃厚的吳中地區,大量翻刻宋代典籍,甚至著意規仿宋槧,翻刻、仿刻宋本成為此時出版的一大特色。
明中期自弘治朝始,拉響了翻刻、仿刻宋本的序幕。過去學術界一致認為從正德、嘉靖年間,私家刻書掀起了翻刻、仿刻宋本的熱潮。首先發端于經濟最為發達的吳下地區,以后延及官刻、坊刻,很快擴展到全國廣大地區。由于其擴展迅速,影響深遠,形成了較之前期版刻迥然不同的一代新風。從筆者查找的資料看,江蘇藏書家翻刻宋本實際上從弘治朝就開始了,最早翻刻宋本是在江陰等地。下面擇影響較大的私人刻書家來敘述。
(1)弘治年間翻刻宋本。
弘治十四年(1501),江陰涂禎得宋嘉泰本,翻刻漢桓寬《鹽鐵論》十卷。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自口,單魚尾,四周雙邊。版心鐫“論×”及頁碼。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評價涂禎翻刻宋嘉泰壬戊刻本云:“前有弘治十四年吳郡都穆序,行格與宋本同,桓寬之桓及書中匡字均沿宋諱闕筆,在明人刻書可謂極有家傳者也。”在版刻界享有盛譽。《鹽鐵論》一書,宋元舊本幾不見傳,涂禎將其刊印行世,廣為傳布,其后不少人據其翻刻。
(2)正德年間翻刻宋本。
吳縣洞庭山人陸元大,于正德十四年借得都穆家藏宋慶元、徐民瞻本《陸士衡文集》十卷、《陸士龍文集》十卷,于蘇州翻刻《晉二俊集》二十卷。該書半頁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精勁古雅。正德十六年,陸元大又在蘇州翻刊了《花間集》十卷。該書未改宋諱缺筆。卷末有晁謙之跋,跋后有“正德辛已吳郡陸元大宋本重刊”一行。該書為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心魚尾下著書名、卷次和頁數。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亦精勁古雅。蘇州袁表于正德十五年翻刻宋本《皮日休文藪》十卷,又翻刻宋本《脈經》十卷。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心上鐫“文藪序”,下鐫卷次、頁數。江陰人朱承爵于正德十六年,刻唐杜牧《樊川詩集》,用仿宋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左欄外上角刻有耳子,有“江陰朱氏文房”六字。所刻前蜀韋莊《浣花集》也有書耳,同樣有“江陰朱氏文房”六字,《四部叢刊》即據此帙影印。
(3)嘉靖間江蘇藏書家掀起翻刻宋本高潮,以蘇州為主陣地,輻射到無錫、常熟、江陰、上海、嘉定等地。
吳縣長洲一地更是摹雕宋版的中心,著名的有王延喆、袁褧等人。王延喆嘗取舊藏宋黃善夫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重加校讎,于嘉靖四年刻印,至六年印成,這是翻宋本《史記》之最佳者。此書行款格式依舊,酷似原刊,書賈難辨,幾可亂真,精雕細印,為世所稱,被譽為“王本《史記》”。袁褧為江蘇吳縣藏書、刻書世家袁氏的一個著名代表人物。家富藏書,其藏書樓為磐石齋。后又筑“兩庚草堂”為藏書之所。并專辟“嘉趣堂”為刻書之所。嘉靖十二年,吳郡袁裝的嘉趣堂復刻宋淳熙本《大戴禮記》,嘉靖十三至二十八年刊《六家文選注》六十卷,嘉靖十四年刻宋淳熙本《世說新語》,精美絕倫,為世所稱。《六家文選注》是復宋廣都裴氏本,由周慈寫板,名工李清、李澤捉刀。袁氏自跋云:“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此刻選優秀底本,摹刻甚精,校勘亦細,是家刻中之精品,被規為嘉靖間影宋刻本之代表作。葉昌熾贊其為“世所稱之精絕”,嘗被書賈抽去牌記偽冒宋版。《世說新語》是復刻宋淳熙嚴州“郡齋本”,很受時人歡迎。當時此書行世本注皆被人翻節,惟此本完整,后有陸放翁跋語,加之紙白如玉、墨凝如漆,真是奇妙珍秘。該本和仿宋刻《大戴禮記》皆因細善而同被《四部叢刊》影收。
吳縣黃魯曾、黃省曾、黃貫曾三兄弟以藏書和刻書而聞名。三兄弟得其父遺產千金,都用以藏書刻書。他們刻書非常認真,多親自校勘,請書法家吳時用寫板、高手黃周賢梓印。特別是黃省曾(1490—1540),字勉之,號五岳,嘉靖十年舉人,后因進士不第,遂棄舉子業,不復以仕進為意,“從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學詩于李夢陽”[11]。以“文始堂”、“前山書屋”、“南星精舍”等為室名刻了很多精本。嘉靖四年于蘇州翻刻宋本《嵇中散集》十卷,嘉靖十三年(1534)復刻宋本晉郭璞的《山海經》十八卷、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四十卷(二書合刻)。左右雙邊,白口,白魚尾。每半頁十二行,行十九、二十字不等。此書用白棉紙初印,字體精整秀美,是仿方塊字之代表作,書賈嘗挖“嘉靖”之“靖”補“定”,以充宋版。
長洲顧元慶,學者稱之為“大石先生”,雅號“顧山人”。為吳中藏書前輩,藏書樓名夷白堂、顧氏文房、大石山房,有藏書萬卷。顧氏讀書至勤,手不釋卷,到老也樂此不疲,多有撰述。顧元慶家有兄弟多人,都忙著治產業,山人獨以藏書、刻書自娛。他刻書亦富,且被認為是翻宋本之杰出者。嘉靖二十六年刻的《顧氏文房小說》四十一種,是他自己編輯的,多依宋本翻雕,是歷代藏書家稱道的善本,民國時期被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
此外,嘉靖七年,吳郡金李澤遠堂所刻《國語》,與吳門龔雷所刻《戰國策》,同出宋本。影刻極似原本,諱字、缺筆依舊,被《四部叢刊》影收。吳郡郭云鵬刻書多題濟美堂,亦題寶善堂。寶善堂在嘉靖二十一年刻《曹子建集》,嘉靖二十二年刻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嘉靖二十六年又刻宋陳亮編的《歐陽先生文粹》。嘉靖間所刊的《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是影摹宋廖瑩中的世彩堂本。影本摹刻逼真,并稱絕妙,實可和原刊媲美,被譽之為“濟美堂本”。徐焴字文明,太學生,明蘇州人。室名萬竹山房。嗜古博藏。嘉靖三年于蘇州翻刻宋本《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寫善鏤精,字體略肥碩,為世人所重。顧春,字元卿,別號東滄居士,明嘉靖間吳郡人,室名為世德堂,世德堂刊書多請周慈寫板、陸奎操刀。嘉靖十三年于吳縣翻刻宋本《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嘉靖十二年寫刻的《六子全書》六種六十卷,用白棉紙細印,此書版式、刀筆皆佳,字體遒勁,展卷令人賞心悅目。該書問世后,從明代至民國多次被翻刻和影印,系諸本之祖本。
蘇獻可,明嘉靖間吳郡人,室名通津草堂。嘉靖十四年于蘇州翻刻宋本《論衡》三十卷,還刻有《韓詩外傳》十卷,二書刀筆工致,字畫舒展,橫清直重,墨色極佳,也是蘇州良匠周慈、陸奎等杰作。被《天祿琳瑯書目》誤入元版,被《四部叢刊》影收。
常熟蔣孝明嘉靖二十五年翻刻宋本《陶靖節集》十卷、《總論》一卷。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無魚尾,左右雙邊。卷首有虞守愚《陶集敘》,次為梁蕭統《陶淵明集序》。文末有“晉陵蔣氏梓于家塾”篆文長方印。卷十后附蔣孝《跋》。
無錫人秦汴,字思宋,號次山,室名繡石書堂。嘉靖十五年,秦汴在無錫以繡石書屋名義翻刻宋本虞載撰《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別集》三十卷。為刻好這部書,秦汴以宋本《錦繡萬花谷》為底本,參校明華氏會通館活字本,重新刊刻。《錦繡萬花谷》為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上白口刻“萬花谷”,魚尾下刻子書名,下白口記頁數。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此外,上海陸深于嘉靖十四年在四川翻刻宋本《史通》二十卷,華亭何良俊于嘉靖二十六年翻刻宋本《劉向說苑》二十卷。金陵人陳守泉于嘉靖四十年在金陵翻刻宋本《陳學士吟窗雜錄》五十卷等等。
2.3.2 私家刻唐人詩集
在以詩人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的倡導下,江蘇刻書家刊刻唐人詩集的熱情高漲。傅增湘指出:“蓋明自嘉隆以來,七子崇尚古學,隆萬時又好用子書,一時風尚所在,刊刻甚多”。袁翼,字飛卿,吳縣人。正德舉人,然終身不仕。文震孟在《姑蘇名賢小記》中為這位愛書的寒士留下了一份歷史記載:“嘗曰:‘吾于世萬事可捐,惟積書藝菊不能忘情。’或時糦爨不繼,回視所有,欣欣自樂。”吳縣黃省曾于正德七年刻《唐劉義詩》一卷,據焦竑《國史經籍志》記載,黃省曾學詩于李夢陽,刻有《三十六家唐詩》。袁翼曾刻印多種唐人詩集,如正德十四年刻《王昌齡詩集》三卷和《李翰林集》十卷,此外還刻《皇甫冉詩集》、《皇甫曾詩集》等。黃貫曾于嘉靖三十三年用浮玉山房堂名刊《唐詩二十六家》五十卷。正德十四年,吳門陸元大刊印《唐五家詩》,輯錄中山郎士元,丹陽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延陵包何、包佶兄弟五人詩六卷。正德十五年,上元沈恩刊唐岑參撰《岑嘉州詩集》四卷。武進蔣孝,曾任戶部主事,嘉靖二十九年刻《中唐十二家詩集》七十八卷。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
正德華亭徐獻忠刊明朱警、徐獻忠輯《唐百家詩》一百七十一卷,《唐詩品》一卷。《唐百家詩》,收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卷首《詩目》后有朱警識語,稱“先大人馳心唐藝,篤論詞華,乃雜取宋刻,裒為百家”。萬歷七年,錢穀刻自輯《靜觀室三蘇文選》十六卷。
2.3.3 翻刻時文
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的多種注解被刊刻。明正統十一年,海虞魏祐刻明謝子方撰《易義主意》二卷。成化十一年,江浦張瑄刊元陳友仁輯《周禮集說》十一卷;正德十二年,吳縣王鏊刻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注》三十卷;正德十三年,吳縣黃省曾刊印《楚辭章句》十七卷;明嘉靖十二年,吳縣袁褧的嘉趣堂刻北周盧辨《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嘉靖長洲張獻翼刊《春秋公羊傳》二十卷、《谷梁傳》十二卷。此類書籍之刊刻一直延續到明后期。如萬歷長洲徐時泰的東雅堂刊漢鄭玄撰《儀禮注》十七卷。明萬歷太倉王世貞刻明張元蒙輯、王世貞校《讀易纂》五卷,《首》一卷。崇禎長洲陳仁錫刻《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大學衍義補》十六卷,《首》一卷。
科舉時文的刊刻。嘉靖郭云鵬刊自輯《文章備覽》二卷。天啟五年,馮夢龍刊刻《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備錄》一卷,該書為科舉而作,以胡安國《春秋傳》為主,并雜引各說。崇禎七年,長洲陳仁錫的閱帆堂刊自撰《四書備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
3 明朝后期(1573-1644)掀起“反王學”運動,實學興起
明朝中后期,政治黑暗、黨爭激烈,閹黨把持朝政,激化了社會矛盾。萬歷四十六年,后金努爾哈赤興兵反明,勢如破竹;崇禎三年,陜西各地農民紛紛起義,聲勢浩大。面對內憂外患,在空疏學風彌漫的大背景下,有識之士看到了空談心性的危害。在理學內部,一些有識之士在對程朱理學反思和對王陽明“心學”批判的過程中,態度鮮明地反對不良學風,提倡實學。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學者,無精思體驗之自得,一切務以詭隨為事。其視先儒之言,皆萬世不刊之定論。不惟遵守之篤,且隨聲附和,改換面目,以為見道,致使編籍繁衍,浸淫于異端之學,而不自知,反而證之于六經仲尼之道,日相背馳,豈不大可哀也。”[12]針對“心學”的誤人、誤國,他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將以輔治,乃倡為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囂囂于心性之玄幽,求之興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13]明末學者們在繼續闡發性理之學的同時,開始注意矯正王學自身的弊端。許多學者開始關注當時的政治,其后發展為對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批判,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性質。這一進步思潮,由學術思想領域而影響及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學藝術。其基本特點是尚實學、重實證、講求“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心性,力倡務實之風。明代中后期,蘇州的許多藏書家和刻書家很有國家興亡的責任感,注重經世致用書籍的著述和刊刻。
明朝人侈談良知心性,在文獻的傳播中,大量刊印理學著作、八股文章,而在翻印古籍時任意刪節,改換書名,冒充異書,脫文漏句比比皆是,甚至偽造古書,使文獻的聚集整理異常混亂,質量低下。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七所指出的:“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而是“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從萬歷年間起,刊印圖書邁入高峰,中舉為官者或學士文人幾乎都刻有文集、詩集,科舉八股等書的雕印相當繁多。總的來說,明后期刻書一方面繼承了前期刻書的優良傳統,繼續翻刻宋本,時有精品,而且注重經世書籍的刊刻;另一方面是書多至濫,質量下降,錯誤缺漏、校訂不精、印刷模糊等現象十分普遍。更有甚著刪節內容、妄改書名,致使新書殘缺不全,不利于文獻的流傳和保存。
3.1 明后期刻書數量多、種類全
明代江蘇藏書家的刻書,大部分都在萬歷朝以后。其中毛晉、陳仁錫、許自昌、趙琦美、陳禹謨等為刻書大戶,所刻書均在明后期。以中國私家藏刻書之杰出典范毛晉、陳仁錫為例。據滎陽道人鄭懋德所著《汲古閣主人小傳》,毛晉裒聚圖籍累至八萬四千冊,且宋槧元刊盈篋。毛晉既寶視典藏,且矢志刻書,“以藏以刊”。始明萬歷四十六年,迄清順治十六年,四十余年間刻書六百零二種、一萬一千零八十九頁版片。刻印的種類也很多,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外,還刻印了大量的醫書、戲曲、小說、版畫、經世致用書等。
陳仁錫,字明卿,號芝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性好學,喜著述,有《四書備考》、《經濟八編類纂》、《重訂古周禮》等。陳仁錫是蘇州閶門酉酉館主人,不但是位有名的文學家,而且是位有名的刻書家。其刻書所用堂名除酉酉館外,間或亦用奇賞齋、閱帆堂。陳氏刻書,校勘精當,多屬經史古文。他于萬歷三十三年刊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于萬歷四十三年刊印《陳沈兩先生稿》兩種和《石田先生集》十一卷,寫刻甚工細,世人多稱善。他還刊有《宋元通鑒》、《南唐書》、《陽山志》、《藏書》、《潛確居類書》、《三國志》、《東坡先生詩集》等。
3.2 明后期繼續翻刻宋本,比較精善
明萬歷以后,蘇州翻刻宋本之風延續,保持了嘉靖時遺風,堪稱佳槧。舉例如下:
徐時泰,字大來,明長洲人,室名東雅堂,萬歷中進士,官工部郎中。萬歷中他覆刻宋廖瑩中的世彩堂本,刻《昌黎先生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傳》一卷、《遺文》一卷,可謂是明代私刻中之精品。
趙均,字靈均,自號墨丘生,明崇禎間吳縣人。崇禎六年于蘇州翻刻南宋永嘉陳玉父小字刻本《玉臺新詠》十卷,摹刻甚精,紙亦良,酷似原本,書賈多以其充宋梁。《郋園讀書志》、《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中國版刻圖錄》等均著錄為覆宋本,趙氏跋語說明據宋刻翻印,字句和編次都不同于流俗之本。
3.3 注重刻經世致用書籍的撰刻
(1)固海防、抗倭寇之書的撰刻
王士騏,字冏伯,太倉人。父世貞,嘉靖進士,刑部尚書,文壇盟主。萬歷二十四年,士騏撰成《皇明馭倭錄》九卷,該書以編年的形式,匯集了從明太祖到萬歷歷朝皇帝有關馭倭的詔旨、大臣的章奏、中外戰守方略等。王在晉,號岵云,江蘇太倉人,萬歷二十年進士,官兵部尚書。王在晉纂成《海防纂要》十四卷,在參考鄭若曾的《籌海圖編》、鄧鐘的《籌海重編》、范淶的《海防類考》的基礎上,旁搜統括,匯集有關海防的各種資料編成,分為山海輿地圖、沿海事宜、外國考程途針路、朝貢通考、朝鮮復國經略、馭倭方略、船器攻圍法等十六部分,于萬歷四十一年刻之。
(2)研究鄰國之書的刊刻
趙宧光,字凡夫,一生不仕,太倉人,以高士名冠吳中。萬歷四十五年,與葛一龍刻《朝鮮史略》六卷,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
(3)經世文編的撰刻
崇禎十一年,華亭陳子龍的平露堂刊自輯的《皇明經世文編》五百零五卷,《補遺》四卷。九行二十字,小字單行,同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此外,長洲陳仁錫撰《經世八篇類纂》二百八十五卷等。
3.4 明代后期私家刻書質量不高
明代無實學,學術浮偽之氣甚重。在“重義理輕訓釋”的影響下,明代學者向傳統經學挑戰,開始疑經改經,由疑經進而刪改經書,使得古書失去原來面目。這就造成明代家刻之書在內容上任意篡改和刪削,在校勘上草率至訛誤甚多,刊刻粗制濫造。
3.4.1 刪節易名,改頭換面
嘉道學者黃廷鑒曾云:“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啟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14]
明人刻書經常改頭換面。如唐劉肅的《大唐新語》,馮夢禎刻本改為《唐世說新語》、《巖下放言》,郎奎金刻《釋名》,改作《逸雅》,把它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為一套,冠以《五雅全書》之名。胡文煥所刻《格致叢書》中之《洗冤錄》,“文理略同,殊多脫誤,且改易卷第。”
3.4.2 校勘草率,雕印粗劣
毛晉汲古閣所刻之書,所選底本雖然極精,但所刻之書錯誤甚多。清人孫從添批評說:“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好者亦僅僅數種”[15]。黃丕烈的《宋刻李群玉集跋》則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顧千里的《陸游南唐書跋》亦云:“汲古閣初刻《南唐書》,舛誤特甚。明人刻(唐)張說的《張說之文集》,脫文一篇,脫頁有二、漏行幾十處。”
1 冀叔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1):217-226
2(明)解縉.大庖西室封事,見王有立.御選明臣奏議.臺灣:臺灣華文書局,1968:87-88
3(明)顧炎武.日知錄集釋·書傳會選(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45
4 同上
5(明)李賢.薛公瑄神道碑銘.見(明)焦竑.獻征錄(卷十三).上海:上海書店,1987:433
6(清)龍文彬.明會要·學校下(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6:418
7(清)趙翼.陔余叢考·刻時文(卷三十三).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573
8(明)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714
9(明)黃宗羲.明儒學案·心齋語錄(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715
10(明)李贄.焚書·童心說(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99
11(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一百七十五(卷二百八十七)·中華書局,1974:7363
12(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答許廷綸(卷二十七).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172
13(明)王廷相.雅述·下篇.見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873
14(清)黃廷鑒.第六弦溪文鈔·校書說(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23
15(清)孫從添.藏書紀要.北京:中華書局,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