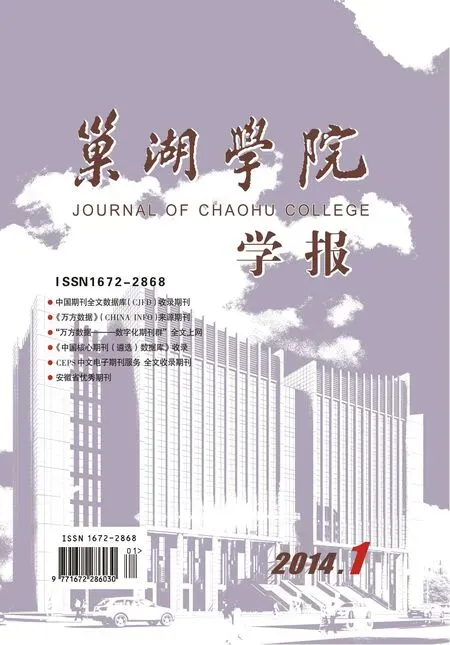論文學產業化與文學跨界發展
方習文
(巢湖學院,安徽 合肥 238000)
“文化產業”的興起,對于當下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影響,首先是建立了“文化的經濟化”與“經濟的文化化”的價值觀與方法論。曾經“物質”與“精神”對立與聯系的二元結構關系轉化為融合統一的關系。即便文學的生產,已不僅僅是作家靈感突發、天才閃耀的偶發機緣,或者僅僅是“我寫故我在”的主體性自我抒發,而是不得不面整個文化生產機制的制約與影響,通過與當下經濟、科技的有機融合,尋求自身的價值實現與發展之路。在這個過程中,“跨界發展”成為文學產業化轉型中一個重要的選擇與途徑。
1 產業跨界與作家身份
無論對于文化工業持有怎樣警惕與批判的態度,都無法改變一個文化消費時代的來臨與形成。文化生產機制與體制的變革,都對傳統文學生產和閱讀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就創作的主體性問題而言,“作者”是什么、“作者”是誰,出現了新的定位方式與解讀行為。生產和消費已經構成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生存景觀,而且它波及到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時空之中,文學受到的沖擊自然也不例外。傳統文學中“自我—寫作”、“寫作—審美精神”實現的單一價值模式轉向了“文學生產—文學消費”背景下,“作者”成為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雙贏實現的生產者與創造者。由此,作者的身份和存在方式發生了轉型:作者的主體性不斷受到削弱,來自外界他律性不斷增強,作者的精英性品質受到沖擊,作者的神圣性逐漸遮蔽,文學寫作將首先置身于文學生產的基礎之上。作品的生產、作者與讀者啟蒙與被啟蒙關系在市場經濟和消費時代里演變成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文學的發生直到文學的傳播的全過程,都受到“生產特性”的內在制約。“不僅藝術傳達具有生產性,而且藝術構思也具有生產性;不僅藝術創作具有生產性,而且藝術消費也具有生產性。只不過有物質性生產與精神性生產之別”。[1]
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種影響不止限于宏觀的文化消費環境與大眾審美走向,同時要將自身置于文化產業的體制與機制之中。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界定,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文化活動。其定義為“結合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等方式,運用本質是無形的文化內容。這些內容基本受到著作權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貨品或服務。”[2]文化產業的機制與體制,使文學寫作進一步受到資本市場的控制與左右。經濟效益與市場占有成為衡量一個作家與一部作品價值的重要尺度。出版商對于文稿的要求首先是考慮其潛在的經濟價值與商業價值,然后才會考慮其文化與社會價值。隨著文化體制改革,文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文化企業在保持自身傳播知識與文化、引領社會精神走向等傳統功能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效益與持續發展,構成運營管理的基本策略。在進一步挖掘“文學”資源與文學產品結構的同時,文學寫作將同時滲透資本運作者的動機與意圖。
“出版主導”置換“作家主導”,作家的“雇傭化”進一步消解作家“主體性”,作家產業跨界進一步改變作家觀念、習慣與寫作方式。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青年出版社和隨筆作家周洪合同簽約儀式在北京舉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作家被買斷與雇傭的首個市場案例。買方是中國青年出版社,賣方是隨筆作家周洪。合同嚴格規定雙方買賣關系的義務與責任:被買斷的周洪,在此后三年內必須在買方的整體設計下進行創作,買方不同意的選題,周洪無權染指。文學寫作的過程,置身于市場運作與策劃的生產性流程。這一流程包括作家人選,稿酬標準,配置作品中的暢想因素,包裝行為,發行時機等,甚至作品的具體標準和要求都標準化。在這個過程中,作品形態的模式化、作品內容的預定化、作品形式的類型化都使文學寫作滲透非文學價值與意義的“預設性”。產業跨界將使作家融入“產業團隊”,寫作只是產業生產的一環,作者只是一個特殊的生產者而已。
作家在產業跨界中,將成為具有雇傭性質的“寫手”或者具有利益共享的合伙人,作家本身也會成立自己的文化企業,實現作家向文化產業經營者的角色轉化。作家身份的變化,與其說傳統意義上的“作家死了”,不如說,這是文學發展史上一次新的革命。
文化產業是知識時代的主導產業。圍繞這一產業出現了相對獨立的文化產品行業如生產與銷售圖書、報刊、影視、音像制品等、以勞務形式出現的文化服務性行業如戲劇舞蹈的演出、體育、娛樂、策劃、經紀業等、以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業如裝潢、裝飾、形象設計、文化旅游等。在這樣的產業布局與空間中,傳統文學的位置與價值受到沖擊。這使得曾經借助紙質傳媒而身價獨顯的文學,在文化產業的發展趨勢中同樣必須通過產業跨界實施對接與轉型。這種對接與轉型,不止體現在文學生產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還包括參與產業創意與策劃,派生出服務于文化產業制造與服務的 “文學性”策劃書、宣傳品、廣告語、臺詞等一系列新的文體與文本。作家的智力、想象力、知識與技能融入產業生產與傳播流程。文學資源也將被文化產業深度開發。如作家故居與博物館的建立和開放、作家作為國家與地域“形象”宣傳與“形象消費”的重要資源、作家作為旅游產業宣傳與開放的對象,以及作家元素、作品元素被廣告業、旅游產品業利用與制造,都是文學產業化的具體體現。英國女作家J.k.羅琳憑借《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不僅制造了一個 “文學神話”,同時制造了一個財富神話。圍繞這部小說,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條。除了書籍和電影,DVD、電視片、游戲、服裝、文具,甚至哈利·波特主題公園、主題旅游都已經滲透于我們的生活,而這個產業鏈還在不斷地延伸、豐富。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產業化應該重新界定文學價值的存在方式,作家連同作品都可以通過產業跨界不斷開發存在形式與價值途徑。
這種情形不僅挑戰傳統文學觀念與方式,也使文化精英充滿憂慮。過度資本運作與效益追求也的確帶來文化泡沫與文化產品的魚龍混雜。“文化”與“資本”的角力和平衡將依然持續。但是文學跨界轉型的趨勢卻難以改變。從一定程度上說,文學產業化在不斷滿足人們精神消費與審美消費的同時,文學資源被更加多樣化與豐富化挖掘,文學的生產力得到釋放與提升,市場細分與開拓也不斷讓文學存在形態多樣化。同時文化市場競爭,在文化市場不斷規范的同時,容量的占有必向質量的提升推進。文化產業要做大做強,除了技術促動、管理先進、創新機制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內容為王”,文化產業最終是“內容產業”,“內容”是“以文字、音樂、圖片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思想與故事”[3]它是文化產品的靈魂。所以,在產業跨界的過程中,文學的精品優質價值追求不會輕易受降于文化資本市場的。
2 媒體跨界與文學生產
文學從來“不是一種‘客觀’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們去發現的永恒實體,而是各種復雜的社會文化力量的構建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構建的”。[4]這種 “力量”不僅來自特定時期的文化機制與體制,同時與特定時期科技的發展與進步息息相關。
文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每一次傳媒技術的進步,都對文學創作與文學生產帶來巨大的沖擊,引發文學的變革與轉型。文字與筆墨工具的出現,使口頭文學轉向了書面記載與書面創作;紙張與印刷技術的發明,使書面文學創作通過圖書事業得到廣泛的傳播與流通。而電子技術的出現,文學文本的存在方式從單一的紙質形態向多媒體形態轉型,聲音、影像、文字呈現融合生成趨勢。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數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文學的書寫方式、創作習慣、文本形式、傳播方式等,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動向與新氣象。一方面,文學向新媒體的跨界,出現了諸多新的文學形式,如網絡文學、短信/彩信文學、博客文學等;另一方面,互聯網傳播與數字移動以及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不僅使文學傳播具有自由度與影響力,同時,文學的生產方式、存在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革。復制、鏈接、媒體融合、電子生成等技術手段被廣泛使用于文學創作與文本存在之中。
就其要而言,網絡文學已經成為文學發展不可遏制的新的增長點,盡管網絡文學還存在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現象,但是,在這個平臺上,網絡寫手從娛樂交流到演變成文學市場巨大的淘金場,網絡文學由個人情感宣泄與意見表達到被網民接受被制造為明星寫手,甚至成為各大文學網站旗下簽約作家。這些寫手借助商業化運作,在取得巨大的知名度和商業利益的同時,同時也最大限度得促進了文學的發展,打破了傳統作家一統天下、也打破了在傳統機制體制下文學生產方式,拓展了文學發展的新空間。“網絡文學原來是對傳統文學構成挑戰,現在是拓展傳統文學的發展空間”。[5]業已存在的事實證明,所謂傳統寫作方式與傳播方式依然存在并獲得存在價值與意義,即如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在當下環境下傳統寫作方式依然可以獲得成功的典型案例。但是,對于文學而言,面對數字化生存就是面對文學發展的新空間,這同樣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莫言也承認,雖然傳統閱讀不會消失,但是“網絡文學、網絡閱讀就像網絡購物一樣,讓人感覺很方便,逐步發展到勢不可擋。將來文學閱讀的時間,會被網絡閱讀吃掉一大部分。再過十年二十年,傳統的紙媒閱讀肯定會縮成小小的角落”。[6]
無論這種格局的調整究竟如何,媒體跨界與文學生產的趨勢,并非徹底意味著傳統文學生產方式的消解與消失,相反,跨界合作的選擇,使原本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的對立狀態轉向了合作與融合。如2008年最具影響力的詩集《瓦礫上的詩》,有三分之二的詩作就來自民間詩人與網絡詩人,網絡詩歌這種自覺融于主流與人文精神追求,體現了網絡文學的調整與定位。一些文學網站網絡文學精英在網絡上擂臺大賽。它的意義在于傳統文學、主流文學、精英文學等力量在逐步摸索數字化生存環境下文學發展的新路徑與新模式。一些實體暢銷書作家也紛紛觸網,與中文網站簽約,將其作品拿到網絡上首發。同時網絡也成為文學新的評價方式,網絡文學入圍文學大獎或者文學大獎評選尊重網絡評價的結果,都是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交流互動的體現,這種體現,使得好的文學作品在獲得巨大傳播效應與社會效應的同時,也取得各方互贏的經濟效應。同時良莠不齊的網絡文學在互動中不斷提升審美品質與思想境界。
在市場運作的過程中,網絡文學的產業鏈由網絡收費閱讀延伸到實體出版、影視改編、網絡游戲改編以及衍生產品的制造。在網上躥紅同時在出版業獲得成功的例子可謂前赴后繼。另一方面,實體出版同樣向數字出版轉型,有的介入到網絡文學,有的自辦文學網站,很多網上作品出現火爆勢頭的時候,就被出版商簽約出版。對于出版社來說,網絡閱讀效應就是市場效應體現與潛在商業利潤;對于作者來說,可以以多種方式實現自身價值與知名度;對于讀者來說,獲得了更多的閱讀渠道與享用消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文學生產不能不受到利益訴求、市場運作、炒作宣傳等非文學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的負面性同樣十分明顯,如網絡文學的快捷化、速度化使創作在追求規模與速度的時候,可能忽視質量與品質的錘煉;網絡寫作在追求點擊率的時候,有娛樂化、膚淺化、炒作化等創作動因與設計,導致精品意識與先進性價值觀引導的缺失;文學創作受到資本市場的壟斷與控制,模式化與類型化寫作盛行,文學的自由寫作與多元化追求在并平衡的市場結構中處于弱勢發展地位。但是,這些問題都并不是文化市場固有的屬性,而是產業化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磨礪過程。市場的競爭與規范、持續發展的需要都將逐步形成比較合理化的生產體制、機制與經驗模式。
網絡文學的興起,的確有別于紙質傳媒傳播與消費環境下的寫作基本規律,包括創作觀念、寫作狀態與寫作方式、話語形式與風格、文體與文本形式等方面。文學網站、電子圖書與刊物、媒介融合傳播等,都是文學生產的新形勢。它們的文學史意義,以及在文學產業化方面活力都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不能因為網絡文學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而過度質疑與憂慮。須知中國的白話小說,當初就是從茶樓酒肆的說書行業形成口語文學與書面文學并行不悖同時花開兩枝的存在格局的,這也是互促雙贏的過程。真正值得思考的,倒是文學生產在數字化生存中,如何處理好文化引領與文化消費、精品制作與數字閱讀、媒介運營與媒介融合等關系的問題。
3 文體跨界與文學流變
“文體”,指“文學的體裁、體制或樣式”[7]。 作者在從事創作時,為達到既定的效用與目的,必然采取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形式、篇幅、組織結構等,這樣就使文學產生了不同的類別以及各種格局特征的文學體裁,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影視文學等幾大類文體。
以“審美性”為主要特征的文學文體從表面看似乎應該具有認知比較統一、模式比較明確的結構與語言特征。如詩歌與抒情方式、小說與敘事行為等。但是文體卻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即如文學文體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詩歌作為審美化抒情手段同樣可以敘事或者靈活運用敘事技巧,小說同樣有抒情小說、詩化小說、哲理小說等。只是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由于過度重視“本體性”與“主體性”構建,文體跨界與融合的問題似乎是異類與邊緣化問題。這就如同確立作家身份與作家價值一樣,通常以文體家作為衡量的尺度與標準。但是當下創作的趨勢則是:廣泛的、自由地活躍于各種文體之間的文體實驗和邊緣性話語,正在不斷探求問題內部奧秘和可能性的力量之源、文學發展和文學之美的力量之源。[8]這種文體跨界現象已經不是理論上是否成立的問題,而是值得關注與研究的實踐性問題。
當下的文體跨界寫作,有兩個趨勢。第一是作家成為文體多面手。即便像莫言這樣以傳統方式寫作、主要以小說家身份出現的作家,同樣會涉足影視、戲劇、詩歌、散文等多種領域。這與其說是作家才華的體現,作家以不同的文體寫作涉足的媒體領域與出版行業,顯示出靈動與活躍的姿態,不如說是文學生產需要對作家才華的煥發與塑造。也就是說,作家與文化產業的合作,會出現“產業運作”預定的內容與“文體”(其中不乏借文體炒作的嫌疑)。這些“文體”并非作家“面對自我”寫什么與怎么寫的問題,而是“必須如此寫”并如何寫好的問題。文體自覺受到消解。行業跨界合作、合作中的跨界寫作能力將進一步挑戰作家跨界寫作的能力,它不僅要求作家嘗試新的文體形式,同時要求作家應融合多種文體或者運用多種文體自由寫作的能力。個體性的自由創作將進一步摸索適應市場文化邏輯,文化媒介人的出現,將任何文化產品按照商品的實踐邏輯進行傳播與轉化,“作者”及其創作創作不得不“被建構”,文學生產首先得接受市場邏輯流程的認同與接受,包括前提市場調查、寫作主題設計與內容設計、語言風格與文體策劃、包裝與宣傳等。針對這種現象,阿多諾指出:“甚至逗樂的技術效果,幽默諷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設計出來的。它們都是由特定的專業人員管理的,而它們有限的多樣性也完全是由文藝機構編制的”。[9]
其次,文學文本的雜糅化與文體雜糅化。今天的文學文本呈現出多樣復雜的方式。其中一個重要的趨勢就是視圖化、視聽化、圖文化。這使得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形式的傳統文學文本被其他媒介文本重新編排與演繹,這些媒介變化與運用,實際上改變了原有文體結構與作品存在方式。一些既定文體模式會和文本形式所需要的文體結構或者構成元素雜糅合一。至于創作中的文體雜糅,已經成為寫作創新與文體實驗的一種自覺。韓少功將小說與詞書熔于一爐,創作《馬橋詞典》;劉震云將小說與戲劇融為一體,寫出《一腔廢話》;李洱將神話傳說、歷史考據、美術作品綴合一處,遂有《遺忘》……更有畢淑敏試手科幻題材,譜成《花冠病毒》;張煒試航兒童文學之域,推出《半島哈里哈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有相容度較小的文體也可以大步“跨界融合”,文體與文體之間的對立甚至沖突的邊界在消解并趨向互動兼容。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 “文體”與科學技術條件、社會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關。從口語傳播到手抄傳播、到印刷傳播直至出現電子傳播、網絡傳播、移動通信傳播等新的傳播方式與形態,每個階段都會產生相應的文體。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中談到“言”“文”“筆”等文體。“言”即是口頭傳播類文學,“文”即是詩歌抒情類文體,“筆”即是散文類文體。其中“筆”就是口語傳播階段和手寫傳播階段兩種文學形式兼容而產生的。中國古典小說的興起與繁榮曾經就是以市民文化消費為基礎、以口頭創作與傳播的方式(“說書”等形式)進行的,其文體特征就帶有滿足市民趣味、同時極大限度吸引觀眾的文體設計策略與話語策略。這些話語已經將詩歌、散文、敘述等文體因素有機融入其中,極大豐富話語資源與知識信息共享。隨著印刷業的發展與紙質傳播的條件改善,口頭文學的“話本”就單獨獨立出來成為書面閱讀的文本,“文人性”因素隨之增強,但是依然保留著貼近讀者、有效傳播的文體特征與功能。
當下跨媒介文學寫作更是一種寫作趨勢。它 “以其強大的技術優勢深刻地影響著寫作的特質和觀念,并對寫作的樣式、社會價值和美學形態進行新的整合與再造。換言之,21世紀的寫作也正因為站在了數字化時代所提供的網絡技術平臺上,才得以積極修改著既往的寫作觀念與陳規,主動改寫著寫作的知識地圖與技術經緯。”[10]譬如網絡文學,在一個由“信息環境”組成的“虛擬世界”面前,這個信息環境本身就越來越成為作家獲取創作材料和信息的另一個“世界”,這就使得作家“模仿、再現、表現、符號化、程序化”等出現了更為復雜的情況。一方面,寫作主體的個體生命存在價值在虛擬世界得到充分張揚,為寫作者進行多樣化的寫作也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但同時,同在現場的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使得創作不斷進行調整與轉換,話語的豐富性造成話語雜糅與混搭等美學形態,從而大大突破傳統意義上文體邊界與觀念范疇。
從寫作觀念上看,“虛擬世界”與 “影像世界”使傳統寫作要求的“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被消解,大眾文化消費需求與文化產業經營,也使得文體實驗與文體創新成為 “文化策略”與“商業策略”合謀的實踐性行為。一方面,寫作主體“獲得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間,并極大增強寫作主體表現世界的能力,最終增強作品的審美效果和藝術感染力。”[10]另一方面這些自由與想象的資源又不得不受制于接受者與消費者的習慣與需要。如同今天的“新聞”趨向“故事化”與“文學性”建構,而“文學”則更加關注“新聞性”,趨向“新聞化”。有學者就指出:“為了迎合媒體的口味,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在文體上與消息、通訊等新聞文體越來越接近,文學創作成了信息社會的文學消息”,“信息化寫作意味著文學的生產與傳播被逐漸納入新聞的生產與傳播體系,文學在藝術上的獨立性逐漸弱化,成為文化工業的產物”。[11]可以說,自古以來,沒有像當今這樣能對一切傳統文體及其內容進行深廣的改造和運用,媒體跨界成為文學新的生產方式。文體跨界與融合、新文體實驗、跨媒介寫作與跨文體寫作,都構成文學產業化背景下文學發展的新趨勢。
總之,文學產業化背景下文學跨界發展問題,將同步解構當下文學批評的慣有思維與定式,重建自身生產方式與知識體系。
[1] 譚好哲.文藝與意識形態[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237.
[2] 林拓,李惠斌,薛曉源主編.世界文化產業發展前沿報告(2003-004)[Z].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6.
[3] 張玉國.文化產業與政策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4] 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J].文學評論,2004,(6).
[5] 范昕,朱燕亮.我國網絡文學規模日趨龐大:“野路子”能否走正[N].文匯報,2009-08-07.
[6] 莫言.網絡文學稱其勢不可擋,傳統閱讀不會消失[DB/OL].
http://book.qq.com/a/20121012/000047.htmhttp://book.qq.com/a/20121012/000047.htm
[7]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1.
[8] 約稿信[J].大家,1998,(6).
[9] 阿多爾諾,霍克海默.啟蒙的辯證法[A].歐力同,等譯.法蘭克福學派研究[C].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117.
[10] 顧廣梅.數字化技術平臺上寫作觀念新論[J].東岳論叢,2007,(4).
[11] 黃發有.媒體制造[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