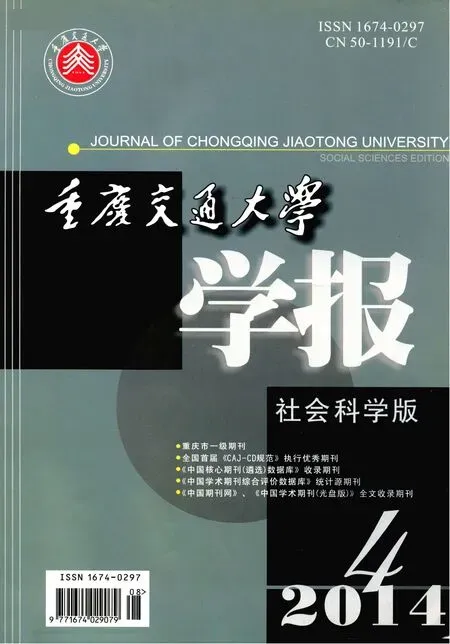辯訴交易制度的法理基礎(chǔ)
趙 馨
(上海交通大學(xué)凱原法學(xué)院,上海200030)
辯訴交易制度(Plea Bargain)從其誕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充滿爭議,但這一制度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絕不是偶然現(xiàn)象。辯訴交易制度是對公平和效率兩大價值之間的妥協(xié)和平衡,這兩大價值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是法理學(xué)學(xué)者們探討和論證的對象。本文從法理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出發(fā),試圖找尋辯訴交易制度的合理性所在。
一、辯訴交易制度的源起及發(fā)展
西方法律界在談到關(guān)于一個概念的解釋的時候,通常都會談到《布萊克法律辭典》。在他們看來,其解釋是最為權(quán)威和專業(yè)的。根據(jù)《布萊克法律辭典》的釋義,“辯訴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較輕的罪名或數(shù)項(xiàng)指控中的一項(xiàng)或幾項(xiàng)做出有罪答辯以換取檢察官的某種讓步,通常是換得較輕的判決或撤銷其他指控的情況下,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經(jīng)過協(xié)商達(dá)成的協(xié)議。”
一般認(rèn)為,辯訴交易制度起源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美國。當(dāng)時美國正處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和轉(zhuǎn)型時期,社會矛盾尖銳,犯罪率急速上升,為了能在有限的司法資源下及時、高效率地解決案件,辯訴交易制度由此催生。但從辯訴交易制度產(chǎn)生直至隨后的半個多世紀(jì)里,這一制度的實(shí)踐運(yùn)用一直處于“地下狀態(tài)”,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其態(tài)度也曖昧不清,直到20世紀(jì)70年代,在“布雷迪訴聯(lián)邦”(Brady v.United States,397 U.S.742)一案中,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才首次明確肯定辯訴交易的合法性。隨后美國在1974—1975年間修改了《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至此,辯訴交易才在美國司法上得到承認(rèn),從而作為一項(xiàng)訴訟制度確立下來。
在隨后的實(shí)踐中,辯訴交易制度在美國得到了快速發(fā)展。“在州和聯(lián)邦兩級,全部刑事案件中至少有90%沒有進(jìn)入審理階段。”由此可見,辯訴交易制度能夠明顯提高司法的效率,能夠大量節(jié)省人力、物力和財(cái)力,因而該制度在美國備受青睞,具有很高的適用率。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帶來經(jīng)濟(jì)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在英美法系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因其和美國較為相近的司法訴訟模式和實(shí)踐基礎(chǔ),這些國家廣泛借鑒了美國的訴訟交易制度。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陸法系國家,因面臨大量積案的沉重壓力,也開始逐步借鑒辯訴交易制度。有的國家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辯訴交易制度,但是在實(shí)踐中出現(xiàn)了為提高司法效率控辯雙方進(jìn)行適當(dāng)妥協(xié)和合作的情形。
二、辯訴交易制度評價
我國法學(xué)界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開始關(guān)注這一制度,特別是2002年的“孟廣虎案”作為我國第一例適用辯訴交易制度的案件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之后,引發(fā)了新一輪對該問題研究和探討的熱潮。
(一)肯定說
對辯訴交易制度持肯定態(tài)度的學(xué)者們認(rèn)為:第一,辯訴交易制度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使案件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得到解決,同時也提高了判決的確定性,節(jié)約了司法成本。對被害人來說,可以減少訴累,迅速結(jié)案,意味著被害人能夠盡快得到賠償和心理上的撫慰;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避免了審判給被告人帶來更多的負(fù)面影響,有利于其回歸社會[1]。第二,這一制度充分尊重了當(dāng)事人的主體地位及處分權(quán),體現(xiàn)了訴訟的民主性,是對人權(quán)的保護(hù)。第三,公正有很多層次,有最高層次、較高層次、一般層次、較低層次和最低層次的公正,辯訴交易制度尋求的是一種相對的公正,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2]。
(二)否定說
理論界不乏對辯訴交易制度持反對觀點(diǎn)的學(xué)者,他們認(rèn)為辯訴交易制度是一場災(zāi)難,呼吁應(yīng)該廢除這一制度,理由在于:第一,公平和效率均是法律追求的價值,不應(yīng)該為了實(shí)現(xiàn)效率的目標(biāo)而損害公平,辯訴交易將效率置于公平之上,不利于正當(dāng)程序的實(shí)現(xiàn),是以正義的犧牲換取效率。第二,辯訴交易違背了罪行相適應(yīng)原則,違背了實(shí)事求是的原則,可能會導(dǎo)致同案異判的結(jié)果。第三,辯訴交易可能會滋生腐敗,引發(fā)權(quán)錢交易,并不能實(shí)現(xiàn)制度設(shè)計(jì)的初衷。
三、辯訴交易制度的法理基礎(chǔ)
綜觀我國現(xiàn)階段的研究狀態(tài),對辯訴交易制度的探討多集中在刑事訴訟法領(lǐng)域,對于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考并不充足。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證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礎(chǔ),甚至大膽建議在我國未來的刑事訴訟法發(fā)展中可以有條件地借鑒這一制度。
(一)正義的時效性
從理論的層面來看,正義的時效性是關(guān)于公平和效率這一法理學(xué)界永恒的主題所做的回應(yīng),這里不得不提及經(jīng)濟(jì)分析法學(xué)對這一問題的見解和思考。法律經(jīng)濟(jì)學(xué)是近40年來發(fā)展起來的,但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方法研究相關(guān)法律問題,則可以追溯到邊沁和亞當(dāng)·斯密。邊沁在他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dǎo)論》一書中寫到:功利原理是指按照勢必增大或減少利益有關(guān)者之幸福傾向,亦即促進(jìn)或妨礙這種幸福的傾向,來贊成或非難任何一項(xiàng)行動[3]。邊沁強(qiáng)調(diào)法律構(gòu)建要以功利主義為基石。亞當(dāng)·斯密更是很早就開始運(yùn)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整個社會的活動。但是經(jīng)濟(jì)分析法學(xu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波斯納,他認(rèn)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實(shí)施過程中的經(jīng)濟(jì)耗費(fèi)是評價和設(shè)計(jì)法律程序時應(yīng)考慮的重要價值,也是司法活動應(yīng)達(dá)到的價值目標(biāo)。正是基于這樣的觀點(diǎn),波斯納曾經(jīng)說過“正義的第二個層次就是效率”。
誠然,公平和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價值。但是法的價值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發(fā)展,其他的價值如自由、秩序、效率等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正是出于對效率價值的考量,我國《民事訴訟法》2013年的修改中,增加了關(guān)于小額訴訟程序的規(guī)定。辯訴交易制度能夠在合理的范圍內(nèi)平衡公平和效率兩種價值,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增進(jìn)整個社會的財(cái)富。
從實(shí)踐來看,近年來趙作海案、佘祥林案引發(fā)了學(xué)界關(guān)于刑訊逼供、程序正義的熱烈討論,雖然最終他們得以沉冤昭雪,獲得清白,但是如果能關(guān)注一下這些冤假錯案的當(dāng)事人的后續(xù)生活,就會發(fā)現(xiàn)“遲來的正義”是多么的辛酸。實(shí)踐已經(jīng)用殘酷的事實(shí)告訴我們,正義是有時效性的,雖然正義不會缺席,雖然正義終有實(shí)現(xiàn)的一天,但是這種遲到的正義背后是巨大和慘痛的代價。
正義在不同的時空中會改變其內(nèi)容,但也有其不變的內(nèi)容,即正義有一個底線,這個底線是文明的人類社會所共同具有的,不具有這些底線的社會就不是文明社會。在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案件急速增加、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將正義和效率在底線之上進(jìn)行平衡,也是正義本身包含的應(yīng)有之義。辯訴交易制度能夠及時地將犯罪與刑罰進(jìn)行相符合的搭配,及時地了結(jié)案件,盡可能減輕當(dāng)事人的痛苦和負(fù)擔(dān),對于正義的實(shí)現(xiàn)具有重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效率對維護(hù)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秩序也就意味著正義是否能更好地實(shí)現(xiàn)[4]。
(二)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事人的主體性,尊重契約自由
辯訴交易是在實(shí)質(zhì)上達(dá)成的一紙合同[5]。在辯訴交易的合同中,控辯雙方各自進(jìn)行了退讓和妥協(xié),辯方放棄對自身無罪的辯護(hù),主動承認(rèn)自己的罪行,以求控方放棄或減輕控訴。控方放棄對辯方嚴(yán)厲甚至苛刻的指控,換取證據(jù)的主動出示和案件的及時審結(jié)。在這一過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辯訴交易是對控訴雙方主體地位平等的承認(rèn),沒有主體的這種平等性,契約和契約精神無從說起,這是現(xiàn)代社會民主自由和人權(quán)保障的象征。出于自然法,每個人對一切都有天然權(quán)利,凡是涉及保護(hù)自己生命和與此關(guān)聯(lián)的手段的一切都屬于個人所擁有的天賦權(quán)利[6],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在訴訟中不再僅僅處于被動地位,其有權(quán)處分自己的權(quán)利,與控方進(jìn)行理性的對抗。
否定說的學(xué)者們會就此提出質(zhì)疑,刑事犯罪是對國家法益的侵害,在我國檢察官是代表國家對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出控訴,在刑事訴訟中雙方不是基于平等地位,并且檢察官享有的是國家公權(quán)力賦予的權(quán)利,履行的是國家公權(quán)力賦予的義務(wù),這種權(quán)利義務(wù)并不能由其隨意妥協(xié)和放棄。在傳統(tǒng)的刑事訴訟理念以及糾問制的訴訟模式下,很難說控辯雙方處于平等的位階,但是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民主自由人權(quán)等觀念深入人心,再加之兩大法系之間的融合及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廣泛,大陸法系的訴訟模式也開始向當(dāng)事人主義轉(zhuǎn)變,控辯雙方的地位不再是絕對意義上的不平等,雙方地位漸趨平等。此外,隨著任何人不受強(qiáng)迫自證其罪特權(quán)、無罪推定、武器平等、公平對抗等現(xiàn)代刑事訴訟理念的確立,為檢察官與刑事被告人之間達(dá)成合意、形成契約提供了現(xiàn)實(shí)可能,在市場經(jīng)濟(jì)浪潮的沖擊之下,辯訴交易制度也就應(yīng)運(yùn)而生[7]。
在辯訴交易中,控辯雙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相互妥協(xié)和退讓,交換彼此的風(fēng)險(xiǎn),就控方而言,交換的是指控可能不成立、真正犯罪人無法得到懲罰、案件因此擱置的風(fēng)險(xiǎn);就辯方而言,交換的是辯護(hù)可能無效、受到嚴(yán)厲判決的風(fēng)險(xiǎn),控辯雙方在平等的地位和理性的思考之下進(jìn)行這樣的風(fēng)險(xiǎn)交換,以期實(shí)現(xiàn)“共贏”[8]。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我國都承認(rèn)了私力合作的協(xié)商模式。除了這種私力的協(xié)商和合作模式,還有“協(xié)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存在和發(fā)展的可能。所謂協(xié)商性的公力合作,是指被告方與刑事追溯機(jī)構(gòu)通過協(xié)商、妥協(xié)來決定被告人刑事責(zé)任的訴訟模式。在這種帶有“協(xié)商”或者“交易”成分的活動中,刑事追訴機(jī)關(guān)和嫌疑人為了避免出現(xiàn)更為不利的訴訟結(jié)局,最大限度地獲得訴訟收益,不得不放棄訴訟立場上的對立,而進(jìn)行基于“理性人”假設(shè)的訴訟合作[9]。
由此可見,從本質(zhì)來看,辯訴交易是在現(xiàn)代法律理念之下作為平等主體的控辯雙方在自由意志和平等地位下達(dá)成的契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基于自己的意志放棄權(quán)利以換取利益,是“自由”價值的體現(xiàn),是其主體地位的體現(xiàn)。在實(shí)踐中這一契約如何實(shí)現(xiàn)最大化的平等互利,如何避免辯方不被強(qiáng)迫和威脅還需要更多的制度設(shè)計(jì)。但是基于契約自由的觀念和對當(dāng)事人主體地位的尊重,我們不能否認(rèn)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三)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下的現(xiàn)實(shí)的司法公正觀
美國社會是一個極其強(qiáng)調(diào)效率、目的、創(chuàng)新和實(shí)用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壞并不是以歷史和傳統(tǒng)為標(biāo)準(zhǔn),而是以是否有用為標(biāo)準(zhǔn)。在同英國殖民統(tǒng)治作斗爭的過程中,這種思維方式漸漸成為一種哲學(xué)思潮: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觀[10]。
這種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觀滲透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經(jīng)常會聽到這樣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jīng)驗(yàn)”,這句話出自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實(shí)用主義法學(xué)觀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實(shí)用主義法學(xué)觀主要是把法律理解為“于社會方便的東西或當(dāng)前社會需要的東西”,即法律人的視野不能僅局限于法律的書本和僵硬的信條,法律是在社會中加以適用的,必須與社會生活結(jié)合起來,必須要能夠解決社會的實(shí)際問題,與社會的需要保持一致和協(xié)調(diào)。在這種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觀的影響和支配下,人們進(jìn)行相關(guān)活動或者制度設(shè)計(jì)的時候,會從實(shí)際情況出發(fā),爭取目的能夠得到最大化的實(shí)現(xiàn)。辯訴交易制度的恰當(dāng)運(yùn)用的確可以平衡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沖突,最大化地實(shí)現(xiàn)刑事訴訟的目的。
同時,在這種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下,人們對于傳統(tǒng)的正義觀進(jìn)行重新審視,以往的正義觀是一種理性意義上的正義觀,要求尋求絕對的真實(shí),實(shí)現(xiàn)絕對的正義。辯訴交易制度常被人們稱為“半塊面包”,在不采用辯訴交易的情況下,提交審判可能會喪失“整塊面包”,但采用辯訴交易至少可以得到“半塊面包”,這正是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的觀點(diǎn)。將正義從絕對化的理想主義轉(zhuǎn)換為現(xiàn)實(shí)主義,結(jié)合我國現(xiàn)有的實(shí)踐,我們的正義觀也需要實(shí)現(xiàn)這樣一個轉(zhuǎn)變。博登海默曾經(jīng)指出:“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當(dāng)我們仔細(xì)查看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于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時,我們往往會深感迷惑。”辯訴交易雖然不能實(shí)現(xiàn)絕對的正義,但是比起案件堆積、放縱罪犯而言,最起碼實(shí)現(xiàn)了相對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上的正義。從這個意義來說,其實(shí)辯訴交易是在絕對正義不能實(shí)現(xiàn)的時候退而求其次,追求相對的正義,其實(shí)質(zhì)是放棄過于理想化的絕對公正,轉(zhuǎn)而追求更加現(xiàn)實(shí)的相對公正[11]。
(四)兩大法系的融合
根據(jù)法的歷史傳統(tǒng)來劃分,現(xiàn)有的主要法系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法系之間存在一些區(qū)別,從國內(nèi)現(xiàn)有的法理書以及學(xué)者的研究來看,這些區(qū)別集中在兩大法系的法律淵源、法律編纂、法律思維、法律分類、訴訟模式以及法律教育模式上。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兩大法系的區(qū)別一直被學(xué)者們強(qiáng)調(diào),特別是在法律移植領(lǐng)域,很多制度因?yàn)槭怯⒚婪ㄏ邓赜械模谖覈闹贫仍O(shè)計(jì)中以該理由被否決。
同樣,在對我國辯訴交易第一案“孟廣虎案”以及我國未來的刑事訴訟是否要引入辯訴交易制度的思考中,持否定態(tài)度的學(xué)者們再次提及上述理由[12]。的確,辯訴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國,當(dāng)事人的訴訟主義模式是其制度基礎(chǔ)。兩大法系的發(fā)展過程雖然各不相同,有各自獨(dú)特的特點(diǎn)和差異,但是兩大法系在世界法律文明的進(jìn)程中不是各自為營、相互獨(dú)立的,兩者一直在不斷地相互借鑒、相互滲透和相互交融,尤其是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和深刻的今天,這一趨勢顯得更為明顯:判例在大陸法系國家越來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英美法系國家中制定法的地位也得到提升;在教育模式上,兩大法系的交易模式開始各取對方之長,特別在大陸法系國家,開始注重對學(xué)生實(shí)務(wù)能力的培養(yǎng);在訴訟模式上,兩大法系有相互靠攏的趨勢,我國在訴訟中賦予當(dāng)事人更多的權(quán)利,越來越重視程序的意義,要求法官保持中立。這些都證明了我國的訴訟模式已經(jīng)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職權(quán)主義模式。兩大法系的融合給我們的啟示是法律移植固然要考慮本土因素,但是這種考慮應(yīng)該是理性的而不是僵硬和教條主義的。并且我們面臨著與美國同樣的情況:大量的刑事案件與有限的司法資源的矛盾;我們與美國有著同樣的追求:希望在實(shí)現(xiàn)司法公正的同時提高司法的效率。
(五)程序正義的再解讀
對辯訴交易制度持反對觀點(diǎn)的學(xué)者們認(rèn)為辯訴交易制度為實(shí)現(xiàn)效率犧牲了正義。如果在刑事訴訟中實(shí)行辯訴交易,違背了正當(dāng)程序的要求,有損程序正義和實(shí)事求是的原則。筆者認(rèn)為,這是對程序正義內(nèi)涵的錯誤解讀。
司法能夠追求和實(shí)現(xiàn)的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真實(shí),法律意義上的真實(shí)是程序意義和程序范圍內(nèi)的真實(shí),這兩種真實(shí)有時候可能是重疊的。但是這種一致性只是偶然的,大多數(shù)時候,程序意義上的真實(shí)和客觀的真實(shí)存在矛盾。因此,把實(shí)事求是原則無條件地適用于司法領(lǐng)域,這本是司法浪漫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13],不是程序正義的應(yīng)有之義。
首先,程序正義的原則之一是保障訴訟當(dāng)事人平等的訴訟權(quán)利和訴訟地位,賦予當(dāng)事人的訴訟參與權(quán)。前文已經(jīng)論述,辯訴交易制度是對當(dāng)事人主體地位的承認(rèn),尊重當(dāng)事人的理性和權(quán)利選擇,此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再是被動的訴訟參與者,而是有機(jī)會充分參與訴訟,并對訴訟的結(jié)果施加影響。其次,程序正義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超然的態(tài)度,在訴訟中不偏不倚,公正對待訴訟雙方當(dāng)事人,這是程序正義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訴訟職權(quán)主義被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批判的原因所在。最后,我們承認(rèn)辯訴交易可能會引發(fā)潛在的不公正,甚至是司法腐敗,但是任何一項(xiàng)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這些問題可以通過相關(guān)配套的制度設(shè)計(jì)來解決。美國的司法實(shí)踐已經(jīng)證明了,只要有完善的制度設(shè)計(jì),這一制度所帶來的積極影響遠(yuǎn)遠(yuǎn)大于潛在的消極影響,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由此可見,辯訴交易重視程序正義,以法律程序?qū)崿F(xiàn)看得見的正義[14]。同時,辯訴交易也重視司法效率和司法成本,這一制度的設(shè)計(jì)不是在摧毀程序正義,相反是為了程序正義能夠得到更好、更有價值的實(shí)現(xiàn)。
四、結(jié)語
辯訴交易制度從其產(chǎn)生的那一天起,人們對它的看法就各不相同,充滿爭議。在近一個世紀(jì)的司法實(shí)踐中,司法機(jī)關(guān)已經(jīng)認(rèn)識到了其價值所在。辯訴交易制度在美國已經(jīng)得到合法化的確立,并且在刑事訴訟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2013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中規(guī)定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在一定條件下,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現(xiàn)的,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附條件地不起訴,這和辯訴交易制度的內(nèi)涵在某些方面有重合之處。
本文從法理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闡述辯訴交易的法理基礎(chǔ),為辯訴交易制度的存在尋求正當(dāng)性。在我國未來的刑事訴訟發(fā)展中可以有條件地引入這一制度。正如龍宗智教授所言:正義實(shí)現(xiàn)必須付出代價。無價的、至上性的正義只是存在于觀念形態(tài)中。而塵世中即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的正義則是有價的正義[15]。辯訴交易制度正是正義實(shí)現(xiàn)過程中適當(dāng)?shù)耐讌f(xié)與利益的合理讓渡,以最終尋求到正義和效率的平衡點(diǎn)。
[1]劉濤.辯訴交易制度研究[D].沈陽:沈陽師范大學(xué),2011:12.
[2]陳光中.辯訴交易在中國[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3.
[3](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dǎo)論[M].時殷弘,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58.
[4]徐超.辯訴交易的法理探析[D].昆明:云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2011:14.
[5]盛斌.利益的權(quán)衡與選擇——淺談司法交易制度在我國的適用問題[C]//第九屆國家高級檢察官論壇論文集.2010:1-11.
[6]陳宇.近代自然法學(xué)說和社會契約論[J].重慶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0(6):41-44.
[7]劉方權(quán).刑事和解與辯訴交易[J].江蘇警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7):78-85.
[8]劉曉梅,于陽.辯訴交易制度與刑事和解制度的“斷裂”與“彌合”[J].天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10):40-44.
[9]陳瑞華.司法過程中的對抗和合作——一種新的刑事訴訟模式理論[J].法學(xué)研究,2007(3):113-132.
[10]汪建成.辯訴交易的理論基礎(chǔ)[J].政法論壇,2002(12):14-18.
[11]高珊琦.辯訴交易制度移植之障礙分析[J].法律科學(xué),2008(5):134-142.
[12]李建明.辯訴交易與正義保障[J].江海學(xué)刊,2003(3):123-129.
[13]王亞新,張衛(wèi)平,陳興良,等.邁入法學(xué)之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71.
[14]汪睿.辯訴交易中國化的可行性分析[J].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4):103-104.
[15]龍宗智.正義是有代價的——論我國刑事司法中的辯訴交易兼論一種新的訴訟觀[J].政法論壇,2002(1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