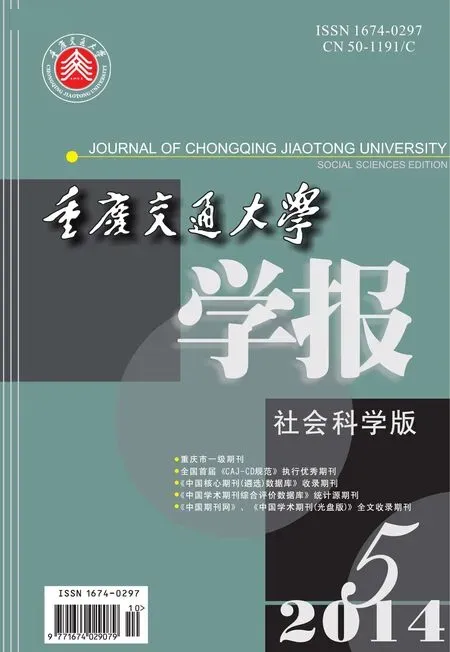儒學的超道德境界探析
郭德君
(重慶醫科大學,重慶 400016)
一、以倫理為本位使儒學的發展保持了超越性連續
儒學的產生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由此形成了和西方哲學迥然不同的風格。先秦儒學具有強烈的入世情結和無神論色彩,正如孔子所言:“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高度注重人生和現世的特征與孕育儒學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系,發源于內陸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屬于典型的內陸農耕文明,儒學因而形成了以重視家庭血緣關系、宗族倫理秩序和強調對祖先的絕對崇拜為顯著特征的思想文化體系。儒學中的“孝”“悌”之義就是此特征的具體反映:“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孟子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孝”“悌”便成了博愛的道德基礎,“仁”則是涵蓋這些哲學思想的總體文化外現,因此,先秦儒學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非常關注人倫理秩序的和諧,這是先秦儒學倡導“修齊治平”人生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和歷史文化背景。從高度注重“邏各斯”精神的西方哲學視角來看,先秦儒學具有更多的倫理學特征,其重要經典之一《論語》更像一部倫理道德手冊。受儒學的重要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許多大一統朝代,統治階級紛紛選擇儒學作為官方哲學,他們不僅推崇“仁”的治國理念,而且把“三綱五常”等道德原則固定化,這些價值原則一直是維系封建社會穩定的重要思想價值體系。
在中國罕見的大分裂和大黑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頻繁的政權更迭使這一時期中華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的影響,其突出表現是玄學的興起、佛教的快速發展、道教的勃興等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因而這一時期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以及傳統儒學的發展等問題也趨于復雜化。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以后,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貫具有的深沉歷史責任感促使他們肩負起了重構儒學的偉大使命,宋明理學就是在這一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儒學出現了和西方哲學或倫理學完全不同的發展路線,它并不是在形而上的層面對道德法則的依據進行廓清,而是先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其后才被賦予了形而上的終極含義。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為代表的儒學大師,成功地回應了佛、道等思想帶來的巨大挑戰,在吸收這些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理”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從而成功復興了儒學。發展到南宋,朱熹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理學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但是,理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構建一種單純充滿思辨性的理論體系,而是當時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和道德危機發動的一場積極的文化攻勢。不僅如此,從自身的理論演進、具體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因素等宏觀視角來看,心學與理學在許多方面也保持了一種超越性的連續。理學中的“理”是一個位于超驗世界的目標,但是僅僅靠格物致知的認知方式無法有效實現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統一,為了克服主客的二元對立,心學將“理”放在了人的心中,格物由此變成了格心。從道德實踐的角度來看,由格物向格心的重大轉變更加凸顯了個人的主觀精神和意志。道德行為的出現不單單是因為遵循道德規范的結果,更是發自個人內心的本然要求,是人天然本性自然顯現的過程。因此,社會道德的內容并不是人可以創造出來的生硬的教條規范,而是源自具有倫理本性的個體之心,這樣認識論與修養論便在以心為本體的心學體系中達到了有機的統一。
因此,以倫理為本位,以普世主義的價值作為最高原則并使其與社會的發展模式保持高度整合,是儒學內在結構呈現連續性演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在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儒學的理論形態愈來愈復雜,但其核心的價值并沒有弱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其價值功能反而有進一步增強的趨勢,儒家思想內在的演繹過程和整體發展脈絡由此得以呈現,這也是了解儒學核心思想和價值原則的關鍵所在。
二、儒學關注的根本是超道德的境界
由上所述,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使儒學的核心價值追求一直保持了一種內在的連續性,注重人自身和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則使儒學有了濃厚的入世情結,宋明理學對終極境域的關注事實上是建立在維護儒學基本倫理道德法則的需要之上的。但是,由此就認為儒學僅僅是一種道德哲學是一種片面的、不客觀的觀點。因為儒學追求的人生境界不僅僅限于道德境域,而是包括了道德境域的更為宏闊的境界①。馮友蘭先生曾說:“中國哲學有一個主要的傳統,有一個思想的主流。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高的境界。”[1]因此,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便成了儒學家畢生努力去實現的最高理想。理想人生境界實現的一個基礎就在于人自身首先要達到至高的修養,在此基礎上實現有效的社會價值才能成為可能。儒學內圣外王的追求決定了人不單單需要“格物致知”等認知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正心誠意”“主敬涵養”等深刻的生命體驗,在此基礎上方可做到知行合一。
在提高個人修養的過程中,儒家世界中更深刻的體驗逐步得以顯現,人一旦達到這樣崇高的境界,就會超越物質欲求。“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貧賤當然沒有什么好樂的,但為什么一般人都不能忍受的貧困憂患不能改變顏回的快樂呢?程頤曾和他的門人討論過這件事:“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氏外書·卷七》)在程頤的視角中,顏子所樂顯然超越了道的范疇,他認為如果顏子真是樂道而已,那他就不是顏子了。顏子所樂的是什么呢?道既然不是樂的對象,這里的樂就是一種神秘的類似李翱所講的“寂然不動”的深刻體驗。如果勉強要用語言來表達,也許說的就是人與道為一的境界。事實上,在儒學家的內心深處,他們有著更為深沉的生命體驗,這種體驗實際上超越了比道德境界更為本源的領域。在這個境界中,圣人與天地星辰融為一體,表現出一種極高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境界與其說是崇高的宇宙領會,不如說是完美的生活體驗。在超道德的境界中,人了解社會萬象,洞悉宇宙的真諦。達到這一修養境界的人擁有一個更為廣博的胸懷和更為高尚的品質,真正可以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是真正的天之驕子[2]。因此,顏子之樂是一個既不脫離世俗生活,情志又超乎物外的至高的超道德境界。在此境界中,人與萬物相融,精神極度自由,道德原則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得以實現。
超道德的宏闊視閾使得中國的哲人對生命和生活本質有著更為深沉的思考,并給予了深刻的、滲透著相當濃厚生活氣息的哲學解答。孔子和弟子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這段精彩而深刻的對話在闡釋了孔子基本政治理想的同時,映襯出孔子追求一種能充分顯現自己個性的理想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模式中,孔子孜孜以求的自由、暢適的精神生活,即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實現。因此,詠而歸的超脫精神境界是人內在氣象的自然展現,這種境界已經超越了道德本位、社會關懷、文化憂患等較為狹隘的層面,達到了一種悠然自得、與天地萬物上下相融的狀態,從而進入到一種極高的人生境界。這種具有自己獨立心性見解和自由人生態度的生存方式遠遠超出了常人的境界,也被稱為圣人境界。但是,悠然自適的精神狀態并不是指人應自然順勢、消極無為,而是在對世事有深刻的洞悉之后所達到的一種極度自由的精神狀態。因此,自信、樂觀的生活態度和自強不息的人生追求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人來到世上,必須要展現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必須要以堅韌不拔的超人毅力去踐行自己的生活目標和人生理想。當然,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冥冥之中的“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當人盡了己力之所及后把事情的成敗歸結于“命”,這并不是一種消極的宿命論的思想,而是將執著的堅持和勇敢的放棄并行不悖地統一起來,執著的堅持是一種智慧;適時的放棄是一種更高的智慧,展現出經歷了世事滄桑后一種非凡的生活睿智和達觀主義的人生態度。
三、儒學超道德境界出現的深層原因分析
由上所述,以倫理為本位、注重人倫關系是儒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儒學發展的一個持久動力。但是,儒學關注的對象不僅僅局限于道德領域,而是追求一種更高的、精神極端自由的境界。儒學對生活和生命本質深刻體悟的目的不單單是倫理性質,而是在于提煉高度的智慧,以達到一種至高的人生境界。
儒學中超道德境界出現的一個重要基礎在于中國哲學中獨特的“天人合一”思維②。雖然“天人合一”的概念是張載明確提出的:“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正蒙·乾稱》),但是中國遠古的先民很早就形成了從宏觀整體去把握事物的方法論和形象思維,在儒學的早期經典《易經》中就以陰陽五行、取象比類以及形象化方法去認識對待周圍世界,從而凸顯出中國傳統哲學主客不分的獨特思考方式。在這種思維模式中,天、地、人并沒有看作是完全對立的兩極,而是在陰陽流轉中自然地統一起來。《周易》中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中庸》亦闡述了至誠盡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認為“萬物皆備于我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因此,早期儒學中“天人合一”的思維對人生存狀態和宇宙生成模式進行了整體性的闡述。之后的宋明理學大師更是從異常宏闊的視閾中來審視人和天地萬物的構成關系,不僅人與天地諸物息息相通,而且人的存在價值也是在天地萬物的整體關系中顯現出來的,道德責任因而也是人必須要勇敢承擔的義務③。這種精神境界集于張載所著的《西銘》中:“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賜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載突破了狹隘的世俗之愛的界限,而是將其推及到了宇宙萬物之間,這種綻放宇宙大愛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訴求不僅是對宋儒哲學內核的高度概括,也彰顯出中華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和永恒的魅力。程顥也曾不無自豪地說過,雖然其學說受到別人思想的影響,但“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因此“理”是理解二程以及朱熹理學思想最為重要的哲學范疇。在程朱理學中,萬物通過“理”彼此聯系起來,天人一理,這事實上是“天人合一”思維在具體哲學思想體系中的另一種形式表達。
“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更多需要的是生命體驗,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主體與客體完整地統一起來,天、地、人被納入到一種多維度的整體關系之網,主體自然而然地融入到這種整體的大系統中。這種認識從本質上來說并不完全是一種反映與被反映的簡單過程,而是需要更多內心深刻的精神體驗,這是中國哲學一個獨特的認識域構成。通過深刻的生命體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領域才可相互貫通,宇宙論和價值論才能密切結合,因此,深刻的內心體驗使儒學中的認知主體具有了先驗性的傾向,不僅在認識宇宙的最高本體的時候,就是在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過程中亦是如此。儒家經典《大學》中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一條修身的路徑。《孟子》中亦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程朱理學則進一步轉向內心,強化了人的內省直覺。程頤曰:“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發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程氏外書·卷十一》)朱熹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遍,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朱子語類·卷五》)由此可看出,和先秦儒學保持一致,程朱理學將成就理想人格的基點建立在了自我身心的基礎上,由內而外的自省自察的認知路徑和自我價值實現方式導致儒學更多賦予了理想人生境界以精神層面的含義。陸王心學更是將心的本體作用發揮到極致,王陽明格竹七日以致勞思致疾后,“方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圣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傳習錄下》),以心為本體可以說是整個心學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因此,從先秦儒學到程朱理學再到陸王心學,都非常注重而且逐步強化了人的內心體驗,在此基礎上再創建使人心有皈依的價值體系,這就是極富魅力的中國儒學的一個獨特的認知視角。
深刻的內心體驗之所以能發生,與儒學對“天”“道”“理”等哲學范疇獨特的釋義有密切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在傳統西方哲學中,人們把自然僅僅看作是認識和改造的對象,由此邏輯的和知識化的哲學得到了自身發展的對象;而在中國哲學中,對“天”等概念的獨特理解使人們獲得了倫理價值和感情的依托,由此可以建立依靠外在力量的價值體系和理想人格范型。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上的差異,與西方傳統哲學中“天”等概念被單純地賦予了自然方面的含義不同,在中國哲學中,“天”等概念包含了多重性,不僅指自然現象,也有宇宙的本源、至高無上的權威等不同含義,但更多包含了倫理道德方面的內涵或使其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論語》中多次談到了“天”“道”以及與之相關的概念:“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五十而知天命。”(《論語·學而》)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論語·公冶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公冶長》)“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恥也。’”(《論語·憲問》)“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在宋明理學中,“理”等形而上的哲學范疇所具有的倫理特質更大于本體論方面的含義。它們并不只具有形而上的終極含義,因為儒學大師們主要不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構建這些范疇的,而是從價值論的層面使理想道德境界的實現有可靠元倫理學的依托而闡釋這些概念的。這樣,人進入無限自由的精神境界才有了可能,至少有了邏輯上的可能。由上面的分析可看出,儒學思想體系中獨特的“天人合一”認知方式以及對人生存狀態和宇宙生成模式的整體性解釋,高度注重人的內心體驗,對“天”“道”“理”等概念給予了多重性的釋義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才使得儒學所追求的超道德境界的出現有了可能。
注釋:
①境界一般指主體的精神感受,境域一般指客體存在的范圍,二者有密切的依存關系,因為主體的心靈感受、精神狀態一般以對客體的感知為基礎,人生境界并不能脫離生活境域而獨立存在,故在此將道德看成了客觀存在現象的一部分而用了道德境域一詞。
②“天人合一”不僅是一種獨特的認知方式,也是一種至高的人生境界,即和本文中論述的超道德境界是等同的,但是本文探討的是這種超道德境界何以出現的深層原因,因此此處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理解“天人合一”的。
③對比來看,西方哲學在古希臘時期就存在著主客不分的思維,將人與自然看成是息息相關的整體。但是,詳盡闡釋這一構成模式卻是在20世紀的存在主義等哲學思想中,海德格爾就認為,此在的基本建構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雖然如此,海德格爾依然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來闡釋此在的基本建構的,此在并沒有倫理學方面的深層含義。因此,通過這一對比更能顯現出理學大師思維的超越性。
[1]馮友蘭.三松堂全集[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573.
[2]王曉興,李曉春.宋明理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