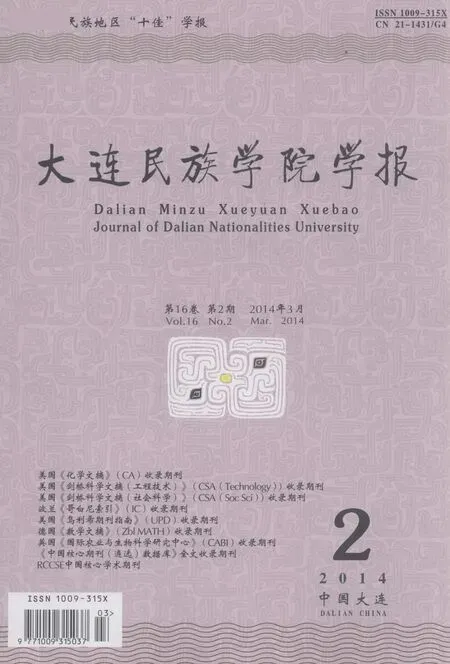蒙古族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研究
王福革,王續增
(內蒙古民族大學政法與歷史學院,內蒙古通遼028000)
蒙古族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研究
王福革,王續增
(內蒙古民族大學政法與歷史學院,內蒙古通遼028000)
通過天與人、人與神以及人與英雄等范式的哲學研究,揭示了蒙古族哲學的思維路徑,歷史地展示了蒙古族在形而上等問題上的哲學智慧以及道德思考的民族性。
蒙古族哲學;思維方式;天人關系;人神關系;英雄
蒙古族哲學以天與人、人與神和人與英雄等范式,在哲學一般性問題上,闡述了蒙古族哲學的特殊性,是一種“蒙古族的哲學”智慧。研究蒙古族哲學,要把握以“誠”為代表的民族道德的主旨,并用民族文化的精神背景襯托蒙古族哲學思維的特殊性。
一、天人關系思維方式
長生天是古代北方民族,諸如突厥、蒙古族等民族關于天的原始描述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賦予了其不同的民族內容。從蒙古族的歷史看,長生天在不同的時期與神、英雄、黃金家族等形象相結合,演繹了蒙古族思考天人關系的主題。
在蒙古族思想文化中,長生天首先出現在早期薩滿教的祭詞、贊歌和神話傳說中,如早期的開天說,描繪了遠古時代,世界是由氣(云霧)、水(脂膏)和土(物團)三種物質組成,它們是創世的基本始料或者說是萬物之源,后來逐漸形成了天地。在這些傳說中,原古的人們用自己身邊的事物說明世界,是人類早期直觀的表達方式。開天說代表著蒙古族的直觀思維形式,把對天的肯定放在終極的位置,是對世界本身來源的說明。開天說把人與世界相分離,反映了早期人類意識到天地與人之不同,用思維把自己與世界相分離。列寧說過:“本能的人,即野蠻人沒有把自己同自然過程區別開來,自覺的人則區分開來,范疇是區分過程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1]開天意識是一種初級范疇,加入了人類勞動的作用,以之區別于人之前存在的自然世界。可以說,人們把眼前的世界開始區分為自然與文化的不同,使人從本能的狀態走向了社會,并通過對自己勞動的肯定,表達了對自己智慧和價值的認可。
與開天說對天的直觀表達不同,在神話故事中,天通過神的影子走向與神性相聯系的天性之中。在“冰天大戰”和“麥德爾娘娘開天辟地”的傳說中,用“魔王吞日”解釋日蝕和月蝕;用“冬天和夏天的由來”解釋夏熱冬冷的原因,用神話回答生活中的問題,神話的認識功能是蒙古族思維從直覺向綜合的轉變。在神話傳說中,天具有了神的生成功能。看似荒誕的神話,體現了人們求真的精神,對客觀事物聯系的追求,對因果關系的探索。
隨著私有財產的發展,開天說與神話傳說具有了自然崇拜的性質,表現為在自然神和職能神中形成了長生天——騰格里,形成了以騰格里為主神的眾神系統。在騰格里主神的領導下,出現了眾多的職能神,如瑪納罕、吉雅其、蘇勒德等。騰格里具有兩方面的神性,一是創世的神性。二是造人的神性。至此,在蒙古族的天人關系中,天從質料性的物上升為與人性不同的神性,完成了天對人的至上性權力。
創世神話回答了天地的來源問題,并從可感知的具體事物探索了因果聯系,試圖解決天地的終極性問題,是人類思維至上性的體現,與因果性相結合,構成了人類思維的必然性。
在史詩中,提出了寶木巴的理想社會,“夏日常在,沒有冬天,——永遠年輕,沒有死亡——人丁興旺,沒有孤獨——永遠安寧,沒有戰亂。”[2]從寶木巴的內容看,表達了人們對心中理想社會的追求,是人類精神的寄托,表達了與信仰相關的思維構架,與開天說表達的理性思維相結合。信仰思維的形成說明了蒙古族哲學思維走向了自覺與成熟[3]。信仰思維是一個民族思維構架的完成,信仰在思維中表現,是一個民族哲學自覺成熟的標志。
“統一是全書(《蒙古秘史》)的主題”,從全書的邏輯結構看,以天命觀為起始,以感光生子等天人關系中天命的思想論證了成吉思汗汗權的神授性。用天命觀論證了世俗政權必然性,神學成為世俗的先導。“就問題來說,天人關系已擺脫宗教形式而直接以抽象的形式表達,并由此引申出價值問題、道德問題和人性問題,使哲學的思考深入到哲學的各領域。就哲學意識看,其自覺性更有成熟的表現,在這一時期,哲學曾三次表現出它的批判精神,一是針對宿命論,提出‘以誠配天’,從聽天由命中把人的思路解放出來;二是針對‘祖述不變’,提出‘祖述變通’的思想,要鼎新革故、宣揚弘遠,要從武功向文治轉變,適應了汗權治天下的歷史任務;三是針對黃金家族的汗權論,提出‘政教兩道并行’的主張,對汗主有明確的要求,其中有并沒有血緣種屬條件,這是汗位繼承上對黃金家族觀的否定,為汗權的鞏固和發展打開了新的思路。”[4]
盡管有天命神權的論證和蒙古帝國的強大,以忽必烈汗為代表的蒙古貴族在處理天人關系時,尊重現實,提出了“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的治國方針。與早期的天命觀不同,他強調先天人合一的關鍵在于人要以德合天,實惠與至誠同等重要。在他那里,天人合一具有了實惠的內涵,實惠成了聯系天人之間的橋梁,這使蒙古族傳統思維倫理化傾向具有了世俗的內容,是蒙古族思維方式的重大轉變。
在《十善福經白史》中,作者倡導政教兩道并行的治國方針,以“道”來論證汗權的合理性,并對“道”作了形而上的說明。與早期的天命觀不同,天命逐漸為“道”所排擠,使蒙古族文化從神學走向了哲學。筆者在《蒙古族英雄文化時期哲學思維方式研究》中提到過“約束”。事實上,“道”是先前“約束”一詞的理論發展,“約束”主要的內容集中在道德上。到了《十善福經白史》,“約束”演化為“道”,超出了道德的內涵,成為根源性的東西,表明人們更加關注事物內在的根本,這體現了人們從感性直覺思維向理性思維的進步。
二、人神思維方式
在天人關系中,交織著人神關系,在人神關系中反映蒙古族文化的天人關系。
原始薩滿教以自然物崇拜為特征,包括把日、月、山、水、禽獸、火等作為崇拜物來供奉(這是早期的神祇),以后才逐漸出現了瑪納罕、吉雅其、蘇勒德等職能神。從自然物、職能神,再到天神騰格里,人們的思維能力從最初對個體事物的把握逐步走向概念抽象。在自然崇拜階段,人們的思維停留于個體事物的屬性,到了騰格里階段,人們的思維上升為共性的騰格里,出現人造神,這標志著人們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是思維能力本身的提高。就宗教發展史而言,是自然宗教向人文宗教的過渡。
在最初的自然神和職能神中,不存在相互的隸屬關系。只是私有制以后,才出現主從的神統觀念。最高的神為霍日穆斯塔(騰格里),下面有55位西方天神等次級神,再往下還有成千上萬的翁貢等,這樣的神譜體系表明,蒙古族原始平等的思維走向了一種不平等思維。
在英雄文化時期,薩滿教統治著蒙古族的信仰世界,到了汗權文化時期,薩滿教的地位有所下降,特別在成吉思汗和合撒爾的沖突中,成吉思汗對薩滿的處罰,突顯了政治高于宗教。在英雄文化時期,人們的信仰是先信仰后理性,但到了汗權文化時期,宗教服務于政治,變成了先政治后信仰。從先信仰后理性,再到先政治后信仰的轉變,是蒙古族信仰思維的根本變化。
與英雄文化時期到汗權文化時期相適應,宗教也實現了從神啟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轉變。所謂神啟宗教是指英雄時代的薩滿教把世界一切看成是神的啟示,人們不過是按照神的啟示來生活,人在神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附從,其思維方式是由神到人。道德宗教是指汗權時代的人們已經把先前神啟的對象演化成一種道德標準,神已經變為一位道德的長生天,由最初的對神崇拜發展到對長生天的崇拜,而對長生天的崇拜演化成對道德境界的崇拜,其思維方式是由人到神。也就是說,在汗權時代的宗教領域中,崇拜的對象已經由神轉化到了道德境界,而道德境界的設定不是由神來規定,而是由人來設定,這樣一來,在人和神之間,變成了由人來規定神,而不是由神來規定人,人成為了思維的中心和內容。也就是說,人的能動性在神面前得到彰顯。這是人們思維的重大轉變[5]。
自16世紀喇嘛教成為國教后,喇嘛教主導了蒙古人的信仰,形成了新的人神關系,構筑了民眾文化時期的出世思維。
首先,喇嘛教以“空”為自己的信仰開端,主張“緣起性空”。“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6]。“有”是事物的假象,“空”為事物表象后的“真有”,是“有”中之空。“空”的主張在理論上,把人存活的基礎挖空了。
其次,喇嘛教以“空”為基礎,立足于“苦”,使人產生出走的思維沖動。喇嘛教認為一切眾生之體出沒無常,輪回之中沒有永恒,一切存在都難免滅亡。人生是苦難的。喇嘛教把現實的世界看成是痛苦的,符合了人們對生活艱辛的感悟。“苦”的觀點在理論上產生了熄滅現世渴望、追求來世的沖動。
第三,現世景象的幻滅,帶來了歸宿于佛的終極走向。既然人性是空的,活著又是痛苦,人只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才能最后解脫,“脫離苦海、慈航普渡”[7]。至于如何能夠達到“大空”境界,只能靠自己努力修行,自己悟道。
從喇嘛教的推理看,人要服從“命運”的安排,勤加修行,秉持戒律,才會有“來世”的幸福。這樣,出世的選擇成為理論上的必然走向[8]。
三、人和英雄人物關系思維方式
英雄是蒙古族文化脫離神性后人性的神化,是世俗文化中俗人的主宰,是民族精神的寄托。
神話是早期蒙古族部落斗爭和部落首領與氏族成員之間關系的反映,盡管天命論和有神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但現實的斗爭使人們已經在神和英雄之間重新選擇新的主人。在《征服黑龍王》《莫日根射日》《阿拜格斯爾》等神話中,最初把英雄和天神對立起來,說英雄罕哈演貴是“為了和天神們戰斗而生”、“為了與地神作對而誕生”。在神和人的斗爭中,著力頌揚英雄的威力,突出肯定人力的思想。這時,人們已經從最初的崇神開始了疑神,這是一種對自己價值的肯定,人的利益、人的道德、人的力量在史詩中得到張揚,這表明了人對自身有了認識,即人的自我意識已經生成。這些作品的意義在于用人的意識去批判神權思想,人的自我意識思維開始出現,突顯了以人為主體來看待這個世界的思維方式的發端。
繼神話之后,大量的史詩開始出現,據統計有近三百部。史詩文學的形成開辟了蒙古民族的新紀元,使民族文化由神話階段進入人文文化的新時期。它把人們的理想追求從天上神界拉回到現實生活之中,用歌頌英雄替代崇拜神靈,贊美人的力量能戰勝邪惡,堅信勇敢和智慧定能使善戰勝惡。總之,人的需求、人的能力、理想的實現都具有了肯定的價值。使得人們思維的對象從神轉向了人自身,英雄形象成了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載體。
史詩通過英雄的業績來說明英雄的偉大。《江格爾》在說到江格爾時,問“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誰”?回答說“江格爾是陽光下的萬物的主宰”,是“世界的主人,主宰陽光下的生靈”。體現了人對自身認識的覺醒,并從神祇主宰萬物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對于寶木巴,過去這些理想被人們依附在神靈的身上,不是用神話的形式表達和實現,就是安在善神身上成了善神的神性。當英雄作為人們的理想的化身被崇拜后,寶木巴又成了英雄的棲身之地,這樣安排的在于提高英雄在宇宙中的地位,客觀上提高人的理想價值。除了他的功績外,英雄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和天神有所不同的是,這是一個生長在地上的天神。也就是說人們把天神崇拜變成了人對人的崇拜,這是一種人對人肯定的思維。盡管英雄只是一個抽象概念而已,也是人從自身來思考自身的開始。
與史詩相銜接的《蒙古秘史》,它把成吉思汗為代表的黃金家族作為新英雄的代表,并影響和左右著蒙古族的命運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蒙古秘史》是對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英雄神話歷史的史學記錄,或者說,從成吉思汗的22代世祖到窩闊臺,黃金家庭的歷史成為蒙古民族的歷史。這一時期的偶像崇拜達到了頂峰,成吉思汗也由人變成了蒙古人間的神,特別是入主中原后,汗權成為蒙古民族的精神寄托,標志著崇拜思維世俗化的開始。
《蒙古秘史》開篇就講:“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成吉思汗被傳說是蒼狼和白鹿的第22代子孫,是蒙古民族圖騰崇拜之子,他完成了對蒙古草原的統一,重創金朝,西征歐洲,被呼為“萬國皇帝”。蒙古族成為草原的主人,而成吉思汗變成了主人之上的締造者,并演化為民族的神靈,人們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也達到了蒙古民族崇拜史的頂點,眾英雄崇拜的思維模式開始向一神崇拜轉化。
入主中原后,忽必烈的元帝國不僅奠定中華地域的基本版圖,也開創了蒙漢民族融合的新紀元,成為影響中華民族走向的重要歷史時期,蒙古族在中原的政治與文化統治也達到了空前的影響。可以說,元朝是蒙古民族的驕傲,忽必烈等可汗人物成為民族驕傲的領跑者,是黃金家族的杰出人物。人們在成吉思汗的影子下思考后輩的蒙古民族。
在北元時期,從脫古思帖上木兒汗到岱總汗,幾十年的時間里,經歷了九位汗主,爭斗始終圍繞黃金家族的正統與否來進行,直到1479年巴圖蒙克達延汗繼位,在滿都海夫人的幫助下,汗權才又回到了黃金家族的手中。人們正統思想的秉持直接影響著蒙古民族已經形成的汗權崇拜思維模式,并左右著政治王朝的基本走向。
對大汗的崇拜也表現在文化等方面,如《羅·黃金史》中,作者用了五分之三的篇幅講述成吉思汗的業績和必力克,是“為了子孫后代不忘其祖先”。羅卜桑丹津在書中始終打著祖先成吉思的旗號,借著成吉思汗的影子說明了蒙古民族要做的事情,這樣的寫作方式是蒙古汗權崇拜的思維模式在文化方面的表達[9]。
四、以誠為主的道德思維判斷
以“誠”為主的道德性是蒙古族文化最顯著的地方,在諸種的關系中,“誠”主宰著判斷的精神,并逐漸演化為一種思維的判斷形式。
在薩滿教的諸神神性中,人們把善與惡看成神性的規定性。神被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善神,一類是惡神。在善神與惡神的斗爭中,代表光明、正義的善神總是戰勝代表丑陋、殘暴的惡神。宗教的問題變成了善惡倫理概念的爭斗,宗教走向了倫理,或者叫倫理入教,倫理思考問題的方式成為宗教的標準。神靈被道德化,人們由最初的對自然神的自然屬性崇拜變成了對神靈道德品性的崇拜。倫理學中的善惡思維方式走進了薩滿教。另外,在解決眾神關系中的“敬”字等原則中,我們也看到一樣的東西,“敬”字本身是一個道德概念,在這里卻變成了神學的標準。也就是說,用道德的標準處理宗教的問題。在薩滿教中,處處可以看到諸如此類的例子。
在成吉思汗箴言中,忠誠被放到重要地位,看成長生天的屬性。成吉思汗對眾人講“汝在背處也,仍如在俺眼,汝去遠處也,仍如在俺近邊,如此思之,則汝將獲上天佑乎。”[10]在人和天的關系中,人做到了忠誠,長生天才會保佑你,忠誠是天與人之間的橋梁,而橋梁的主要構成是道德,用道德做思維判斷是當時思維的主要特征之一。成吉思汗把忠誠看成長生天的屬性,長生天又是世界的生成的來源,因而具有形而上的性質,使忠誠在世界生成論中取得了自己的地位。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編年史,書中記載了大量的道德故事,形象而又生動,如“五箭訓子”,告訴人們只有相互團結,才能戰勝困難,形象的比喻成為蒙古民族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方法。在這些故事中,告訴人們:做人要胸懷博大,對主人要忠誠,上戰場要勇敢等,因此,《蒙古秘史》也是一部道德教化史。
《蒙古秘史》宣揚的忠誠、勇敢、廣博等道德范疇,在作者看來是上天的屬性,是天人合一的核心,如成吉思汗對速別臺講“我們如果忠誠,上天會倍加佑護的。”[11]在這里,道德范疇被客體化。《蒙古秘史》從屬性出發來思維,并把道德推演成客體的方法,是一種“道德屬性客體化思維。”
事實上,蒙古族文化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可以發現它的道德思維判斷,如蒙哥汗“以德治經”的主政思維;忽必烈汗的“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的治國方針;哈斯寶在《新譯<紅樓夢>回批》中提出的“我欲做忠臣而成為不忠,欲做義士而成為無義”[12]163的文學批判。特別要指出的是,尹湛納希提出了智慧和忠誠的關系,認為耿直生忠誠,忠誠出大智。他說“福德勢恩如車輪,首尾相關而轉動,車軸就是賢明”[12]634。在解決勢與恩即天與人的關系問題上,關鍵是賢明,這就把過去“以誠配天”的思維轉向了“以智配天”,智成為連接天人的車軸,使天人關系從道德的領域走向了知識的領域,這是蒙古民族在思維天人關系上的重大變化。
研究蒙古族哲學思維方式,用蒙古族文化闡明蒙古族哲學,不僅解決了蒙古族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更重要的是證明了蒙古族哲學的民族性。上述研究僅就一些問題的原則作了說明,意在為研究蒙古族哲學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就視域看,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本文拋磚,期待美玉。
[1]列寧.哲學筆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0.
[2]江格爾[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7.
[3]王福革.蒙古族英雄文化時期哲學思維方式研究[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8(1):21-24.
[4]蘇和,陶克套.蒙古族哲學思想史[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71.
[5]王福革.蒙古族汗權文化時期哲學思維方式研究[J].前沿,2008(8):80-83.
[6]龍樹.郭然巴注.中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2.
[7]嚴北溟.中國佛教哲學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25.
[8]王福革.蒙古族傳統思維方式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08(11):112-114.
[9]王福革.蒙古族民眾文化時期哲學思維方式研究[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8(4):298-302.
[10]蒙古民間英雄史詩:上冊[M].蒙文版.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46.
[11]額爾登泰.《蒙古秘史》還原注釋[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634.
[12]額爾敦·陶克陶.蒙古族作家文論選[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of the Mongolians WANG Fu-ge,WANG Xu-z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Histor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Tongliao Inner Mongolia 028000,China)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God,man and hero,the paper reveals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of the Mongolians,demonstrates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the Mongolians in metaphysics and their judgment ofmorality.
Mongolia nationality philosophy;thinkingmode;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hero
C95
A
10.13744/j.cnki.cn21-1431/g4.2014.02.002
1009-315X(2014)02-0100-04
2013-07-26;最后
2013-10-29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09BZX071);內蒙古東部經濟歷史文化研究基地資助項目(D07)。
王福革(1968-),男,蒙古族,內蒙古通遼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和民族文化比較研究。
(責任編輯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