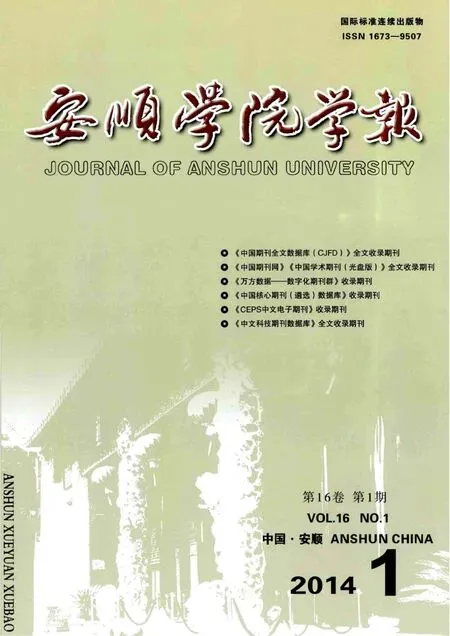《文心雕龍》“奇正”思想的批評方法
婁仁彪
(安順學院人文學院,貴州 安順 561000)
《文心雕龍》“奇正”思想的批評方法
婁仁彪
(安順學院人文學院,貴州 安順 561000)
劉勰 “奇正”思想的批評方法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獨立地使用 “奇”與 “正”來批評文學要素,二是運用 “奇正”的辯證關系來進行批評。作者認為在文學批評過程中 “奇”與 “正”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應該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或批評領域隨時注意 “奇”與 “正”的相互轉化,并靈活地以此來分析問題。
《文心雕龍》;劉勰;奇正觀;批評方法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在該著作里,劉勰對文學批評方法進行了系統、全面的闡述,并對歷代文學理論、文學作品以及文人進行批評。奇正觀作為 “六觀”[1]之一,歷年來很受學界的青睞,臺灣學者林中明首先從兵家的角度論述劉勰對兵家 “奇正”思想的繼承發(fā)展,認為這是 “引兵入文”[2]的先例。學者寇效信從思想內容、修辭方法等角度對劉勰奇正思想進行全面和深刻的研究,但對 “奇”與 “正”的論證 “失之于籠統,原因是在于脫離了 ‘奇’與 ‘正’的關系孤立地看‘奇’”[3]。王英志從 “奇”與 “正”的對立統一關系中系統地論證了劉勰的奇正觀[4],而對劉勰如何運用這種方法,則沒有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論證。牟世金認為奇正觀是批評方法,而不是批評標準[5],這對于研究奇正觀方法論很有啟發(fā)性,但牟先生沒有作具體的展開。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論述 《文心雕龍》奇正觀作為批評方法的批評過程。
一、“奇”和 “正”獨立自足
《文心雕龍》奇正觀的 “奇”和 “正”有時是分開運用的,并且都有實在的意義。寇效信認為 “所謂 ‘正’應該包括這樣一些意思:文章思想內容的純正,符合儒家正統思想的規(guī)范,用 ‘事’詳實可靠,語言平正暢達以及風格典雅端莊。而 ‘奇’也包含多方面的內容,如思想的奇突新穎,標新立異,用 ‘事’的奇詭怪誕,荒唐不經,辭采的奇絕詭麗,振聾發(fā)聵,以及風格的雄奇恣肆,不墮庸反。”[6]寇先生從 “奇”和 “正”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和具體的研究,使人深受啟發(fā)。但 《文心雕龍》是怎樣分別用 “奇”和 “正”的思想來批評文學現象的呢?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探析。
1、“奇”的用法
劉勰奇正觀中 “奇”的運用是對兵家 “奇正”思想的“奇”的繼承和發(fā)展。兵家講的是 “出奇制勝”,比如 《孫子兵法》中的 “奇兵”“以奇治兵”“奇正相生”[7]等都是能給勝利帶來希望的重要因素。《說文解字》對 “奇”的解釋是 “奇,異也”,而 《康熙字典》對 “奇”字的解釋則包括“異”、“詭異”等多個義項。《文心雕龍》中的 “奇”繼承了兵家褒義的一面,如 “奇文郁起”“事豐奇?zhèn)ァ保?]45等。另外,劉勰還發(fā)展了 “奇”貶義的一面,如 “愛奇反經之尤”[1]284等,這與文學追求 “美”的藝術性質有關,文學不排除有 “雄奇”之美,但一味追求 “奇”的風格,難免就會劃入 “險”的范疇,而流入藝術美的另一端。劉勰把“奇”的這兩層含義都運用到文學批評的各個方面。
在修辭技巧上用 “奇”,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1]1是指大自然的奇花異草,都有自己的色彩,無需能工巧匠的神奇技巧。這里的 “奇”修飾技術、技巧。“錦匠”的 “奇技”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與大自然的作品作比較,劉勰用 “奇技”來反襯大自然的杰作,認為自然的作品最美。如 《詮賦》篇論述說:
至于草區(qū)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qū)畛,奇巧之機要也。[1]135
劉勰稱司馬相如、楊雄、班固等的賦為大賦,認為他們的賦 “體國經野,義尚光大”[1]135。但是,像這樣的賦也有亂辭 (“履端于倡序,亦歸馀于總亂”)[1]135的毛病。然而,在一些小賦 (“小制”)的創(chuàng)作技巧上,反而比大賦更加“奇巧”,內容上雖然是一些禽、獸、草、木等的雜類,但他們能觸物生情。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隨著情況的變化,抓住時機,加以刻畫。語言、文采都注重細密、確切。劉勰認為小賦的創(chuàng)作技巧不但巧,而且 “奇”,為什么呢?按《老子》:“人多伎巧,奇物滋起。”[8]《說文》:“奇,偉也。”“奇”有罕見之意。在賦這種文體繁榮興盛的西漢,人們往往重視大賦的創(chuàng)作和欣賞,而忽視了小賦、短賦。劉勰用一 “奇”字點出這些小賦不但有可觀之處,甚至在創(chuàng)作技巧上還比大賦更加的巧妙。
劉勰也用 “奇”的貶義來批評文學作品。除了 “奇”本身外,他還用了一些與 “奇”意思相近的詞。如詭異、詭奇、詭巧、淫麗等,這些詞都被他歸入到 “奇”的范疇里,他認為之所以導致這樣的失誤,是因為作者 “逐奇”[1]531的結果。那么,劉勰用 “奇”來批評作者創(chuàng)作上的失誤,表現在哪幾個方面呢?
首先表現在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容上。儒家思想雖然不是劉勰批評文學的唯一標準,但卻是他重要的參考標準之一。這就表現在他對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的態(tài)度上。他認為儒家的六經是 “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1]21,所以作品的思想內容,符合儒家思想就為正,反之則為奇。劉勰用 “奇”批評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如 《時序》篇批評戰(zhàn)國時期鄒衍、騶奭的瑰麗艷說和屈原、宋玉的奇譎暐曄時說:“觀其艷說,則籠罩 《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1]672鄒衍、騶奭美艷的辭說和屈原、宋玉等的奇特虛構,從修辭的角度看,他們繼承了戰(zhàn)國時期文人 “事豐奇?zhèn)ァ钡难赞o,但從內容上看與 《雅》《頌》不符,所以也被劃入 “詭俗”的范疇。其次,對貶義的 “奇”的運用,還表現在對風格的批評上。對于 “六義”中的 “風清而不雜”“文麗而不淫”“體約而不蕪”[1]23,都是從風格上來要求創(chuàng)作的。這里的 “雜”“淫”“蕪”都有 “詭怪”的意思,所以也是 “奇”的近義詞。要求在創(chuàng)作上要注意風格的清新、雅麗、要約,反對繁雜、淫濫、蕪亂的風格。
2、“正”的用法
《文心雕龍》里的 “正”,內容也相當豐富,有些學者僅僅從字面上來解釋 “正”,認為 “正”有正常、雅正、呆板和作為證據等的意思[9]。但劉勰在 《文心雕龍》里對“正”的用法主要是從內容和修辭兩個方面來闡述的。
首先,內容要符合儒家的 “雅正” “義貞”的要求。劉勰認為符合儒家思想的內容就是 “正”,如 “義歸無邪”[1]65就是 《詩經》的 “思無邪”,“辭譎義貞”[1]65,“辭雖傾回,意歸義正”[1]270“無邪”“義貞”“雅義”“義正”等是純粹的意思。例如在 《樂府》篇,劉勰認為好的音樂標準是看它能否表達儒家思想。他說:“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1]101”他認為音樂之所以受到圣人的重視,是因為它有 “務塞淫濫”的功能,因此能夠起到教養(yǎng)天下子弟,歌頌圣人的功德和教化四方風俗的作用。符合這個作用的音樂就是 “雅聲”,反之則是 “溺音”。
其次,內容要充實,感情要真摯。劉勰認為作品的內容充實,感情真摯,才符合 “正”的要求。在 《征圣》篇里,他引用孔子的話 (“情欲信,辭欲巧”)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里的 “情”不只是指作者的感情、情志,而且還包括作品的思想內容。要求感情要真實可信;內容要充實可靠。所以他說: “然則圣文之雅麗,固懸華而佩實者也。”[1]16這樣做就符合圣人 “雅麗”的要求, “雅”就是“正”。他又說 “博文以該情也”[1]16,這里的 “情”指作品的思想內容或作者的情理。是說用很多言辭來概括思想內容,使文章顯得瑣碎、雜亂,不符合 “正”的要求,是劉勰要反對的。
從修辭上看,劉勰認為符合經典的修辭手法就是“正”,并以此作為評判作品好壞的標準之一,如 “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1]23,又比如 “然文術多門……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1]514這里的“正式”(吳林伯先生釋為 “舊式”),是指經、史、子、集中的法術,即修辭的法則,本書 《定勢》篇易 (改變)為“舊式”,以其不變,世代相傳,故曰 “舊”也[10]。也就是“執(zhí)正馭奇”的 “正”。
二、“奇”與 “正”的辯證統一
討論劉勰 “奇正”思想的辯證統一的關系,也就是“奇”與 “正”的相輔相成的關系,這種關系體現在 “酌奇而不失其正,玩華而不墜其實”[1]48的特殊要求中,即如何處理好 “奇”與 “正”,“華”與 “實”的辯證關系。童慶炳先生解釋 “奇正華實”的辯證關系說:“劉勰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一個創(chuàng)作中的 ‘奇與正’、‘華與實’的關系問題,在奇與正、華與實之間要保持張力,既不能過奇而失正,過華而失實,也不能為了正而失去奇、過實而失去華。”[11]童先生提出了 “折衷點”和 “藝術的張力”,也就是說只有正確處理好 “奇”與 “正”, “華”與 “實”特殊的關系,才能創(chuàng)造出好的作品。
1、對立統一的奇正觀
“奇正”思想的辯證關系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形式的要求上。所謂 “執(zhí)正以馭奇”就是以正確的思想內容來駕馭作品的形式,或 “奇”的形式必須符合純正的思想內容。《文心雕龍》的前五篇是全書的總綱領,即所謂“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1]727。《原道》《征圣》《宗經》是 “執(zhí)正”的 “正”的思想根據,《正緯》《辨騷》則突出了 “馭奇”“酌奇”的要求,即在 “執(zhí)正”的基礎上,可以 “酌乎緯”之 “事豐奇?zhèn)ィo富膏胰”,從而 “有助文章”,更可以 “変乎騷”而寫出跨時代的 “奇文”。[1]31儒家思想是劉勰文學批評的標準之一,但是儒家思想不是 “執(zhí)正”的唯一標準。周振甫先生就指出:“所謂的 《征圣》、《宗經》并不是要按照儒家思想來創(chuàng)作,也不是根據儒家的語言來創(chuàng)作,實際上是要學習經典的各種創(chuàng)作手法,這是無可厚非的。”[12]周先生的話是有道理的,比如被稱為 “奇文”和 “騷經”的 《離騷》則是在繼承 《詩經》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出來的。
“奇正”思想的對立統一關系還體現在具體文體的創(chuàng)作要求上。比如對 《哀吊》篇里 “吊”的文體創(chuàng)作,劉勰概括其特點為:“夫吊雖古義,而華辭末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1]241”他認為 “吊”這種文體,意義雖然很古老,但它的辭采并不以華麗為美。從修辭的角度來看,如果文辭過于華麗,則會流于 “淫侈”,也就是“奇”,從而導致音調的遲緩,那么所作的 “吊”就會變成夸張的辭賦。所以在創(chuàng)作這種文體時,要用 “吊”的 “舊式”(原則)來馭 “奇”,也就是 《通變》篇所講的 “資故實”才能 “酌新聲”。從思想內容的要求上看,“吊”這種文體應當以正直的義理為準繩,昭示道德,而又有諷諫的功能,這是作 “吊”的原則,要按照這種原則來創(chuàng)作才能符合 “哀而有正”的要求。無論在文辭,還是在思想內容上要做到 “奇”與 “正”(原則與方法)的有機統一,才符合文學的創(chuàng)作要求。
2、奇正相生”的奇正觀
兵家所講的 “奇正相生”的辯證統一關系,即 “奇”“正”在一定的條件下,“奇”可以轉化成 “正”,“正”亦可以轉化為 “奇”。劉勰在 《文心雕龍》里闡述了他 “奇復為正”的思想:“淵乎文者,并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1]530他認為 “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可見,他在 《文心雕龍》里是用到“奇正相生”的思想的。《文心雕龍》里提到了很多標準,例如 “六義”“八體”[1]505等,概而論之,其實就分為兩條標準:一是經典的標準,二是辭賦的標準。所謂經典的標準就是除了以儒家正統的思想作為批評的標準外,還以是否符合經典創(chuàng)作的各種寫作手法作為標準[13]。而所謂辭賦的標準就是 “事豐奇?zhèn)ィo富膏胰,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1]31在 《文心雕龍》里,劉勰經常對同一文學現象持不同看法,原因是他所采用的批評標準不一樣。如果站在儒家經典的標準來批評,這一批評對象是 “正”,如果站在辭賦的標準來批評,這一批評對象就是 “奇”了。“奇正”的相互轉化,表明他是繼承了兵家 “奇正相生”的奇正觀。比如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就反映了這種觀點。
劉勰認為屈原的作品中存在著 “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猖狹之志”“荒淫之義”[1]47,并稱它們?yōu)?“異乎經典”的四事。然而,所謂的 “詭異之辭”“譎怪之談”是指屈原作品里的神話傳說和瑰麗的言辭;“猖狹之志”則是他愛國的表現;而 “荒淫之義”是他諷刺統治者的荒淫。從劉勰的角度看,他認為 “異乎經典”的四事不符合儒家經典的要求,即不符合 “六義”所要求的 “事信而不誕,義貞而不回”[1]23。所以劉勰把它歸入 “奇”的范疇里。但是,在《詮賦》篇里他說:“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并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1]135這里的 “頌”是指風雅頌的“頌”,是朝廷祭祀祖先或歌功頌德的詩歌,他把 “楚賦”和商代的頌歌相比較,認為它們都是屬于大賦的范圍,是典雅之文。可見,在這里他又認為屈原的作品是 “雅文”,也就是 “正”。劉勰對同一批評對象所采取不同的批評標準,因此得到不同的結果。用這個標準來批評可能是“正”,而換另一個標準則是 “奇”。他根據批評標準的變化,不但能夠靈活地使用 “奇”與 “正”來分析變化的因素,而且還能用 “奇”與 “正”相互轉化的思想評價它們。
綜上所述,“奇正”思想作為兵家重要的用兵理念,被劉勰引用到文學批評領域,并賦予它豐富的內涵。在《文心雕龍》里,劉勰有時單獨用 “奇”或 “正”來批評文學現象,指出作品在思想內容、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文學發(fā)展變革等方面的特點。另外,劉勰還注意到 “奇”和 “正”這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詞組的特征,并用這種辯證關系來處理一些看似相對或矛盾的文學現象,很好地把這種矛盾統一起來,這與劉勰多角度,全方位,辯證看待文學發(fā)展有關。正因為這樣,劉勰才創(chuàng)作出 《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思精”的文學批評專著。
[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751.
[2]林中明·由《文心》、《孫子》看中國古典文論的源流和發(fā)揚[EB/OL].藝術中國網站,http://www.artx.cn/artx/guoxue/16188_4.html,2007-01-15.
[3][4]王英志·也釋《文心雕龍》之奇正[J].陜西師范大學報,1982(1).
[5]牟世金·劉勰論文學欣賞[J].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4).
[6]寇效信·釋奇正[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80(2).
[7](春秋)孫武·孫子兵法[M].(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2:83.
[8]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譯[M].北京,中華書局,2008:197.
[9]陳書良·《文心雕龍》釋名[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73.
[10][13]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373、358.
[11]童慶炳·文心雕龍的奇正華實說[J].文藝理論研究,1999(1).
[12]周振甫:《文心雕龍》二十二講[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137—138.
The Methods of Criticism in the“Qi Zheng”Theory on the“Literary Heart Carving Dragons”
Lou Renbiao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Anshun University,Anshun 561000,Guizhou,China)
There are two methods of criticism in the“Qi Zheng”theory.The first one requires the independent usage of“Qi”and“Zheng”to criticize the literary elements.The second one lies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Qi”and“Zheng”,which one require the control of odd by using positive and supplement the positive with the odd.And the other one claims the usage of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Qi and Zheng,which calls for a flexible usage of“Qi”and“Zheng”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literary field.
“Literary Heart Carving Dragons”;Liu Xie;Qi Zheng theory;Criticism method
顏建華)
J207
A
1673-9507(2014)01-0004-03
2013-11-12
婁仁彪 (1983.03~),男,布依族,貴州鎮(zhèn)寧人,安順學院人文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