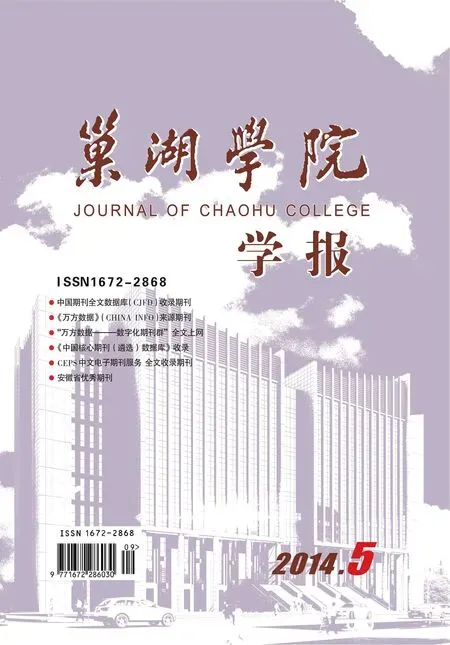凌家灘遺址防御體系及其社會意義之蠡測
劉松林
(含山縣文物管理局,安徽 含山 238100)
凌家灘遺址防御體系及其社會意義之蠡測
劉松林
(含山縣文物管理局,安徽 含山 238100)
凌家灘遺址具有天然與人工防御體系,早期利用“后枕太湖山,東、西、南三面環水”地理形勢進行防御。隨著氣候、地質等條件的變化,崗地兩側大片水域漸退、緩慢成陸,加之聚落人口的增多,故居住范圍向崗地兩側灘地拓展,由此帶來了天然防御功能的消退,于是凌家灘先民便開挖環壕,以強化其防御能力。作為新石器晚期聚落遺址,其防御體系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處于大規模環壕與城墻轉變的過渡節點上,與社會結構形態演變相關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較多存在,具有普遍之意。
凌家灘遺址;防御體系;環壕;城址;社會意義
1 前言
凌家灘遺址位于太湖山支崗南麓,其南臨裕溪河,北枕太湖山,面積約160平方公里。從198 5年起,安徽省考古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勘探與發掘,揭露出大量的重要遺跡,其中有祭壇、墓地、約3000平方米的紅燒土塊建筑遺跡、大型圓弧形紅燒土塊遺跡、規模較大的環壕及居住區等。祭壇、墓地處于遺址最高處,南可俯視居住區及裕溪河。居住區分布于裕溪河北岸,呈東西條帶狀分布,遺跡甚為豐富。特別近河岸邊,堆積較厚,似有疊壓、打破關系,且方向與裕溪河平行。勘探及試掘表明,環壕為不規則形,東西兩側處于圩區,中間居于高崗,且兩端對接裕溪河,從而形成一環抱居住區的聚落環壕。高崗段環壕外側為祭壇與墓地。因此,從遺址周邊的地理形勢、環壕功能等方面來觀察,這一規模宏大的聚落群定有其防御外族及野獸襲擾的設施體系。筆者下文試就此進行初步分析,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2 從地理形勢角度看遺址的防御功能
從《巢湖凌家灘遺址古人類活動地理環境特征》[1]一文可以得知,凌家灘時期之初 (距今約5800年前),該處地理條件較為特殊,即太湖山南伸出多個支崗,呈“手指”狀分布,支崗之間均為大片低洼水域地。凌家灘遺址便居于其中一支崗南麓,即現在的長崗南麓,其后枕太湖山,東、西、南三面為大片低洼水域(圖1),由此可見其地勢顯要,堪稱當時的“風水寶地”。現從地理形勢角度分析其防御功能。
其一,高山對外族入侵有阻隔作用。凌家灘時期,社會生產力較為低下,人們所使用的砍伐工具多為石器,如石斧、石錛、石鑿之類,試想要越過海拔441米的太湖山,是多么的艱辛。其次,三面環水的形勢,在當時更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因此,筆者認為在這相對封閉地理空間內,應具有較強的天然防御功能。
其二,通過前幾次的調查、勘探及發掘,發現凌家灘遺址周邊具有較為豐富的小型聚落遺址,如韋崗、小田、田王、李崗、錢墩、烏龜墩等遺址,且對其呈拱衛之勢,地理條件及文化面貌一致,即均為凌家灘文化的一部分。從廣義上來看,這些聚落遺址均處于一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內,即南臨裕溪河、北枕太湖山、西近東關土山、東靠含漕公路。且在此空間內,眾多的小型聚落以凌家灘遺址為核心,從而既對其形成一定的防御作用,又產生了一定的等級差別。

3 從社會形態及聚落規模角度來看遺址的防御功能
凌家灘時期之初,其先人居于支崗南麓、臨近河岸,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出現了先進的玉石工藝、發達的稻作農業及四通八達的水域交互網,從而使得聚落規模加大、人口增多。加之氣候、地質等地理條件的變化,崗地兩側、裕溪河北岸大片水域漸退,且緩慢形成灘地,人口便向灘地拓展,由此產生了一個社會問題,即水域成陸后自然防御功能的減退。因此,人們為了對其聚落加固防御,于是在居住區東、西、北三面開挖壕溝,南面與裕溪河接通,其規模較大,平均寬約30米,局部深淺不同,如崗地處最深可達10米,兩側圩區深約2.5米(圖2)。由此可見挖壕土方量極大,試想當時若不存在掌握最大的神權、軍權聚落首領及巫師,怎能組織大規模的平民建造如此浩大工程,從另一側面體現了凌家灘人口的繁盛及防御功能的重要性。

從前幾次勘探情況來看,在吳莊與王洼交界處發現一早期溝渠,其西接裕溪河,東邊為大片水域。是否為凌家灘遺址外壕,暫不能定。但從其形制、規模來看,該溝渠寬與壕溝相當,崗地段亦較深,且位于地勢高差達8米左右的兩村交界處,完全具有野獸、外族入侵的防御功能。另在環壕與早期溝渠之間區域進行勘探,結果表明兩溝間存在零散的居住遺跡,但與環壕內居住遺跡相比,較為零散且規模小,反映出凌家灘先民居住范圍的拓展是從南至北,即由壕內向壕外延伸至早期溝渠,但居住址中心未變,仍處于壕內,因此,可以認為凌家灘遺址具有“雙重壕溝”防御之功能。
4 遺址防御功能的社會意義

新石器早中期 (約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農耕技術得到初步發展,聚落的分布密度及規模均相對較小,戰爭還不怎么頻繁,故其防御體系較為原始,多利用地理形勢進行防御,環壕發現不多,且規模較小,防御功能較差,多起界溝之作用。其寬度多在1~2.6米之間,深度往往也比較有限。按年代序列,凌家灘遺址防御功能不在此段。
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許多環壕規模不斷增大,其性質更傾向于防御,如安徽蒙城尉遲寺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遺址的特大型壕溝寬度已達29.5~31.0米[2],這與凌家灘遺址環壕的寬度相當。深度亦進一步加大,如西安半坡聚落的大圍溝(外壕)深5~6米[3],凌家灘遺址勘探結果表明環壕(崗地段)深達7米左右,上述情況均說明通過加大壕溝的寬度及深度來提高聚落的防御效果。從防御功能角度及年代序列來看,凌家灘當屬此段偏后。
銅石并用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隨著戰爭的發展及其殘酷性的不斷加劇,以壕溝為主的防御體系演變為以城墻為主的防御體系,且后來城墻形制亦發生了較大變化,即由圓形為主的發展演變成長方形或方形為主,而這種變化似乎更多地體現著社會集團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組織結構的一些重大變化[4]。《聚落群聚形態視野下的長江中游史前城址分類研究》[5]一文雖未論及城址形制的變化,但提及城址的規模與社會結構形態的演變切切相關,其歷史意義首先是史前血緣社會的重組與融合,是長江中游史前晚期社會變革的主流,從而促使文明古國的出現。凌家灘遺址防御功能包括天然與人工兩方面,即天然防御依據“北枕太湖山,東、西、南三面環水”的地理形勢,而人工防御-環壕則是在隨著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口規模的增大及戰爭頻繁所形成,其防御體系當處于壕溝與城墻防御之過渡節點,且與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分工細化、等級差別較大相對應,從而使得最為先進的凌家灘文化成為文明古國的先聲,且率先出現文明曙光。

新石器晚期,凌家灘遺址稻作農業較為發達,其先民過著穩定的定居生活,且對農耕土地的依賴性較強,從而顯示出土地的重要性,由此促使其把捍衛領地作為首要任務。然凌家灘遺址天然防御功能受氣候、地質等條件的影響消退,于是便開挖了環壕,其目的雖存在排水、界溝之功能,但主要目的應是增強防御功能。這正是農業文明所帶來的重大變化,甚或有學者把農業階段視為人類文明的“第一次浪潮”[6],由此便帶來了較多新石器晚期農業聚落開挖大規模環壕以防御其領地。

凌家灘遺址防御功能較為多樣,早期利用地理形勢防御,即“后依太湖山、三面臨水”之格局,形成特有的自然屏障。隨著時間的推移,崗地兩側圩區水域漸退及人口增多,從而使得居住范圍向崗地兩圩區灘地拓展,其東西兩面天然屏障漸失。為了提升聚落防御功能,便在聚落周圍開挖人工防御設施-環壕。然隨著人口進一步增多,在環壕外出現零星的、小范圍居住遺跡,從而出現了早期溝渠,其防御功能進一步增強,似“雙重壕溝”之防御。這在同時期文化亦是存在的,如半坡遺址便出現了雙重環壕防御設施,內外壕間有一定的居住遺跡[7];再如日本彌生時代發現較多的雙重環壕,防御功能較強,雖時代甚晚,但卻是農耕文化開始發生、發展的時期,其文化是從我國東北經朝鮮傳播過去的[8],與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雙重環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及可比性[9]。再者,在遺址周邊相對封閉的區域內,有眾多中小型聚落遺址對其呈拱衛之勢,便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由上可見凌家灘遺址具備一定的防御體系,且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

從時代大背景來看,凌家灘遺址防御體系的變化當與社會結構形態演變有關,即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聚落分布較少,規模較小,其防御體系單一,一般多以自然防御為主,即利用山川形勢作為天然屏障,即便存有壕溝,亦大多為小規模,其性質以界溝為主,防御功能較弱,這種情形與其較為單一的社會結構形態是相對應的,即聚落間沖突少見,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如《中國東北先史環壕聚落的演變與傳播》[8]一文便提及東北興隆洼文化時期環壕較淺,不足以進行防御,其主要功能起界溝之作用。與興隆洼文化年代相當的后李文化小荊山環壕為圓角三角形,其人工挖溝寬4~6米,利用的自然沖溝寬19~40米,雖然存在一定防御功能,但與后期大規模的環壕仍不可同日而語,其作用應與界溝有較大關聯,如壕溝外側西北部為墓地便可為證[10]。到了新石器晚期,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聚落分布較多,規模有大小之分,且出現等級差別,農耕水平較高,對土地的需求愈加重要,從而引發頻繁沖突,加之天然屏障已難以維持聚落之安全,大規模防御性環壕便由此產生,凌家灘遺址環壕產生便與此相關。像這種情形比比皆是,如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現一廟底溝文化聚落環壕,其寬9~13米,深2~4米,具有較強的防御功能,凸顯出遺址在當時聚落群中的特殊地位[11]。半坡遺址居住區內的二重環壕結構及哨所的出現,反映其防御功能進一步加強,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社會結構[8]。新石器時代末期,隨著社會結構形態復雜化,等級差別進一步拉大,從而出現了貴族特權階層,如巫師、軍(王)權首領等,聚落間利益沖突較為頻繁,僅僅依靠天然屏障及人工環壕進行防御,已遠遠不夠,如應對防御遠射或投擲類武器的襲擊,即便在環壕邊使用輔助設施-柵欄等,亦未能完全應對外族或野獸的入侵。隨著社會發展及人類思想的進步,發現因開挖環壕產生的土方可以就近置于溝邊,從而起到一定的防御之效,這便是城墻的雛形。如尉遲寺聚落壕溝內側深3.5米,而外側僅深1.2米,便是一例。

凌家灘遺址防御體系是天然與人工的有機結合,這種情形在新石器時代是較為多見的,這里就不一一列舉。其原因是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人類認識與改造自然的能力受限所造成,故早期防御體系多與自然條件有關,即便開挖環壕,亦多位于水域或河道之處,從而形成早期特有的防御體系。后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文明化程度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從而形成以城墻為主體的防御體系,且城垣做工愈加精細,存在著從地面起建到挖槽筑基、從夯土堆筑到夯土版筑的技術發展歷程[12]仍至后期出現了城墻馬面等防御設施,這與自然防御的能力大大消弱有關。
[1]王心源,吳立.巢湖凌家灘遺址古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特征[J].地理研究,2009,(5):1209-1214.
[2]梁中合.尉遲寺聚落遺址發掘成果累累[N].中國文物報,1995-07-10.
[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4]錢耀鵬.中國史前防御設施的社會意義考察[J].華夏考古,2003,(3):45-47.
[5]裴安平.聚落群聚形態視野下的長江中游史前城址分類研究[J].考古,2011,(4):50-59.
[6](英)柴爾德著,周進楷譯.遠古文化史·第七章[M].北京:中華書局,1958.
[7]錢耀鵬.關于半坡遺址的環壕與哨所—半坡聚落形態考察之一[J].考古,1998,(2):45-52.
[8]朱永剛.中國東北先史環壕聚落的演變與傳播[J].華夏考古,2003,(1):32-41.
[9]錢耀鵬.日本學者關于環壕聚落的研究[J].考古與文物,2002,(4):58-67.
[10]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館.山東章丘市小荊山后李文化環壕聚落勘探報告[J].華夏考古,2003,(3):3-11.
[1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1,(6):16-32.
[12]錢耀鵬.簡論中國古代“城”的起源問題[J].新疆文物,1995,(3):71-74.
ON THE DEFENSE SYSTEM OF LINGJIATAN RUINS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LIU Song-lin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of Hanshan County,Hanshan Anhui 238100)
Lingjiatan ruins,wi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efense systems,early make use of“located in Taihu Hill,surrounded by water on three sides of East,West and South”to show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defense.With the changes of climate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slowly moving back of water on both sides of the land and a dramatic increase of settlement population,the living area extends to the beach land of both sides of the land,resulting in the extinction of natural defense function,so the Lingjiatan ancestors will dig moats to strengthen its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the late Neolithic settlement sites,its defense system has the certain social significance.In a transition node of large-scale moats and walls changing,its defense syste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has more universal meanings.
Lingjiatan ruins;defense system;moat;city ruins;social significance
K878.3
A
1672-2868(2014)05-0005-04
責任編輯:楊松水
2014-05-22
劉松林(1972-),男,江蘇揚州人。含山縣文物管理局(凌家灘遺址管理處),文博館員。研究方向:凌家灘文化。